另一种水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苗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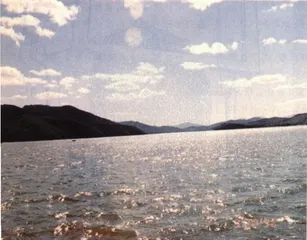
滔滔松花江水,你还能重现往日清澈吗?
松花江:浪花飞出有毒汞
住在吉林化工集团附近的农民从来不吃自己种的菜,可是他们的菜地却一年比一年膨胀。这些农民有自己的小算盘:且不说把这些菜拉到城里能卖个好价钱,单是拿它们说事儿,向吉化集团索赔就能进帐颇丰。
拉着蔬菜去索赔,透着一种农民式的精明,而且个个理直气壮:你们厂的废水废气把我的菜污染了,没法吃没法卖,没了生计。你们不赔谁赔?
农民的振振有词,源于吉化的排污事实。50年代末60年代初,松花江曾发生震惊中外的汞与甲基汞污染。无机汞在自然环境中转化为毒性更大的甲基汞,通过生物的富集作用和食物链传递,在人体中积累,最终使人致病,甚至死亡。而吉化公司103厂醋酸车间乙醛工段就曾是向松花江排汞的大户。以其为代表的松花江沿岸百余家用汞单位先后把149.8吨无机汞,排入松花江水体,致使松花江鱼虾绝迹,水体功能受到严重破坏。虽然目前松花江流域的汞污染源已得到一定控制,人为排放的汞量目前已不能构成对水体的污染威胁,但已经进入沉积物中的沉积汞在微生物作用下还会不断进行甲基化,成为汞污染源。汞污染的警报并未解除。
与此同时,松花江吉林江段的有机毒物污染又让人忧心忡忡。监测结果表明,松花江被检出的有机化合物中,属于美国EPA首要污染物名单的有44种,占检出有机污染总数的31.9%;属于中国有毒化学品优先控制黑名单的15种,占检出有机污染物总数的10.9%;其中有致癌性的23种,占检出有机污染物总数的16.7%。松花江吉林、扶余江段和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江段中,有多达65种有机毒物。自吉林九站至哈尔滨四方台水源地持续检出致癌物14种。
比起身处松花江下游,以松花江为饮用水源的哈尔滨人,身处上游能喝到干净水的吉林人堪称幸运。
哈尔滨市原市委书记陈剑飞有一句“名言”:上游配什么方,下游喝什么汤。这位多年为解决哈尔滨市民饮用水源污染问题而奔走呼吁的老人,一语道破哈市人饮水的危险处境。哈市是整个松花江流域唯一一个全部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源的大城市,每天需水120万吨,实供100万吨,其中取自松花江的有80万吨。在全国城市定量考核中,哈市城市饮用水达标率仅为89%,居全国最低水平。哈市环保局长陈怀涛说:“水源地是哈尔滨的命根子,我们把朱顺屯水源地的水质当成眼珠子那么看。”根据哈市提供的监测数据,朱顺屯水质已经超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标准。1996年上半年,高锰酸盐指数超标率为100%;生化需氧量超标率为67%;非离子氨超标率为50%。哈市自来水公司根据历年污染状况指出:松花江水流量在500m3/秒时,水污染指标氨氮超标,流量在300 m3/秒时,污染更加严重。用传统净化工艺处理后的水质已经难以达到饮水标准。
陈剑飞书记到北京参加人大代表会时,总是随身带着两瓶哈尔滨市的自来水。每当他把这两瓶浑浊的液体展示给与会领导时都会动情地说:“我要让大家都看看,哈尔滨市民喝的就是这样的水!”现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安振东在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写提案要求治理松花江污染。他说,自己有生之年的一大愿望就是为哈尔滨市民开辟出一处相对安全的新水源地。
最近,数名记者来到哈尔滨,记者们在下榻的宾馆拧开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是黄黄的浑水;在哈尔滨人家里作客,主人会殷勤地为你倒上矿泉水,告诉你这水你绝对可以放心,不是哈尔滨市生产的,没有污染。几位哈尔滨商人到北京看朋友,绝对不喝暖水瓶里的开水,而是从街上抱回一大堆矿泉水,他们说,知道北京的自来水是安全的,但我们喝矿泉水已经习惯了。更有消息灵道人士透露,哈尔滨市生产的一种名牌啤酒出口俄罗斯时被拒收,因为里面的汞含量超过标准……
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污染事实,更令人痛心的是,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通过对哈尔滨市癌症死亡率调查分析表明: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逐年上升。而居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死亡率高可能与饮用松花江水有直接关系。
哈尔滨市民临江而居,游泳爱好者众多。但是横贯市区的松花江水质多数地段已经是超4级,按理说,这种受到严重污染的水已经不适宜游泳。江水穿城而过,哈尔滨水多却无处游泳。实在按捺不住“游兴”的人们想了个掩耳盗铃的补救措施,游泳之前从家里带桶干净水,上岸后马上用它冲洗身子消消毒。由此,游泳带桶水成了哈尔滨江边一景。然而,一桶水的效力实在有限,江中的污染物附着在身上,许多游泳者都落了个皮肤搔痒的毛病。
松花江流域是个贫水地区。人均占有地表水资源量为1650m3/年人(全国为2400m3/年人);亩均占有地表水资源量为440m3/年亩(全国为1770m3/年亩)。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用水量每年以5.3%的速度递增,同时水污染的程度也在以每年7.7%的速度递增。于是有人担心:长此以往,松花江流域是否也将像淮河一样,几百万人守着大河没水吃?
松花江在全国7大水系中属于水质污染相对较轻的河流。但是,199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已把松花江列为我国严重的污染河流,松花江大部分江段不能满足使用功能……松花江的污染特点是流域内重工业比重大,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的企业较多,结构性污染比较突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松花江上游吉林市江段水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松花江因此被列为国家先期治理的水系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松花江水污染的治理比起其他水系来要早。松花江的污染与其他水系相比有其特殊性,但是松花江污染治理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以松花江为镜,也许可以折射出中国江河水系污染治理中一些误区。

由于淮河污染严重,河南省宿鸭湖水库被污水毒死的鱼在水面漂了一层,渔民朱义良捧着一把死鱼说:“过去每天可捕鱼1000多斤,现在最多200斤。”
7大水系:何处寻觅一片净水
松花江上游吉林江段的汞污染应该算作松花江水系污染中最典型的始作俑者,如今汞源虽然切断,但沉积在水体中的57.7吨汞仍然是危险的次生汞源,如果通过自然降解办法进行疏散,至少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水体动力学的作用,这些沉积汞将不断疏散并向下游运动,成为下游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根源。即便如此,吉林市在分析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仍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境外来水。吉林市称:根据“松花湖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成果及近年来松花湖的水质监测资料,目前安图、抚松、靖宇、辉南、梅河等市县,通过松花江干流及辉发河水系对松花湖的污染贡献已达67%以上。因此我市的水环境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上游来水的水质,而我市又不能控制,故存在调控能力不强的问题。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更把哈尔滨江段的污染责任大包大揽地分给了其紧邻的上游城市吉林市。哈尔滨称:来自吉林省的松花江和来自齐齐哈尔的嫩江在我市上游三岔河口汇合,流经肇源江段进入我市松花江段。每日分别接纳来自吉林省城镇的360多万吨污水、嫩江100多万吨污水。历年监测资料表明,松花江在进入我市江段前已受到严重有机污染,上游来水中主要污染物就已超地面水三类水体的标准,不宜饮用。尤为严重的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所属各厂排放的大量化工废水中含有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直接威胁着我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把眼睛紧盯着上游的污染,这似乎是每一座城市抨击水污染的杀手锏。然而,下游还有下游人,监测数据表明,沿江每一座城市都以其自身的污染为松花江污染作了“贡献”。以哈尔滨为例,在哈尔滨市下游断面“大顶子山”断面监测结果表明,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非离子氨均100%超标,而且这些数据明显高于上游朱顺屯断面。这说明除上游对松花江哈尔滨江段的污染外,哈尔滨市自身对江水的污染也十分严重。
从上游到下游,每一处都深受上游污染的影响,同时每一处又都是其下游的排污源,受害者亦是害人者。就这样污染的贡献层层迭加,滔滔江水东流去,松花江的水质也越来越差。
那么,“毒源”是如何形成的?以松花江论,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的重污染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是江水主要污染源,其中绝大多数的污染贡献来自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松花江沿岸的中小企业80%处于休克或半休克状态。经济不景气帮了环境的忙,工厂不开工,自然也就不排污。乡镇企业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污染,这一点与深受乡镇小企业污染之苦的淮河形成对照。
目前,淮河流域水污染严重已经是家喻户晓,综观我国7大江河水系,竟无一能逃得过被污染的噩运。中国之大,想找一片净水竟已成一种奢想。我们从来都把大江大河比作自己的母亲河,江河孕育人类文明,而可悲的是,我们如今也许只能在工业文明难以触及的蛮荒之地才能找到一条丝毫未被污染所害的河流。
还我净水:国家官事自家事
佳木斯市环保局长符国志原来是佳市的建委主任。佳市的许多企业的扩建工程,当初是由符局长批的。如今换了位置的符局长思路也随之转换,现在他督促这些工厂一个个地治理污染,就像当初批准它们开工建设一样,毫不含糊。符局长调侃自己说:这是屁股指挥脑袋。
话虽粗,可是道理深刻。说到治理污染,地方政府口头上都喊得挺欢,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干了,却又都现出一脸愁容:没钱。在江河流域污染治理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把眼睛向上看,盯着上游的风吹草动,振振有辞地揭露他们的污染、拆穿他们为了应付检查而玩的“花活”。因为污水流下来,喝水的是他们自己。但是与此同时,却对自身的污染治理不那么上心,因为治理污染必然要花钱,大治则花大钱,而直接受益的却是下游,于本地并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又有哪个肯把钱投到这些个见不到效益和成绩的治污项目中去了?
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安振东一语中的:狭隘的地方利益是制约治污的痼疾。
谁都希望,每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就不产生污染,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现代工业的副产品就是污染,于是人们寄希望于建工厂的同时建治污染系统,防止污染溜出厂门,可实际上这又成为人们的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任何企业的第一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每个企业家都要算投入产出帐,治污等于在最初投资时增加一笔资金,而这笔投入又不出效益。于是,我们又走进另一个倒循环圈:当环境被污染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再大声疾呼治理污染,而此时又需更多的资金,没钱又成为治污的头等障碍。
在环境治理方面,我们似乎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但松花江流域的污染与治污又给我们某些启示,让我们换一种思路:从污染源看,松花江与淮河不同,淮河主要污染源是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而松花江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对于淮河的治理,国家采取的是强硬的行政命令,关掉沿河700余家小化工厂,但如此作法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关闭工厂必须砸掉一批农民的饭碗,其付出的代价尤为惨重,而且效果很难持久。松花江的治污则有些不同,因为是大中型企业,国家可以集中投资治污,相对而言投入少见效大。也许正因此,松花江水还未到淮河水毒死人的地步。
作为松花江原来最大污染源的吉化集团,在治理污染方面的进展又使我们的思路进一步开阔:吉化为我国第一大化工集团,它污水量大,从污水中可提炼的有用物质也多,因此它的污水处理厂从1980年投入运行以来,共创产值5.91亿元,利税3.74亿元,治污变成赚钱事儿。
今年,吉化上马30万吨乙烯工程。化工部一位高级工程师当时谏言:在发达国家,30万吨乙烯项目已禁止上马,这不仅因为生产规模偏小,导致产品成本偏高,更重要的是治污成本也因生产规模较小而偏高。我国目前已建了好几个30万吨规模的乙烯工程,且不论污染处理设施重复建设浪费投资,就是这些治污设施运作后,废水的重复利用、提炼的有用物质也因规模偏小而效益偏小。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建1个100万吨的乙烯工程比起建3个30万吨的乙烯工程,在治污方面的投入前者只是后者的2/5,而治污设施运行所产生的效益前者却是后者的5倍。
工业文明破坏环境,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大工业却比小工业更少地破坏环境,这也是一个事实。可我们并未足够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与环境破坏程度,并非成正比。
毫无疑问,中国环境状况每况愈下,关键原因在于各级政府的环境意识,这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保护环境的认识程度,也取决于他们改善环境的思维方式。不过,相对于“长官意识”而言,更为广泛的是保护和治理环境的“全民意识”又如何?
我们应该承认,人们的环境意识近年来与日俱增,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意识尚停留在浅层次。以松花江流域为例,哈尔滨人知道自己的江水被污染了,他们最直接的反应是自己解决问题,环境意识至今只停留在自我保护的层次上。至于主动的防污意识,老百姓认为污染环境是企业的事,忽略了自己的排污量。其实,城市污水由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两部分组成,生活污水的比重约占30%以上。
现在仅停留在唤醒“全民意识”上远远不够,要把全民意识转化为全民行动,需要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使命就是不仅让百姓意识到自己对环境的责任,更要让百姓看到自己对环境付出努力的实效。
郝春曦(国家环境保护局污染控制司水处副处长):
为什么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我国水污染的状况仍无明显改善?主要因为我国工业基础差、污染欠帐多,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速度一直很快,高速度发展势必对环境造成压力。城市生活污水增加、人口膨胀等等问题,则加重了水体的污染负荷强度。污染物削减得少,增加得多,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以太湖为例,“六五”期间水质为2~3类,“七五”期间降为3~4类,到了八五期间更降为4~5类。“八五”末期污染已经相当严重。
夏青(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淮河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组组长):
目前我国城市邻近水域的水体功能基本被破坏,而真正解决水污染的工作只能算刚刚开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为我国水污染防治提供了一个范例。明确污染的法律责任,树立“超标排放即违法”的观念,环保部门大胆、严格地执法,对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企业坚决关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污染防治工作落在实处。 水污染环境污染环境保护松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