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风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伯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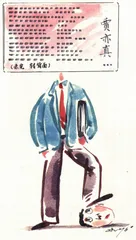
经年游走在人群里,“场面”虽不多见,但场面中人却见过一些,其收获之一(也有可能是唯一收获),就是抽屉里积压了厚厚的一撂名片。尽管这些名片上电话、地址大都凿凿可考,但我几乎从未按上面的电话、地址去打扰过谁。张承志说他“对名片的行为仅仅是淘汰”,另外就是“大撕特撕”,从中得到“充满快感的体验”。这种“行为”和“快感”只有名人才有——只有有幸经历无数场面的名人才有可能被递交如此多可供大撕特撕的名片,也只有名人中的名人才有如此激愤的心境。而我之所以一直保留这些于我毫无实际用处的名片,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值得细细观赏的“人文景观”,因为它们展示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万种风情。曾经有一个戏剧小品,说的是两个人把名片当扑克牌来玩,玩者兴高采烈,观者感慨万千。人海茫茫,一场大牌局,其游戏规则简单到与“争上游”的规则差不多:点大一级压死人。依此规则,在争当“黄雀”的共识下,人们交替担当着螳螂、蝉、黄雀的角色。社会生活因此呈现为一种全盘牌局化的特征,所谓“档次”,所谓“品位”,所谓“腕儿”,都不过是“点数”的另一些说法,人的社会行为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牌”而已,而散发名片可谓最为直观的“出牌”方式。一日忽发奇想:以手头这些名片为基业,再到各路朋友那里讨、拿一些名片,将之汇编起来,并在每一张名片下面加两三句正批、歪批的话,以阐发每张名片之微言大义,成为一本似书非书的东西,令与我有玩味世相之同好者或若有所思,或解颐喷饭。然性情疏懒如我者,要完成此虽非宏大但也并不轻松的工作,只能留待猴年马月。今仅将平日观赏名片之零星感受聊作小文以记之。
没名人的名片
有人(好像是韩少功)曾对名片下过一个定义——它是这样一种纸片:人们在上面尽可能多地写下一些莫须有的头衔,以尽可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不自信。此定义颇有老吏断狱之风,准确得到了尖刻的程度,但它大概只适合于一种名片——时刻觊觎着名声和地位而又一直未遂所愿,暗暗忍受着不被承认之苦的人士的名片。此类人士尽管在某个地界内(至少在他的家里)可能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但自知之明告诉他还小不可言,于是他开始在一张小纸片上重塑形象。以阿德勒的学说观之,这些名片是以病态的方式实施着“对自卑的超越”,实属一种对于名声和地位的“意淫”。比如这样一张名片:
亚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XX省XX市XX乡个体劳动者协会理事
蔡亚洲 农民企业家
这张名片的主人的真实身分是一个路边饭馆(兼营切面加工)的老板。再如这样一张名片:
神农人体科学研究开发中心副秘书长
华侨气功师
孙元祥 研究员
(“农”、“体”、“学”、“侨”等字兼以繁体排印,背面是以上内容的英译,其中“神农”被译成peasant of God[上帝的乡巴佬],“研究员”被译成study member[英语无此说法])
这位研究员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早晨在武汉某公园教一群老人练“摆子功”。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总经理(甚至总统)比一个饭馆老板高贵和高明许多(这也是我与那位饭馆老板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我也不认为一个教人练气功的人一定没有当教授或研究员的能力(爱因斯坦就当过邮局职员)。我尊重从事每一种正当、合法职业的人,但我无法尊重(除非出于礼貌的考虑)那些因不自信、不尊重自己职业而虚张声势、装模作样的人,或者干脆以虚张声势、装模做样为业的人。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然也包括印老实的名片(如果印名片为他的工作所必需)。拉大旗做虎皮、以白萝卜冒充象牙的名片满天飞舞,只能表明经济、法律秩序的不健全造成了人的经济、法律身分的模糊,以及人的心灵秩序的紊乱。而这也必然意味着整个社会敬业精神的欠缺,虚与委蛇则成为一种被认为是万难改变因而只好顺从的习俗,巧立名目、夸大其辞的广告术成为在社会上“争上游”的人们彼此心照不宣的附加规则。
这种广告术非自今日始,古来即有“精兵10万,号称30万”之常规。如今乐于声称或暗示“我最近很忙”的人都说“商场如战场”,自然也就把过去战场上的惯技挪移到了商场以及别的什么“场”上来了。奥斯卡·王尔德有一次接受海关检查,当被问到有什么要申报时,他的回答是:“除天才之外,本人一无所有。”不管在你看来这是一则佳话还是一则笑话,我们——这些组成了各色人等并在各色人等中讨生活的人们——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别人的检查,并力图周到地申报着我们的内涵,每个人手中随时准备向各色人等散发的名片就是我们事先填好的申报单。凭着这张复制了无数份的单子,我们力图进入到别人的视野并在其中占据我们预期的位置。在这种过程中,名片不仅具有先声夺人的优势,而且充当了我们最忠实、最得力、最不失体面的吹鼓手。《围城》里的汪处厚爱借他在教育部当次长的侄子之势压人,但又不好意思直说“我侄子在教育部当次长”,只好一边拉长了声音说“我那侄子——”,一边把目光投向站在身旁的一位善解人意的拍马者,拍马者立即补充道:“就是教育次长……。”要是爱吹牛的人常常有爱拍马的人侍候左右该多好,只可惜这样的幸运又常常可遇不可求!而万幸的是名片可以完满地担当此任。名片再准确不过地体现着名片主人的意图,上面写满一堆在清夜静思时或许会令他汗颜的封号、头衔,但当他在各种热闹的场面中发放这些名片时,全然是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派头,因为他并没有像王尔德那样大失体面地吹嘘自己,而是一种由白纸黑字构成的身外之物在介绍自己,他当然可以超然物外,不出一言而尽得风流。
不过这“风流”并不太可靠,因为它全然从纸上得来,当然也就具有了许多纸上之物的致命弱点——无法由自身来确保其有效性。它随时有迅速“通货膨胀”的可能。几年前,报上一条新闻标题令我大吃一惊:“南斯拉夫人都是‘亿万富翁’”!读罢这则新闻我则哑然失笑。当一个人扛着一袋子纸币去买一袋子面粉时,他会很自然地想到该重新设定一种货币单位和面值了。同样,当“总经理”、“董事长”、“知名学者”等头衔已显出滑稽意味来的时候,人们也会逐渐达成某些共识或“行规”。比如这样一句新俗谚就包含着此类共识——“见女士别问岁数,见编辑别问印数,见总经理别问手下的人数。”这似乎表明在有片阶层内部已出现“洗净铅华,再度收拾”的呼声,预示着一场“名片维新”也许即将来临。
名人的名片
本来是一种社交用品的名片担当了太多的功能——名片是申报单,名片是遮羞布,是便携式广告牌……但这些描述只是对大多数——对名声孜孜以求而难逃默默无闻命运的人总是占大多数——名片而言。在社交场合,偶尔也能见到或得到另外一种名片。它们的主人是那些其名字本身早已化作一张无形无际的名片的人,即名人。名人虽总是社会的少数,但由于各种媒体的发达,名人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有社会学家指出,名人数量的通胀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在社会各领域,“名人”像昆虫一样繁殖也像昆虫一样短命。因一首小曲而一夜成名的小歌星也在广播电视上诉说她(他)暗以为荣的“名人的烦恼”。台湾作家柏杨把所有名人统称为“大家伙”,其实在大家伙儿都想领风骚三五天的风气下,有许多“大家伙”本是些“小家伙”,而且不久之后会泯然众人。所以同为名人,其层次也参差,其姿态也各异,其名片也就形形色色,一点也不单调乏味。
由于对于名人来说,普通名片所刻意标榜的那些角色、名份已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他们用不着再在名片上画蛇添足。名片上但见其大名位居正中,恰如其分地表示着他在社会上如日中天的状态。但“大家伙”这种不标榜、不自夸的风度并无多少不俗之处。禅宗有“开口便俗”的说法,套用萨特的话来说,你不得不自吹,你不得不标榜,你不标榜就是以“我已用不着标榜”的语式来标榜。如果你是一个红得比太阳还红的节目主持人,那么在你的名片上标上“节目主持人”比不标自然得多,本份得多。印名片无罪,但诚恳、本份是印名片应守的通则,“不俗”也从这里开始。甚至可以说,有了这诚恳、本分,在名片上标明头衔与否和标出何种头衔都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名人或非名人地位处之泰然、坦然。手头有一著名指挥家的名片,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指挥家本人的亲笔签名和真实的地址、电话。名片上的字迹庄重、洒脱,决无那种为掩饰字迹的粗陋而精心设计出来的花梢笔法。整张名片看起来既不矜持于自己的名人身分也不表演性地作淡然状、随和状以博得更多的颂扬和敬佩。正如拉罗什福科所说,一个人回绝自己应得的赞誉不过是为了得到两次赞誉。与没名人爱以莫须有的头衔给自己涂脂抹粉相应,有不少的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爱以另一种忸怩作态的方式亮出自己的身分,其动机都是要因某种自封的头衔而使自己在所属的群体中超凡脱众。所以某些名画家给自己加上“油漆工”,某些名作家给自己加上“码字工人”等欲雅故俗的封号。不知道这到底是在侮辱艺术还是在侮辱工人,是体贴下情还是自命不凡。本人手头就有这样一张名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身分证号码:
XXXXXXXXXXXXXXX
XXX 手工艺人
名片下方照惯例是住址及住宅电话,但二者之中至少有一个是编造的,因为上面的电话局号表明名片主人住在北京市东北部,而住址“永定门”在北京的南部。这编造的住址或电话部分地表明名片的本意并非想你把它当作名片来用,而只是让你好好拜读一下这张名片,一睹名人风采而已。
从另一角度,这张名片,倒也很充分地阐释了名片的某种值得人琢磨的意味。很多时候,名片就是“明骗”,他并不想告诉你你真正需要的,他只想让你“意会”他最想告诉你的,真与假,虚与实,藏与露,巧与拙,云笼雾罩,风情万种。 名片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