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权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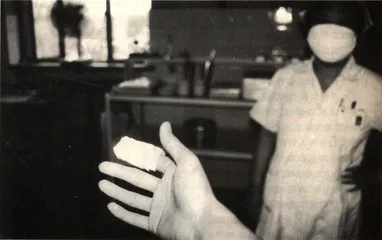
病人在医患关系中,往往甘居被动地位。多少病人会问:我们需要什么权利?
长期缄默的病人权利
一支珍珠明目滴眼液在新城药店标价3.5元,在宁夏自治区医院的划价单上竟是22.91元,价差7倍;北京一王姓消费者反映,一次感冒花掉他半个月工资,冲剂、片剂、糖浆加针剂,种类多多近300元;浙江台州师专一病人使用浙江临海第一人民医院销售的“多次获奖、无毒、安全”的“坤洁乐药巾”,不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加剧了病情。据台州卫生防疫站化验,该药巾细菌含量高达11万,超标110倍,霉菌540个,超标54倍;内蒙古某医院为患者做接骨手术,8枚钢钉中5枚断裂,导致骨折错位;植入人体的劣质心脏起搏器因“电池耗尽”,则使山西、四川的多位患者身遭不测……
年初的这些医疗恶性事件至今让人心有余悸。今年第二季度医疗医药投诉竟达1961件,占整个投诉案件的12.3%。“医药费用过高,医疗事故频繁,医疗质量无保证”;“铜臭玷污了红十字”;“假药泛滥触目惊心”;“血泪控诉:究意谁对病人负责……”在媒体缺乏行动力量的悲观报道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似乎又默认了病人在医患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求医问药往往不仅要有“吃白眼受冷淡”的心理准备,而且可能遭遇钱袋和身体的“双重宰割”。
好在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了病人的权利保护。今年3月,青岛市卫生局发布了红头文件,开宗明义告诉病人:您有得到医务人员礼遇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您有对本人病情和医务人员采取的治疗方案知情同意的权利;您有要求保守隐私,解释所付医疗费用,提出意见并得到答复的权利。
紧接着,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8月联合出版的《病人的权利》一书,从实用角度,告诉病人“有什么权利”“怎么和医院打官司”,警醒医院医务人员“全包全揽”和“怠慢不管”一样可能造成对病人的侵权。
“病人的权利”在长期缄默之后,经医学、法律界“再三斟酌”,由此可能纳入公共话语。
谁的权利最需要关怀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确认的“一张病床只能睡一个病人,每两张病床之间距离3英尺”算起,到1970年美国医院审定联合委员会提出的“26款病人权利”,再到1975年欧洲理事会16成员国在“安乐死问题备忘录”中确认的“病人的基本权利”,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病人权利的提出和成熟是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医生的职业化,病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得到主流的认可。医生和病人才渐渐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双方,以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基于信仰的传统医患关系。
“一个病人开刀或不开刀都能治愈,一个医生既有责任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又要‘在业务上进取’——评职称,但评高级职称需要凑足50例手术病例,这时候医生该怎么办?”长期从事医疗法律实务的中国政法大学卓小勤先生认为,病人权利提出的现实根据是价值的多元化。
病人进医院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减轻痛苦?病人希望医生帮他什么?卓小勤先生在了解诸多医疗纠纷之后甚至认为,“‘病人价值多元化’也是病人权利提出的理由。”“治病还是减轻痛苦、维护尊严在一些时候是矛盾的,比如妇女难产母婴不能两全,癌症晚期病人身心遭受无谓的折磨……”什么是病人真正的“愿意”?尊重病人的选择不仅仅是对病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能使医院避开不少麻烦。
医学模式的转变是病人权利提出的又一依据。医学本身包含了技术和人道两要素,但随着现代科技的介入,技术要素不断膨胀,人道要素逐渐被湮没,医院异化为“见物不见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不治人”的“机器修配厂”。化验单、心电图、X光片的检查结果似乎就是一切,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完全被抛弃。而近年来,这种“纯粹的生物医学模式”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轨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病人的权利,作为脆弱的个人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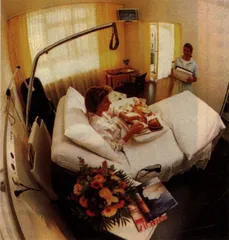
药人权利的提出,是消费者权益运动发展的产物
谁是权利的最终尺度
“病人有获得为治疗他的疾病所必需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病人有获得尊重人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病人有获得公正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病人有获得节省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病人有就有关自己的病情作出决定的权利;病人有知情同意、保密权和隐私权。”
医疗权源于健康权,健康权归基本人权之列,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实标榜公正和机会平等的现代社会向人们许诺的医疗权存在不少现实的龃龉:今年1月27日上午,北京东城一王姓女孩突然发病,头晕、胸痛、呕吐,惊惶失措的父母将女儿送到附近医院就诊。医院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病人被打发回家,病情继续恶化。晚9点,父女再次到医院就诊,并向医生提出怀疑“可不可能是肺炎”,但医生拒绝给病人照胸透,维持上午诊断,只加一针止吐针,并拒绝病人留院观察、输液的要求。病情继续恶化。结果第二天,病人辗转到崇文区一医院,被确诊为双侧肺炎,病人提出转院被拒绝。第三天下午4时,这位19岁的姑娘停止了呼吸。死亡通知确定为中毒性心肌炎、急性肺水肿和休克肺炎。
事后,死者家属起诉两家医院,法院以“两院玩忽职守,重视不够,延误诊治时机,涂改丢失病历”为名判处,并责令赔偿损失。但是几千块钱顶得上一条性命吗?病人最基本的医疗权遭到了践踏。
必需的医疗服务权不但取决于医疗水平,而且与患者的支付能力相关:而“不分贵贱,不论愚智(《千金要方》)”不但在孙思邈时代仅仅是理想,医疗等级的现实存在使受尊重的医疗服务缺乏普遍意义;医疗“大处方”成了古人徐大椿所谓的伤身害人破家的现代“人参”,医疗费用的高涨不但使个人节省费用的医疗服务权受挫,而且给国家社会带来负担。
与隐私权与保密权当仁不让的地位相比,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则长期以来“存在异议”。
古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的教海“不要把病人的未来和现在的情况告诉他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法典喋喋不休地强调“只在绝对必要时才可将病情透露给病人”,近又有“医生讲真话还是‘心灵有所保留’”的争议……他们的理由似乎不无道理:缺乏医学常识的病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理解病理学专用词,而误读引起的情绪波动对治病弊大于利;医生讲真话告诉坏消息是“浪费时间,不顾恶果的蠢行”。医生的神圣责任不正在于“避免做使病人沮丧以及挫伤他们精神的一切事吗?”此外,医学本身并非精确科学,存在于模棱两可之间的或然性使医生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撒谎”。
高尚的谎言还是令人沮丧的实话?实际上,当今的患者以及家属都认为,真实地了解病情更有助于治疗,在对癌症病人的调查中,73%的人认为“医生应该告诉病人真相”。
“从现状来看,最大的问题在于能给病人的权利给了多少。”据北京大视野调查公司调查,北京市民对医疗服务的评价是刚刚及格,14.3%的人认为医生态度恶劣,21.4%的人反映挂号难,31.6%的人认为开的药太多,12.1%的人向医生递过“红包”。
“门诊不敢进,药品不敢用。检查不敢做。手术不敢动”……到底是什么妨碍病人权利的实现?
谁比谁更无知
据《病人的权利》责任编辑袁钟先生说,此书从出版到现在反响颇多,而且有意思的是,对这部旨在“普及知识,提高病人权利”的书,掌声主要来自医务人员,病人却反应冷淡。一些新华书店的经销人甚至很为难:“病人讲什么权利?卖给谁看?”
“只要不说出来,即使出了事,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起他了解的几桩医疗事故,“明明是医院的错,可病人还要感激涕零。”
“病人只管生病,医生只管看病”,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上相差悬殊,病人一般处于脆弱和依赖地位。医学技术化和分科细密化,“隔行如隔山”,诊断书上的潦草字迹又夸张了医院的持宠地位。
病人在医学常识上的空白直接导致病人“权利意识的沉睡”。病人一迈进医院门槛就可能变得驯服,雪白的墙,来苏水的气味、医生冷淡无情的面孔、庞然大物一样的检测仪……所有这些都使病人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他们要对自己做什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记者在9月25日对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病人进行了随机采访,问及“病人的权利”,他们的普遍反应是“病人还有什么权利”?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同志讲,“虽然近年医疗投诉增多说明病人权利意识有所提高,但是依法保权意识尚待进步。”
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胡搅蛮缠”。权利受挫之后不是去法院投诉,却搬着被子睡在医院长凳上等“公平”,起诉书上只有“要求查明真相,以儆后人”,而不是确切提出某项权利受损,要求医院赔偿。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作为病人权利的承担和维护者,医院和医护人员对病人权利的无知。“一心为患者好”的医生没有存心害病人的,造成侵权的原因往往是医生“不知道什么是病人的权利,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冒犯。”
据讲,我国现有医学院校中,医学法律教育基本上是盲点,而国外学医从医不但要宣誓,而且《医生法》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医学院的必修课。

病人价值多元化是病人权利提出的理由
谁保障谁的权利
在一个法权社会,人们一般不能指望社会风尚、人性良知维系权利,而应当把围栏与利剑的权利交给有力的国家制度、合适的法律。
被认为是“医院顽症”,普遍败坏医护人员形象的“大处方”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医疗体制和国家财政分配的问题。
一方面,药价越涨越高,医药收费“令人咋舌”;另一方面医院的技术服务价格则纹丝不动,看病挂号费仅相当于一般公园门票的1/2。“医院收费结构的失衡不但损害了病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对医生劳动价值的亵渎”,社会科学院医学伦理学专家邱仁宗先生说。
对此,药管局的“处方”是:医药分开,医生处方金额与奖金脱钩,医务科室收入与药房效益脱钩,压低卖药品和大型设备检查收费标准,提高技术劳务价格,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卫生部类似的处方是“分开核算、分开管理”。但据卓小勤先生分析,“无论是药管局的缓药还是卫生局的猛药,因前提都是体制不变,都很难根治大处方问题。”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医院虽名义上仍是“公益性社会福利事业”,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30%左右,剩下的主要靠医院创收,而创收的主要形式是卖药。全国每年有1千亿元的医药收入需要药费填充,如果将售药补偿折算成技术劳务费,则诊治医疗费整体至少提高40%以上,同样加重患者的负担。无异于“按了葫芦起了瓢”。
怎样既维护病人的权利,又保证自身的生存发展,目前许多医院都摆不好彼此的关系。
医疗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矛盾”也是影响病人权利实现的重要原因。就拿《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来说,这部1987年颁布的“办法”历经10年,患了“不适应症”。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袁钟博士分析,《办法》“不适应”的原因不仅在于10年来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而且在于针对对象性质的变化,“10年前的医院属于更纯粹的计划经济下的福利事业,而近年经营性已逐步成为医院的主要特征”。
是补偿还是赔偿?《办法》中规定对“医疗事故采取一次性补偿”,“最低100元,最高不过8千元”,而根据《民法通则》公平公正原则,“补偿”一说根本不存在——当民事责任双方中一方责任受损时,有权要求对方“按实际损失赔偿”。从医疗事故给病人及家属造成的身心伤害角度考虑,哪个更“人道”?“补偿”还是“赔偿”尚待商榷,但从法律效力上讲,《民法》优于《办法》是无疑的。
谁是公正科学的“第三者”
无论是“和颜悦色”的医患双向承诺书还是“翻脸不认人”的医患纠纷都需要一个客观的“仲裁者”“监督人”。
在我国目前充任这一角色的是省市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卫生局。据袁钟博士分析,“鉴定委员会的组成和鉴定都存在对患者不利的因素”。鉴定委员来自当地其他医院,很难保证他们与医疗事故单位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医疗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医疗监督必然带有感情色彩”。
多方参与、异地鉴定、聘请法医和患者代表,依照病例和原始物证,听取当事双方的意见,可能是保障病人权利最基本做法。
此外,国外以医师公会为主要形式的行业自律也值得借鉴,医师公会不但以市场的形式调配医疗资源分布,而且集团的共同利益对有损行业形象的作法“绝不手软”,客观上加强了医疗管理。
有人建议也可以让医生买保险,不买保险的医师获得不了行医资格和公众信任。起保点随着医疗事故的增多而提高,这样,医生如果想少掏保险费,除了敬业之外就别无他法。
“提高知识,保障权益”,无论是青岛的双向承诺书还是北京的《病人的权利》,都以鲜明的姿态表达了对医德医风的呼唤,对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立法的翘企。病人权利的充实与兑现,需要人们对生命与尊严更深的体认。 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