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盛气打哪儿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伯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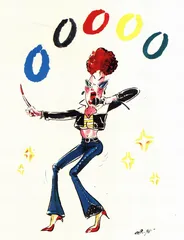
最近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歌星李玲玉因违规装修房屋而惹起诉讼的事。这位歌星装修房屋的风格堪称大手笔,为了贯彻她在居室格局上的艺术构思,竟然将住房内原有的水管、暖气管一一挪位,致使地板渗水,令住在下一层的住户苦不堪言。受害住户和房管部门多次找她讲理,皆被她冷傲地拒之门外。受害住户无法忍受这位歌星凌人的盛气,只得求助于法律。李玲玉虽然败诉,但她在成为被告时仍然保持她自以为应该有的气派——法院两次开庭她都拒不到场。这条新闻让我们有幸领略歌星走下舞台——此即大众文化时代的“神坛”——后的风采。各路明星花费重金包装后呈现出来的面貌——无论她们在MTV中穿一件土到极处也洋到极处的花棉袄作清纯兼纯情的少女状,穿一身铠甲作护花使者似的英雄状,还是穿一件长衫、系一个施洋大津师系过的大围脖作深沉学子状,以及泪流满面作大慈大悲状——都无需当真也无法当真,这如同当他们以通俗并且因通俗而美丽的歌喉唱着要送你“999朵玫瑰”或“365个祝福”时,他们姑枉唱之我们姑枉听之,用不着去想那些“玫瑰”和“祝福”是怎样的。可以并且应该当真的是他们铅华洗尽后,切实地与普通人打交道时,用他们本来的口音说出来的话,在他们本来的心思支配下做出来的事。
一位朋友给我找来与明星们此类风采有关的报道和文章,令我惊异的是这方面的材料出乎意料地丰富。一位以扮演清官而名声大噪的男演员在北京和宁夏分别面对交通警察和宾馆服务员,两次不用替身地上演了大打出手的戏;某女演员不让须眉,拍戏时因对与她配戏演员不满意,恶言相向之外还拳打脚踢(如果不是在《法制日报》上读到这则新闻,我会以为如此巾帼形象是出于记者的“演义”);一位张姓明星乘飞机时不遵守航空公司的有关规定,非但不听空中小姐的劝阻,反而口出狂言:“老子有的是钱,连你也买得起,可打七折我都不要!”北京一位名女演员事先答应在预定的日期到重庆去参加与观众见面的电影首映式,可临到那一天却置千万名等待她的观众于不顾,拒绝启程,理由很简单:她的姓名谐音是“亡机”,因而她只乘坐她认为有安全保障的国航班机,而偏偏那天国航没有到重庆的班机……
读着这些报道,我顿生一种疑问:这是些什么人?或者说,他们所从事的是怎样一种神圣已极的职业?——这种职业使得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让邻居遭罪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有勿庸置疑的理由无限地鄙视一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由傲视法律和规章,对警察可以恶言相讥,对法院的传唤置之不理,把自己的小脾气、小迷信当作毁约的强硬理由。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规定他们的特权身分,但至少他们已习惯地以为自己是高蹈于众人之上、法律之上的骄子、宠儿,当别人以对普通人有效的法律、规章来要求他们时,他们立即觉得自己的特权和尊严受到了侵犯,于是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神圣的特权和尊严。在某些堂而皇之的场合,这些明星们也可能说一些诸如“观众就是上帝”、“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之类动听的佳话。而从他们的上述行径来看,对他们来说,观众是上帝、父母还是子民、孙子已自不待言,观众的伤心、失望、愤懑之情也可想而知。但如果我们不想止于生气和抱怨,我们就得问:谁应对这一切负责?这听起来是一个相当唐突、无谓的问题——难道除了他们本人之外还要由他们之外的人来承担某种责任?但细想起来这个问题并不荒唐。
在大众文化氛围下,明星自以为高人一等决非罕事。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有一段话部分地解释了明星的自以为是:“我的朋友讲了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琴多维奇带着一种纯粹是孩子气的虚荣心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显赫,然后说道,‘一个来自巴拿特的21岁的农家青年只要在棋盘上动动几个棋子,就可以在一星期内赚到一大笔钱,比他全村的人一年内砍伐木材艰苦劳动所得的还多,你说他怎么会不染上虚荣的毛病呢?再说,你的脑子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那你不是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吗?这小伙子智力有限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他根本没想到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去自我陶醉。”同样,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伦勃朗、但丁的少男少女们也有一切理由陷入到对这些英雄替代物的崇拜之中。风助火长,火借风势,明星崇拜和明星的自我崇拜遂成如火如荼之状,那些被认为且自认为是“天王”或准“天王”的“大哥大”、“大姐大”们顺理成章地获得了类似于“朕即法律”观念和感受,而无数追星者在程度不一地认可了这一个个“朕”的同时,也就无意中程度不一地认可了“朕”们的“法律”。广义的“法治”从来都包含两个方面:法律的颁布(成文)与人们对此法律的潜在的理解和认可(不成文),没有后者,前者当然难以真正通行和实施。同时,内在于人们心中对某种法律关系不成文的理解和认可(接近于“人情”)将在很大程度上暗中干预和影响一种外在的成文法律(接近于“法理”,在西方法律制度中,主控官和陪审员大致分别代表法理与人情)的实施,甚至可能使后者徒成一纸空文。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常说,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法律,法律的进步既依赖于法律条文的修正,更依赖于人们对与法律有关的“人情”的“修正”。

现在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在大众与明星关系方面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有文字可稽的法律,这种法律从不认可明星的特权:一种是不成文的“法律”,即在明星崇拜的大众文化氛围下人们不同程度地认可了明星特权的“人情”,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后者虽然不能全然否决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前者的实施,使得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特权作出让步。具体说来,它导致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刑不上明星”现象,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对明星和大众作出一种暗示,并逐渐强化着那一不成文的“法律”。这也是明星们表现其盛气、霸气的事件时有所闻的重要原因。
多年前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一位专栏主持人对一封读者来信的答复,一位母亲来信抱怨说,她的女儿如何懒惰,如何自私,这14岁姑娘具有18岁姑娘的身材和权利意识,可要命的是她又具有一副属于8岁女孩的头脑。主持人的回答很简单:“是谁造成的这一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一味抱怨和指责明星无法无天的人来说,这一答复也是相当适用的苦口良药。我们在领教他们的无法无天之前,已不知不觉地认可并助长了他们的无法无天。在不少情况下,无原则的妥协、善意、崇拜暗中成为了丑行、恶行的同谋,尽管当丑行和恶行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又觉得难以接受,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个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渔夫。在当今的大众传媒上,作为大众代言人的记者们对明星们的肉麻吹捧与对明星们恶劣行径的指责(其中包括对明星对于记者们的不恭和专横的不满)常常是相映成趣的。那些除受来自金钱和浮名的宠爱教育之外很难有机会受别的教育的孩子们(如果条件允许,对他们也应该实施一种特别的“希望工程”)本来就具有两种极不对称的年龄(如上述“18岁”与“8岁”),极易或已经部分地被宠坏,大众传媒对他们宠而又宠,其结果不言而喻。不管你当真不当真,大众在多种意义上都是他们的父母,而“天王”和准“天王”在多种意义上都是一些被大众簇拥着的“小皇帝”——有显赫权势的孩子,把孩子当成“小皇帝”的父母总是在悄悄地造就着自己的命运——当“臣子”和“孙子”的命运。父母之道,显然应该在娇纵和抱怨之外去找。
李玲玉一案折射出了很多我们习焉不察的信息。为什么原告为了能够胜诉而只索赔500元?为什么李玲玉既不是正在开会的人大代表又没生病卧床不起,却可以在审判时不出庭等等。但无论怎样,我赞赏原告向一种本不合法但被无意中认可的显赫权势宣战(虽然是相当有保留地)的勇气并庆幸于他的胜诉。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原告的这种行为里无勇气可言,对原告的胜诉无庆幸可言。 法律李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