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又要授受不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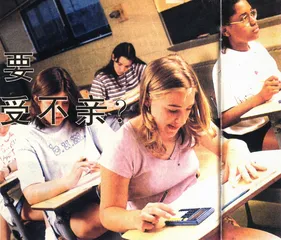
马斯泰勒中学的女学班
谁能忘记中学时代的青春躁动呢?小男孩长出了青春痘,说话瓮声瓮气的,小姑娘生出了种种古怪的烦恼,来不来就要发个小脾气,彼此之间开始感到区别,但又说不清对方的存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又正是求知的年龄,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是最为棘手的。现代的教育学家推出了种种理论和实践途径,但谁也没有美国弗吉尼亚州马斯泰勒中学那么大胆的举措,要重新把男女生分班施教,免去异性之间过早的注意力分散。他们说,女孩子上体育课往往不愿旁边有男生看着,因为她们觉得腼腆拘谨;男生背诵莎士比亚时也嫌女生挑眼,因为怕丢面子所以放松不下来。话虽中肯,但这些说辞掩饰不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这不是又倒退到本世纪之初时的教育状况去了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打破男女界限、实行男女合校教育方面,莫不为冲破宗教禁忌和封建道德枷索而走过了一条长路,方才迈入开放、平等的文明教育阶段。该怎么解释这种“复辟”呢?
社会舆论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审慎的评价,美国各地便已有不少中学如梦初醒般地对此拍手叫好,并继起而效之了。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密执根和佐治亚等10多个州都出现了开设性隔离课堂(sexual segregation)的公共学校,具体多少尚无统计,因为许多这样的学校担心触犯了有关性别偏见方面的法律,故不愿声张。
虽然看似重蹈覆辙,这种形式的男女分堂教育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式的传统封建道德其实大相异趣,在它的推广者的眼中,它恰恰是近百年现代文明教育的一个成果,是对性别方面教育实践的一个总结。这种男女分堂教育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恰恰不是强调性别差异,而是要克服性别差异带来的思维和兴趣的隔膜,因势利导,根据不同的性别特征在教育上开“小灶”。据“美国学院女性协会”4年前的一个报告,女生在男女同堂情况下学数理化的效果很不理想,经常感到思维受到压抑,以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无独有偶,近年来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开始主张并积极推动对中小学生重新实行男女生分开教学,认为至少在自然科学及数学学科中应这么做。据这些专家说,部分地取消男生同堂对男女生都有好处。德国基尔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男女同堂教育下的女性的职业前景并不美妙。在电脑行业、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等富有发展前途的职业领域中,女性构成比重一直很小,这是因为她们从早年受教育时起就对这方面学科产生了畏惧心理。比如在升入大学后,学电气工程学的女生不到4%,而这门学科恰恰是仅次于企业管理和机械制造两门学科的最热门学科之一。

1955年正上植物课的北京女五中师生们
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几乎没有哪个教育家认为重新开办纯粹的女子学校或清一色的男子学校是可行的。目前美国和德国出现的这种新式教育尽管是在男女合校基础上的分班制,也已引起不少争议,比如密执根大学的学者瓦拉里·李就说:“孩子们早晚还是得到一起去相处。新式的教育改革确实是针对现代教育中的一些疏漏的,可惜这么做恐怕不是办法。”更多的人是直觉对这种形式表示反感,美国某人权机构人士就大声疾呼:“我们不想走老路!”
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其实是不难引起共鸣的,且不说在美、德这些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早、在生活观念上极为开放的发达国家,即使在今日科技发展中的中国,实施这么一套保守色彩很浓的教育改革,恐怕也极难有市场,尽管在中国女子学校曾一直存在到了五六十年代。妇女先是为争取受教育的权利,继之为争取与男性共享受教育的环境,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其实男女分堂教育改革的基调是激进的而不是保守的,推行者中不乏女权主义者。这些人认为,由于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偏见,现代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得益者主要是男生。教师往往把班上的女生当作“社会缓冲剂”或“教育润滑剂”来使用,他们把规矩和勤奋的女孩子安排在粗野躁动的男孩子身边,好制约他们的淘气顽皮。由于教师的教学安排偏向男生,女生的兴趣和特点得不到照顾,因而迅速失去对自己的能力的信心。
这些教育改革家强调,通过男女同校以获得更多平等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无条件的男女同校也绝非合理,其中在操作上难以摆脱隐性的性别歧视。例如在课堂上,男生被提问的机会相当于女生的两倍;男生获得优良成绩往往被认为是聪明和理解力强,而女生取得好成绩则往往被评价为勤奋的结果。德国基尔自然科学研究所对600名中学生的抽查证明,在男女分班的化学和物理课上,女孩子对这些学科的兴趣明显增加。因此,新式教育的改革者言辞激烈地提出了另一种教学思路,其指导思想是:对女生有利的,对男生也应有利,但话不能反过来说。
随着这股风,德国的某些州已适时地制定了实验性条款。比如石荷州的《学校法》已经规定:“由于教育学上的原因,允许在某些学科中临时地按性别分班教学。”除此之外,柏森和黑森也作了教育法的修改,其总的原则是:“男女同校的原则不容怀疑,但部分地进行分堂教学是可取的。”
在美国,联邦法律仍然没有任何松动,仍不允许基于性别进行隔离教育(一些特殊的团体活动或组织教学,如唱歌、性教育、接触性体育竞技除外),但这股新式教改的风气依然很盛。一些学校声称,他们设的女子课堂是心理修复课,以此避过法律的指摘。缅因大学教授鲍尼·伍德发现;她教的女生班学生来年注册数理化科目的人数比其它普通班女生要多一倍;马斯泰勒中学的女生班理科成绩也远高于平均水平。
对于教改的操作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意料之中的效果。马斯泰靳中学教自然科学的谢瑞尔·昆兰说,单性课堂使得她的学生得以集中精力想些性激素控制之外的事;做点什么来吸引异性伙伴的目光,这在生理上是一个14岁小孩存在的理由。抽掉这种压力,奇迹自然会发生。男孩女孩不在一起时才会发现,他们彼此其实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差异。
看得出,在新的社会和时代形势下实行的这套教育改革尚大值商榷。我们可以依稀分辨出,尽管这套男女隔离教育的思路在形式上是在往从前走,但本质上是激进的。如果说历史上的男女分校教育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选择,那么今天出现的这种新女校不啻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反戈一击,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它自身的意味恐怕和它出现的原因一样复杂,其实践的意义和前景实难预料。
近代中国的女校
19世纪中国的女校多由来华传教士创设,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办学传播福音,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类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1844年,爱尔福赛在宁波创办女塾,浸礼会的叔末士夫人在香港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根据现有资料,这是中国近代女校的开始。当时中国人对这一新鲜事很不习惯,爱尔福赛办学之初,宁波谣言频传,说她办学是假,骗儿童挖眼睛炼药水是真。1857年,这所女塾并入了长老会在宁波所办的女子学校。
据不完全统计,1844—1860年,这类女校在全中国共有16所,均设在当时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福州、宁波,以及香港,教学程度大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规模也不大,不少学校开始时学生不足10人。学校所授课程,十分重视当时称为“西学”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如代数、几何、生理卫生、地理、天文等,兼及中国传统学问,从《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课本开始,直到四书五经。《圣经》不仅是必修课,常常占有压倒一切的位置。此外英文也是贯穿始终的必修课。
1860年至19世纪末,这类学校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有:1864年在北京创办的华北第一所女校贝满女学,即后来的贝满女中;1871年在福州创办的毓英女学;1881年在上海由原文纪女塾和裨文女塾合并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1888年在广州设立的塔道女中;1890年在上海设立的中西女塾,即后来中西女中的前身。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女校,是1898年上海的中国女学会书塾。
20世纪以后,中国各大城市均设女校,包括中学和大学。50年代以后,女子大学取消。60年代文革开始,所有女中均改为男女同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