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70寿辰与共和英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寒山(英国)

“童话般天真纯洁的婚姻”,曾被英国人称道。全球有7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豪华的婚礼
今年4月2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家人及几个亲近的朋友在她的私宅,——用她自己的话讲是“宁静地”——度过了70岁生日。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女王客人名单上少了一位客人:女王的儿媳黛安娜王妃。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从1952年加冕登基至今44年,是自从上个世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在位最长的英国君主。较之100多年前的老祖宗时代,伊丽莎白二世治下的当今帝国已今非昔比,英国已从维多利亚女王全盛时的世界头号帝国,衰退成今天欧洲的二等发达国家。非但世界霸主的交椅让位于美国,就是在欧洲,英国也开始捉襟见肘。1995年,英国的国民总产值(GDP)和人均收入均落后于意大利。在这种时候,作为英国君主立宪制象征的国君——伊丽莎白二世自然成了公众舆论注目的焦点之一,而有关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讨论也因英国皇室最近几年接连不断的离婚案而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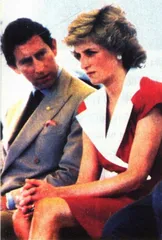 不过伊丽莎白二世是幸运的。她当任英国国君完全得福于她的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温莎公爵。1936年,二战的凶兆笼罩在欧洲上空,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作出了惊震世界的退位声明,以求得与他相爱多年的辛普森太太结婚。辛普森太太是美国人,已经离过两次婚。按照英国王室规矩、法律及英国国教习惯,在位君主不得娶离过婚的女人为王后。爱德华八世因此而让位于其胞弟——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
不过伊丽莎白二世是幸运的。她当任英国国君完全得福于她的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温莎公爵。1936年,二战的凶兆笼罩在欧洲上空,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作出了惊震世界的退位声明,以求得与他相爱多年的辛普森太太结婚。辛普森太太是美国人,已经离过两次婚。按照英国王室规矩、法律及英国国教习惯,在位君主不得娶离过婚的女人为王后。爱德华八世因此而让位于其胞弟——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
爱德华八世取爱人舍江山这件事,后人褒多贬少。在英国以外的社会中,人们津津乐道于其中的人文意义,随着大众文化的加工,此事常引为爱情至上的象征。但在当时的英国,却几乎酿成一场全国政治危机。举国上下,无不为国家无君主而伤心,悲哀,气愤。这种情绪化的国民态度终使包括英国政府、议会、皇室及英国国教在内的英国当局斥温莎公爵及辛普生太太于英国大门之外。温莎公爵及爱妻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一起踏上英国本土。
英国皇室爱德华退位蒙上的阴影直到二战爆发后才始褪去。一半因为彼时举国上下都忙于与德国开战,另一半得因于当时接替温莎公爵的乔治六世的妻子,现任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老伊丽莎白皇太后。仓促之中登上英国国王宝座的乔治六世,天生性格平平,身体羸弱。当时伦敦每天遭受德国飞机空袭,又有V1、V2飞弹袭击,就连白金汉宫也未能幸免。皇室尤其是王后及两个年幼公主的安危,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话题。有人向邱吉尔提议,让老伊丽莎白王后带上小伊丽莎白及玛格丽特两位小公主到加拿大避难。可是老伊丽莎白王后执意不离开乔治六世。在把两个孩子安顿到乡下去后,老伊丽莎白王后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无数饱受空袭之苦的伦敦市民宣布,她将伴随乔治国王,不离开伦敦,将与英国共存亡。这种精神鼓舞了英伦三岛上广大军民迎战纳粹德国,也赋予了老伊丽莎白王后国母的地位。
1952年,乔治六世逝世,小伊丽莎白仰仗着英国公众对老伊丽莎白王后的爱戴和崇敬,登基就任新女王,成为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二世年轻、勤奋,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浦亲王,二战时曾服役于皇家海军。为重建皇家形象,几十年来,伊丽莎白二世深谙“无为而治”的精要,平时给人以沉稳持重印象,尤不轻易发表见解。除开撒切尔夫人外,伊丽莎白二世与她历任首相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和梅杰的关王与和她同岁的撒切尔夫人的关系则一直比较冷淡。据说有一次在每周例行公事的谒见女王时,撒切尔站着向女王汇报,因为女王没有让她坐下)。几十年来,女王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慈祥和蔼的形象,她平素穿戴以朴素出名。当其他王室成员纷纷穿着昂贵的时装出入于社交场合时,女王则经常围一头巾出入于皇家场合。
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25年银庆大典,在伦敦曾造成万人空巷的景观,随之而来的是举国上下对王室信心的高涨。王室的深入人心以1981年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结婚达到高峰,据称当时世界上有7亿人通过电视观看婚礼。英国人每每谈及就不禁沉浸于这个“童话般天真纯洁”的婚姻神话中。 然而女王这辈的福气好像并没延续到下一代,皇家内部接二连三发生婚变。首先是女王的大女儿安妮公主与其丈夫离婚,开始了姐弟间在婚姻上的离婚比赛。其实,王室中婚姻变化由来已久。早在50年代,女王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婚姻就以失败告终。当时,年轻的玛格丽特爱上了一位二战时的功勋飞行员,但终因双方门户相差悬殊而作罢,玛格丽特不得不嫁给斯纽顿勋爵。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4个孩子这辈,皇室“门户”的纯洁其实已无法保证。经历了50年代末的性解放、60年代以摇滚乐为首的社会通俗文化的流行,孩子们的婚姻都已是打破“门当户对”的自由恋爱。女王大女儿安妮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卫士长,二儿子安德鲁亲王的妻子萨拉婚前是个公关小姐,大概只有黛安娜多少有点贵族的联系——她的继母是个伯爵夫人。然而黛安娜自己在认识查尔斯王子之前是个幼儿园老师。
然而女王这辈的福气好像并没延续到下一代,皇家内部接二连三发生婚变。首先是女王的大女儿安妮公主与其丈夫离婚,开始了姐弟间在婚姻上的离婚比赛。其实,王室中婚姻变化由来已久。早在50年代,女王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婚姻就以失败告终。当时,年轻的玛格丽特爱上了一位二战时的功勋飞行员,但终因双方门户相差悬殊而作罢,玛格丽特不得不嫁给斯纽顿勋爵。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4个孩子这辈,皇室“门户”的纯洁其实已无法保证。经历了50年代末的性解放、60年代以摇滚乐为首的社会通俗文化的流行,孩子们的婚姻都已是打破“门当户对”的自由恋爱。女王大女儿安妮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卫士长,二儿子安德鲁亲王的妻子萨拉婚前是个公关小姐,大概只有黛安娜多少有点贵族的联系——她的继母是个伯爵夫人。然而黛安娜自己在认识查尔斯王子之前是个幼儿园老师。
一方面,巨大的社会变化在不知不觉影响着王室内的一切,王室本身也在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王室的窥视,已使王室的隐私越来越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传媒对王室的兴趣变得日益“病态”。因王室的存在,豢养了一批专事于报导皇家新闻的“royal correspondents”(皇家记者)。专门捕风捉影的所谓的皇家观察家(royal watcher)热衷于任何一个有关王室成员私生活的爆炸性镜头,以此换取金钱。
传媒对王室私生活的“侵入”,给王室主要成员的公共生活带来很大压力。在这种媒体高压下,王室的抱怨有时也能博得公众的同情。前段时间,伦敦《星期天泰晤士报》刊登文章,称女王与爱丁堡公爵50年婚姻也未必都像外界想象的幸福,暗示爱丁堡公爵可能有过外遇,只是女王采取“无为而治”,施用于家政“视而不见”。文章刊出后受到不少公众的批评,但公众的同情毕竟也会像资源一样耗尽。
1992年,用女王自己的话说是“灾难的一年”。3月,女王大女儿安妮公主正式与其丈夫离婚。6月,一本获得黛安娜王妃许可的书中首次披露黛安娜与查尔斯11年婚姻的不幸实质。据该书作者宣称,黛安娜曾有过5次自杀企图。8月,英国法院禁止在英刊出一幅女王二儿媳约克公爵夫人的照片。该幅在法国巴黎曝光的照片披露了女王二儿媳在海滩上与她的私人财务顾问、德州富翁吮脚趾的亲昵镜头。12月,白金汉宫证实,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正式分居,从而提前给这桩令无数英国人为之倾倒的婚姻划上了句号。
同年11月,一场罕见的大火把温莎皇宫——女王的伦敦郊外宫宅——烧得目面全非。事故起因于电线工不慎煤气着火,修复温莎王宫的费用估计逾上千万英镑。按照常规,这笔开销由英国政府拨专款,而这意味着是纳税人出钱。本来,王宫遭灾,理应受到社会的同情,可一家报纸登出一条“她(女王)毕竟是世界上最富的女人”的标题,引发了传媒到底谁该出这笔钱——是纳税人还是女王——的争论。
为了扭转每况愈下的王室形象,女王不得不宣布她将正式纳税,从而结束了英国税制上沿袭几百年的君主为唯一免税人的历史;另外还准备向公众开放白金汉宫,每年的门票收入(估计可达数百万英镑)用来补贴温莎王宫的修补费用。 尽管有这些心烦意乱的王室内部事务,但迄今为止,伊丽莎白二世的地位仍然没受到根本动摇。除极少数偏激分子外,大部分英国公众还是认为女王是位称职的君主。英国国民性中天生的保守性,使大部分国民目前仍拥护君主制。他们认为,1688年英国君主、保皇派与议会派达成妥协分权,英国从此有了300多年的太平无内战,政治改良引发社会良性启动,历经工业革命后,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君主制功不可没。赞成君主制的人说:任何一个像君主王权这样的国家机器给社会带来300年的太平无事,非但有它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社会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珍惜它。况且,君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已经不再是王室几个成员之间的事。
尽管有这些心烦意乱的王室内部事务,但迄今为止,伊丽莎白二世的地位仍然没受到根本动摇。除极少数偏激分子外,大部分英国公众还是认为女王是位称职的君主。英国国民性中天生的保守性,使大部分国民目前仍拥护君主制。他们认为,1688年英国君主、保皇派与议会派达成妥协分权,英国从此有了300多年的太平无内战,政治改良引发社会良性启动,历经工业革命后,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君主制功不可没。赞成君主制的人说:任何一个像君主王权这样的国家机器给社会带来300年的太平无事,非但有它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社会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珍惜它。况且,君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已经不再是王室几个成员之间的事。
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人还以历史上诸多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的例子说明,大部分这种转变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流血内战。保守的英国人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法国产生出了国王的断头台、慷慨激昂火药味浓重的《马赛曲》。保守的英国人问,到底是流血的内乱对社会、民众好,还是像我们英国这样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好?
英国国民性中的保守及对政治家的天生怀疑态度使得英国人常质疑政治家们的动机。这些英国人说,政客们拼命是为了再度当选,我们选民如何去相信政治家所说的是百分之百为选民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党利益及自己的再度当选?我们英国人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世袭的君主,因为她(他)不属于哪个政党。这种貌似不合理的世袭君主的存在,却保证了政治利益上的中立性。
虽然站在拥护君主制对立面的持共和观点的人数近几年快速增长,但这派阵营从历史上看从来是少数。人们记忆中上次公开辩论共和制还是在1936年爱德华退位事件,当时英国下院专门辩论,结果赞成弃君主立共和的总共才5票。从此以后,公开赞成共和的人在议会中从未兴起过大风浪。
在持共和观点的人看来,一代王朝,君主本来就是一个社会象征,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由。目前的英国温莎王朝(源自现英国王室的家姓温莎)确切点说也不过是1917年放弃德国祖姓而“发明出来的”。持共和观点的人认为,王朝要能适应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君主的作用已非同从前,王室的功能已转变成公共象征性,更多的是君主依赖于社会,因此,现代社会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女王?在90年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公共象征的王室及君主,为频频家丑所累,则君主/王室的正面社会楷模作用已荡然无存。在现代社会里,君主得以存在的基石是其在社会上的拥护程度。当现在的君主已经从一个国家的象征变成一个“肥皂剧”或“肮脏玩笑”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拖住君主不放?
持共和观点的人还以一个变化的社会因素说明君主制正在变得与现代社会不相关。目前持保皇思想的以上了年纪的人居多,那是因为老一辈还有二战时对王室的怀旧情绪,而对新一代英国人来说,王室已和现代生活越来越毫无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的去除只是早晚问题。
于是大家来欢呼一个共和英国的诞生?问题没这么简单。共和英国怎么产生?通过什么机制把现有君主王权废除?又用什么去取代目前君主的作用?一连串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大选将近,对英国几大政党讲,任何有关废除君主的建议都无疑于政治自杀,会马上被政治对手用作杀手锏。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前不久斥责他的一名重要阁僚攻击查尔斯王子的言谈为愚蠢之举,并让该名议员作出道歉。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政党政治对温莎王朝这块最后的肥肉是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1994年,工党负责内部事务的发言人杰克•斯特劳已直言不讳地提到对英国君主需“重新定义”。据普遍认为,在现有工党议会议员中,约有半数以上是铁杆共和分子。即使是在保守党内部,也有不少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现代撒切尔分子,视君主制已不适合一个朝气蓬勃的、21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而这些无疑与公众舆论对皇家的不满构成推波助澜的反君主制倾向。当然,现任女王仍拥有公信力,所以只要女王活着,持共和观点的人还有最难攻的一个城堡,而女王家族中女性成员素有长寿基因,维多利亚女皇就活到83岁,女王的母亲老伊丽莎白王太后96岁仍健在。一旦女王去世或退位,则王室的香火就难保了。 据英国最力倡共和的斯蒂芬•哈色勒教授认为,走共和制有3条途径可供选择:一条是长途,一条是短途,还有一种是走欧洲途径。
据英国最力倡共和的斯蒂芬•哈色勒教授认为,走共和制有3条途径可供选择:一条是长途,一条是短途,还有一种是走欧洲途径。
长途涉及面最广:包括全面体制宪政改革,而废君主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唯一没有一部书面形式宪法的国家,所以长途形式的改革还将解决起草书面宪法的问题。哈色勒认为这是一条最前途未卜的途径,因为现有法律的每个条款都要斟酌,而这种修宪过程无疑给保皇派以各种机会反击及破坏,所以成功机会很小。
中策是走欧洲路,这比较适合激进派的口味。只要照搬一部泛欧化的宪法,则现任女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弃——因为在英国与其他欧洲各国走向超级欧洲合众国的过程中,女王肯定是个牺牲品。
但是像大多数诚心诚意的共和派分子一样,哈色勒认为还有一条上策可走。因为英国没有一部书面宪法,议会实质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议会颁布一个法令,就可终止君主的权力。当然这要事先征得女王的同意。但这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女王的签字只是个形式而已,事实上女王从未否决议会通过的法令。
接下来的,首先是如何处置现存的女王及皇家其他成员。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倾向于由国家给予君主及皇家一定的赔偿。废位后的君主及皇家直接成员仍可住在现有家庭,并享有普通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君主及皇家“拥有”的巨大房地产业,大部分将归还国家,这包括著名的白金汉宫。而数以万计的珠宝王冠,处理起来则会非常复杂,因为其中有不少仅仅用于正式场合,比如加冕仪式用的王冠上镶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这很难说到底是属于女王个人的,还是该属于国家。而许多目前属于女王的艺术藏品则是来自于外国元首。共和派人士说,这些东西也应该收归国有。
当然更加严肃的问题是:女王没有了,谁来行使这哪怕是礼仪性的一国之主的功能?若细究起来,这个问题比想象的复杂。因为现在女王的权力,虽然大部分是象征性的,但按英国法律,却拥有一种称为“保留权力”的特权。从理论上讲,这种保留特权使得女王可以在全国紧急状态时,行使解散议会,而以“枢密院政令”形式施政。这种保留权力也使得女王成为唯一可以防止首相大权独揽的人选。若废除女王这些特殊权力将由别的机制来取代。在许多国家,这些权力由议会议长行使,或由总统行使。问题是,在许多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总统、议长也是政党政治的产物。
走向共和还会产生一些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比如现行流通货币上的女王像,护照、政府公文抬头上的女王徽记,都要用别的代替。议员、政府公务员在宣誓就任时的誓词也要改动,现用誓词是对女王效忠,这是基于所有的人都是女王的臣民:政府是“女王陛下的政府”,政府各部部长正式称呼也是“女王陛下某某大臣”。一旦变成共和了,这些都要改,因为在共和制下,一个基本假设是,大家都是“公民”,因而,以前对君主的效忠就变成对社会中其他公民的效忠。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都是咬文嚼字的话,则有些字面游戏的处理,就显得左右不是。“皇家”两字的使用,就是一例。“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邮政”和“皇家造币局”无疑都要改名。但是怎么处理学术、艺术方面的团体机构带“皇家”二字呢?有些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名字了,比如皇家学会、皇家歌剧院。若是如激进的持共和观点的入主张的那样,则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将更名为大不列颠科学院。这样一改,顿时丢去了与牛顿、达尔文这样著名历史人物联系的历史感。没有了女王,英国国歌的歌词要改,荣誉授勋制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现存的荣誉制下的爵位、勋爵等封号将最终变成诸如“共和国勋章”、“人民勋章”等等,这也使得保皇派人士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历史。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都是咬文嚼字的话,则有些字面游戏的处理,就显得左右不是。“皇家”两字的使用,就是一例。“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邮政”和“皇家造币局”无疑都要改名。但是怎么处理学术、艺术方面的团体机构带“皇家”二字呢?有些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名字了,比如皇家学会、皇家歌剧院。若是如激进的持共和观点的入主张的那样,则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将更名为大不列颠科学院。这样一改,顿时丢去了与牛顿、达尔文这样著名历史人物联系的历史感。没有了女王,英国国歌的歌词要改,荣誉授勋制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现存的荣誉制下的爵位、勋爵等封号将最终变成诸如“共和国勋章”、“人民勋章”等等,这也使得保皇派人士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历史。
在这场君主对共和的争论中,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仍要触及:这些改来改去,都是为了什么?英国人究竟会失去什么?英国一旦变成了共和制,到底与一个女王下的英国有多少差别?一句话,英国人是否真的想要拥抱一个共和英国?
共和派坚信一个共和英国将从根本上消除英国几百年来的等级社会,他们认为在共和制下的英国,大家从臣民变成共和的公民,成为社会日常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保皇派则坚信,所有这一切走向共和的道路,都可能是政治、社会动乱的开始。牛津大学的持保皇观点的巴格达纳坚持,英国的君主制是英国人最好的民族象征,是英国现行议会政治、民主的最好的守护神。在赞成君主制的人看来,废除一个伊丽莎白二世,以一个撒切尔(或梅杰)总统取而代之,不见得给英国带来任何明显的好处。共和制也不一定就代表着现代的社会的进步。
从这场共和对君主的争论中,可以得出结论,未来英国的君主及君主制的前途将系在公众的情绪上,将随着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展的顺利与否而变得更加微妙,更加错综复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国际政治这个90年代世界大森林中,英国的君主及君主制无疑已成为一个濒危动物了。当王室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时,其意味早就被粗暴地改写过了。至于像欧洲土地上的女王和君主制能否作为一种象征,90年代再安泰生存于21世纪,人们将拭目以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欧洲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