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火起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张晓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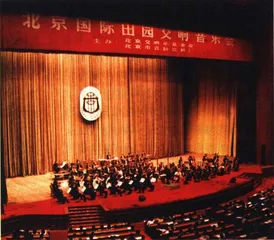
北京交响乐基金会拥有中国唯一的一辆流动舞台车 “为此我们已等了11年”
1985年秋,施今墨老先生的儿子施小墨把一张祖传秘方无偿捐赠给了同仁堂制药厂,这张秘方价值2万元。随后,同仁堂扣除税金,把剩下的1.5万元转交给北京市卫生局的有关人士。同年9月底,北京市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以1.5万元启动资金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立。
11年后,中医药基金会秘书长张革在谈到基金会远景时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基金会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后,将建立一座中医药城。城中将以博物馆的形式展示中华民族历代中医药的杰出成就,把散于各处的珍贵中医药文献集中起来,为专业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便利。另外,设立一定的床位,使分散在各地甚至埋没于民间的当代中医药最优秀成果汇集一堂,并应用于临床。中医药城将建立自己的种植、养殖场,配备最先进的科研设备,为改变国内看病拿方,却到国外中药店才能买到药的现状出一份力。
设想有了,基金会甚至物色好了昌平县高尔夫球场附近的一块地,那里环境幽雅,利于休养,交通也很便利。而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为此已等了11年。
这项卫生部门未想到,即使想到也无力实施的工程,据估算约需5000万至1亿美元的投资。北京振兴中医药基金会目前帐上有10万元人民币。11年的时间基金增值还不到7倍,照这种积累速度,恐怕中医药城只能是人们头脑中一张美丽的蓝图。张革并未指望10万元的基金能产生奇迹,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的大公司大财团。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项目宣传出去,这就需要印制一些十分精美的宣传册。这笔钱由谁来出呢?张秘书长为此已联络了不少企业,可是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张秘书长说,“只能慢慢做工作。”
创办初衷是想靠基金会的招牌吸引外资,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可除了举办过几次义诊,奖励过北京中医药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及对北京部分受灾郊县进行过支援外,11年中大部分时间基金会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没有钱就办不成事,办不了事就不如摘牌子。”产生这样的想法倒也在情理之中。基金会溯源
“基金会”是一个道地的舶来品。美国人早在18世纪就有了信托基金,我国的基金会历史只能追溯到本世纪初。1915年一批留美中国学生组织“中国科学社”,20年代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大学设立“汉卿奖学基金”,30年代上海实业家顾乾麟先生建立“叔频公奖学基金”,成为我国基金会的先行者。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基金会在我国呈现一片空白。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创立,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的基金会事业,还引发了持续10余年的“基金热”。据1989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立各种基金会214个,其中全国性的基金会33个,地方性基金会181个。而各地利用救灾扶贫款建立的救灾扶贫基金会到1986年就已达6275个。
“基金热”的兴起始料未及,当时国家没有建立规范的审批程序和相应的管理办法,一哄而上的基金会中滥竽充数者不在少数。最突出的问题是,钱没用在该用的地方,相当一部分基金会用募捐的资金投资办企业获利。
1988年国务院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基金会的宗旨应是“通过资金资助推进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并禁止基金会经营管理企业。经过一番整顿,1995年全国的民间基金会不足千家。生财有道
规范的基金会运作方式应是使用基金的增值部分,而不动用基金本身,这样才能确保基金安全与稳定。这就要求基金会的经营者生财有道,理财有术。
1995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两地同时颁发的各项诺贝尔奖金合计达720万克朗(约合110万美元),从而达到了自1901年发奖以来的最高值。同时诺贝尔基金会的基金也由创办时的3300万瑞士克朗达到现在的18亿克朗。
诺贝尔基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50年代由于只进行政府债券投资,基金会只能靠吃老本维持。直到1989年,奖金额也仅有300万克朗,约合46万美元。但是1989年成功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进入90年代在股票债券等领域的大胆运作,使得近年基金会年经营收入一直保持在1000万美元。
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必须报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这意味着基金会的基本属性为金融性社团。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前任秘书长沈晓丹认为,基金会的运营不仅含有社会公益性因素,还有金融经营的性质。
1988年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成立时,中国科协投入300万人民币预算外收入。6年后,基金总数已达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科协所属基金有1000多万元人民币。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的初衷是要成为综合性以奖励为主的“中国诺贝尔基金会”。为此,沈晓丹算了一笔帐。诺贝尔基金会百年基金总增幅为50多倍,年递增率为4—5%,科技基金会创办6年基金总数年递增率为60%,自身基金年递增率为20%。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要达到诺贝尔基金会的实力,以60%的年递增率增长还需8年,以20%的年递增率增长还需36年。
基金的积累是基金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虽然政策上允许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基金会的经营者又有多少人是懂得经营之道呢?
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也想通过金融投资使基金尽快增值,但基金会从秘书长到理事,全部是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对股票、债券可谓知之甚少。1993年从熟人那里得知天津一家房地产公司不上市股票前景看好,便找门路认购了5万股,一下子就投入了全部基金的80%,即8万元,可直到现在还没收获1分红利,8万元被套在那里,进不是,退无门。现在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就只能由剩下来的2万元的存款利息支付。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基金会的存款可按同档次储蓄存款利率执行。可即使按今年4月1日调低存款利率前的利率计算,2万元一年可仅得利息2196元。这笔钱甚至不够支付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注册登记处处长王杰介绍,北京市现有基金会40家,其中50%的基金仍保留在注册登记时的水平。 1988年对基金会进行整顿,一大批“基金会”被清除,但由于我国基金会大多带有官方半官方色彩,保存下来的基金会也并不完全符合规定。例如《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二条要求基金会要有人民币10万元(或者有与10万元人民币等值的外汇)以上的注册基金,去年有关部门又规定新成立的基金会除10万元注册基金外,还应有至少200万元的流动资金。北京市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以1.5万元注册基金保留至今,而北京市交响乐基金会注册基金为零,目前帐上也只还有不到1万元。
1988年对基金会进行整顿,一大批“基金会”被清除,但由于我国基金会大多带有官方半官方色彩,保存下来的基金会也并不完全符合规定。例如《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二条要求基金会要有人民币10万元(或者有与10万元人民币等值的外汇)以上的注册基金,去年有关部门又规定新成立的基金会除10万元注册基金外,还应有至少200万元的流动资金。北京市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以1.5万元注册基金保留至今,而北京市交响乐基金会注册基金为零,目前帐上也只还有不到1万元。
启动基金少必然会影响到基金会开展工作,但这并不能成为许多基金会名存实亡的全部原因。民间基金会研究专家沈晓丹认为除了广开财源,严格的内部管理也是基金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们不妨做一下横向比较。美国资产超过亿元的大基金会不过占基金会总数的0.5%,资产在10万元以下的基金会占36.8%,在1万美金以下的小基金会仍有2910个,占基金会总数的10.5%。而这些小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也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事实表明,美国同行也并不都是像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这般实力雄厚。相当多的基金会仍要为筹集基金而四处奔波。筹钱是门学问,花钱更有讲究。
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启动基金300万元,这在我国基金会中可算得是财大气粗的一家。但当时的秘书长沈晓丹却在基金会章程中明文规定:“基金会的办事机构开支由基金会的办公费解决,基金会办公费不能超过当年收入的5%。”这一比例比国际上通行的办公提留比例还要低5个百分点。勤俭持家、艰苦创业在沈晓丹这里绝不是一句空话。基金会刚刚成立时,他们甚至把一个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一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更多的钱用在刀刃上,同时也才能有更多的积累。
目前我国大多数基金会都属于筹款型基金会,但是相当多的基金会运用基金时忽略了积累。有资料表明,美国1988年当年66.6亿元的资助款有74.4%来自当年的受赠款,而大部分基金会的受赠款都大于其资助款。按国际上通行的原则,基金会当年获利或募集的基金,一部分用于专职机构办公费用,一部分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除这两项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基金积累,不能全部花光用光。
北京市交响乐基金会成立至今已近10个年头,活动办了不少,但按其负责人的说法是“现买现卖”,要来一笔钱,办一笔钱的事。去年去广州主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平万岁交响乐音乐会,预算为2.5万元,企业赞助3万元,只剩下5000元。而这5000元在基金会看来也就算不得钱了。直到现在基金会负责人为了找人赞助而疲于奔波,为了基金无法增值而焦躁不安。
事实上,虽然交响乐基金会帐上只有不到1万元的现金,但是他们却拥有中国唯一的一辆流动舞台车,现在就停在总政歌舞剧团宿舍大院外。今年五一节,基金会利用这辆舞台车为筑路工人办了一台歌舞演出,公路局为此免掉了舞台车全年的公路养路费,算是变相赞助。但是流动舞台车要流动起来,否则停在路边上,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辆集装箱运输车。
崔立珍退休前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基金会审批工作,她十分注重的一点是基金会法人代表“有没有经营这个社会团体的能力”。这个“能力”绝不仅指有没有经济头脑,更重要的是有无奉献精神。基金会的宗旨决定了它不同于公司、企业,其经营者可以藉此发财。把目光都集中在钱上的人办不好基金会。
对此沈晓丹深有同感。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专职机构工作人员从最初由科协出工资到现在有100万元的保险基金,这一切沈晓丹可以自豪地说全部来自5%的提取费。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几年来为希望工程募集了几亿资金,而该基金会法人代表在谈及管理如此大规模基金的感受时,用了4个字:“如履薄冰”。至今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及办公费仍由团中央支付。而规范的基金会运作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办公费。青少年基金会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沈晓丹在1994年辞去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一职。第二年这个曾被誉为“中国科技界最大的民间基金会”却发生以常务副秘书长为首的受贿案,3名处级干部参与合伙侵吞基金约百万元的重大犯罪行为。该常务副秘书长年方40,有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位,有美国进修的经历,调入基金会后被提拔为司局级干部。去年8月被捕时,已查实的贪污款达78万元。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他不仅自毁前程,也给这个在中国科技界颇具影响的民间基金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从第一家基金会诞生,基金会在我国已存在了近20年,但是直到今天基金会的精神与意识并未深入人心。其实我们有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当杨晓霞病魔缠身时,无数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可晓霞病愈归家,她却留给了人们一个难题,大笔剩余捐款该如何处理?倘若有一个为公众所信赖的特种医疗基金会,这个问题也就可迎刃而解。
从第一家基金会诞生,基金会在我国已存在了近20年,但是直到今天基金会的精神与意识并未深入人心。其实我们有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当杨晓霞病魔缠身时,无数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可晓霞病愈归家,她却留给了人们一个难题,大笔剩余捐款该如何处理?倘若有一个为公众所信赖的特种医疗基金会,这个问题也就可迎刃而解。
有资料表明,从1981年到1989年美国新成立的仅资助型基金会就有1620个;1988年日本有各类民间基金会11781个,到199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229个。而我国自《基金会管理办法》公布实施至1993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全国性民间基金会仅40家。
一方面我国的基金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现存的基金会又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江介绍,1995年文化局只有50万元活动经费,根本无法满足其工作需要。而文化局下属7个基金会,除少数经营较好外,大多数是在勉强维持。
基金会发展缓慢,除受基金会经营者自身素质限制,社会缺乏基金会发展壮大的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市振兴中医药基金会早在1987年就与香港永安集团、德国克洛克那公司、香港美丽华旅行社就一笔3000至5000万美元的投资密切接洽,如此项目谈成,将在北京落成一座仅次于夏威夷国际体检中心的第二大国际体检中心。在签定了初步意向书后,主管单位一纸“此项目暂不施行”的文件,使基金会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
我国的民间基金会诞生和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管理模式在基金会成立之初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基金会作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必须要走经费自立,工作独立的道路。这已成为我国绝大多数民间基金会的当务之急。
80年代,日本新设立的170个资助型基金会中,有65%是由企业出资或由个人和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而由企业出资办基金在我国几乎还是一个空白。不仅如此,许多基金会在向企业筹资时,大多被礼貌地回绝。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相关法律中,都明文规定,企业把当年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社会公益团体,是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这种税收制度营造了资本家宁愿向社会公益事业投资的环境。例如日本的继承税规定,遗产金额的1/3乃至1/2将被政府按继承税抽走,经二三次继承后,原遗产金额几乎全部交了税
1988年《管理办法》出台时,并未做此规定。同仁堂在向中医药基金会捐赠时还不得不先扣除5000元税金。1994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6条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应纳税所得额3%之内部分,准予扣除。”这或许可以预示着由企业、公司或集团捐资设立的基金会将会是我国民间基金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新闻媒介报道了宏志班孩子们的感人事迹后,宏志班的老师收到了一笔笔资助某个孩子上学的捐款。这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1995年4月,中国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考察非营利机构。深有感触的一点是,美国有一家慈善信息局,专门评估公共筹款机构和服务机构的工作成效。他们拟定了9条评估标准,定期对非营利机构进行评估,每个季度出一份评估结果,而捐款人往往根据该机构的评估结果来决定捐赠给那一个非营利组织。
我们的基金会目前还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而这造成了许多募捐人的茫然,把钱交到哪里呢?或许交给最需要它的人手中才最安全。从个体行为来看,这当然最直接最有效,而当整个社会都如此行事,又必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现代慈善事业不同于传统慈善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善行,而是社会化、组织化的行为。而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则担负着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图片由北京交响乐基金会提供) 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