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呼唤大“王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阿计 1995年,北京市各级行政机关实施各类行政处罚达1千万人次,平均每个北京人被罚一次。行政处罚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1995年,北京市各级行政机关实施各类行政处罚达1千万人次,平均每个北京人被罚一次。行政处罚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从1990年起,国务院法制局就开始研究行政处罚条例,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的法律责任制度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规章,你小心地往前走
各级国家机关能够设定哪些行政处罚,即行政机关遇到一种新的违反秩序的行为,能够独立地做出什么处罚,这在立法学上称作设定权,又叫“创设”。在社会生活中,设定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然而,长期以来,正是由于这项权力的权限不明,缺乏制约,直接导致了今日中国在行政处罚方面的混乱。
国务院法制局曾经进行过几次特别调查,结果令人深思。
对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川、辽宁、宁夏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7省市在1994年共发布地方性法规199件,有97件创设了行政处罚,约占50%,其中,有25件创设的行政处罚超出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处罚种类。在97件创设行政处罚的地方性法规中,有95%规定了“罚款”、“没收财产”、“没收所得”等财产处罚,有38件规定的罚款数额超过了1万元,此外,还有3件地方性法规竟然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身处罚。
7省市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亦是令人疑窦丛生。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这意味着,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制定规章,但必须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但7省市约有半数以上的规章创设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完全是各地“一厢情愿”的创造。据统计,1994年,七省市发布的大量规章中,有半数以上即120件创设了行政处罚,其中,只有19件有地方性法规作依据。在难以计数的罚款名目中,有的罚款额定到了10万元,最高的达到20万元。罚款的计算标准也是五花八门,各出奇招,比如,某大城市有一个有关公共场所用字管理的规章规定:对使用不规范文字的,按每日每字100元处以罚款。
国务院法制局还对7个部级机构发布的规章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7部门1994年发布的95件规章中,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而自作主张、自行设定行政处罚的有33件,占总数的35%;其中,有2件规章所涉及的管理问题已经由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予以明确规定。但具体部门却觉得不过瘾,重新制订规章,增添“加码”处罚的条款。在这些规章中,有一件规定的罚款最高额甚至达到了100万元。
事实证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不明确,行政责任制度就不能走上正常轨道。因此,中国的立法者们在制定行政处罚法的过程中,着重要解决的就是确立不同级别规则的行政处罚设定权。 法律作为最高效力的规则,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作为效力稍次一些的规则,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作为效力更低一些的规则,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这些立法思想和原则,在立法者中并无歧议。唯独谈到效力最低却又花样百出、名目最乱的各级规章时,对于到底允不允许规章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立法者们各持己见。
法律作为最高效力的规则,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作为效力稍次一些的规则,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作为效力更低一些的规则,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这些立法思想和原则,在立法者中并无歧议。唯独谈到效力最低却又花样百出、名目最乱的各级规章时,对于到底允不允许规章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立法者们各持己见。
一些立法者们坚决主张:绝不能允许规章创设行政处罚!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立法把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去执行。而规章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政机关不能自己给自己树一个权力,再自己去执行。何况,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通过都有严格的民主程序,唯有规章是行政机关一家说了算,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在行政处罚上最乱七八糟、最“无法无天”的就是规章。
另一些立法者们则针锋相对:必须允许规章创设行政处罚,否则,社会生活管理就会陷于瘫痪。道理很简单,尽管中国已经有了200多件法律、800多件行政法规、近4000件地方性法规,可这些法律法规仍然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全呼呼地蹦进我们的生活中了,不依法管理行吗?
毫无疑问,这场法律纷争的症结就在于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历史性困惑,最终,《行政处罚法》作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选择:规章可以享有最低程度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即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的罚款,罚款的限额应由各上级部门规定。
一位资深的法学家说:《行政处罚法》通过后,需要对浩翰如海的地方性法规和各级规章重新修订、清理,摒除那些与法不符的处罚名目,这乃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十顶大盖帽与一顶小草帽的困惑
中国老百姓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好端端地在大街上走着,不经意地扔了一张废纸或吐了一口痰,就有一个小脚老太太或老爷子,现身在你面前,罚款!你也许心里直犯嘀咕,凭什么把罚款交给他们呀?他们也算执法者?谁给他们的权力?谁又监督他们执法?
谁有权实施行政处罚是保障法律严肃性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国行政处罚方面的一大弊端恰恰是执法主体的混乱。行政机关在上街罚人,事业单位在上街罚人,企业在上街罚人,社会团体在上街罚人,一些莫明其妙的组织和个人也在上街罚人,真可以说是大盖帽满天飞,红袖匝到处舞。
一个卖早点的小贩因为摊点摆错了地方,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竟连续遭到物价、工商、税务、交通、防疫、环卫等8顶大盖帽的“轰炸”,一口气被罚了8次!
一些印着“此处不得停车,违者罚款”的警告牌堂而皇之地到处悬挂,细看落款却是“某某公司”、“某某餐厅”、“某某学校”……更加荒诞的是,这些“公司”、“餐厅”、“学校”还常常派出个闲来无事的离休人员,随便弄个红袖匝,描上些“检查”、“纠察”之类的威慑性字样,在门口溜来溜去,瞅空就理直气壮地向路人要起罚款来。
面对铺天盖地的大盖帽和红袖匝,老百姓叹出辛辣的顺口溜:一曰:“满大街都是大盖帽,十顶大盖帽罚一个戴草帽”,那“戴草帽”的,自然是平头百姓。
按理说,行政处罚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行政机关却有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将少兵寡,逼得许多行政机关只得委托外界的力量帮助执法,特别是在农业、卫生、交通、劳动等管理范围宽广的领域,这种委托执法的情形就更为突出。
上海,非行政机关的执法队伍占到50%左右;北京市现有54个执法部门,其中20个部门是事业编制,占37%,还有6个部门是行政和事业混合编制,占11%。全国交通部门的执法人员约26万,基本上都是事业编制;全国卫生系统每天有25万人上街执法,真正属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不过几千人,以查痘猪肉为例,一个偌大的城区往往只有一家卫生局,即使从局长到收发室老大爷全军出动,恐怕忙乎一上午还查不完一个农贸市场,那老百姓还吃不吃肉了?真正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的,还得归功于众多受委托的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
为了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不良局面,一些地方还尝试了“综合执法”,由政府建立综合执行机构,几个机关联合检查,或者把诸多行政机关的执法权集中起来,由一家集中行使。在青岛滨海路的一座繁华站桥,短短几百米的路段,曾经有11顶“大盖帽”在揪人罚人,老百姓怨气很大。后来实行了巡警制度,干脆由公安一家出面,治安秩序、乱设摊点、无照经营、乱倒垃圾、市政面貌……无所不管,其余“大盖帽”则统统撤退。如此一来,老百姓的心气顺了,行政效率提高了,政府形象也大为提高。如今,施行“综合执法”的巡警制度已经在许多城市流行开来。
“委托执法”和“综合执法”滋生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推动了中国行政执法的实践,然而,它们也有亟需克服的弊病:一些受委托的执法人员水平低下,滥用执法权;一些综合执法的人员也并不熟悉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素质并不“综合”和全面,再加上缺乏其他部门的监督,过分膨胀的权力容易造成执法中的随意性,怎么罚往往是执法人随口敲定,事后缴钱的要多罚些,当面交钱的可以少罚些,愿意私了的还可以再少些,有利的几个部门争着罚,费力不讨好的大家都撒手……
新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既强调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又肯定了“委托执法”和“综合执法”,同时对受委托组织规定了一系列严格条件。听证:公平和效率的抉择
一名出租司机犹豫再三,终于硬撑着堆满一脸笑容,走进了某交通执法队的大门,因为在不许停留的路段停车,他的驾照已给扣了4天,他连续4天来索回驾照,却总无下文。
10秒钟后,这位司机垂头丧气地出来了,这回,那位没收他驾照的交警还是没有把证件上交有关领导处理,还是爱搭不理地让他“再等等”。按说,驾照被没收后24小时内就要作出处理,可司机敢申张这个理吗?
“唉,明天再来一趟吧,硬着头皮也得来呀,不知道还得陪上多少好话?”40出头的汉子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是笔者搭乘一辆出租车时亲身所遇,然而,比这种刁难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以下的场景。
两名执法人员走进一家个体餐馆,表情肃穆地在厅堂里巡视一圈,然后一声不吭地掏出随身携带的苍蝇拍,追击起空中飞舞的几只苍蝇。“啪”!一只苍蝇坠地了,执法者口中立刻蹦出一句:“50”!随着苍蝇们的不断“牺牲”,执法者也不断念念有词:“50、100、150……”
末了,执法者把苍蝇尸首聚拢一处,向餐馆老板摊开了手:“每只苍蝇罚50,一共12只苍蝇,600块!”
这是发生在河南某市的一个真实场景,而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且不说每只苍蝇罚50元的依据令人怀疑,如此简单的执法方式也叫人难以接受。按说,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违法者自觉守法,处罚应当坚持和教育相结合,处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我们哪里看得到半点教育的影子?没有预先的身份表明,没有事前的教育警告,没有文明的执法态度,没有合理合法的解释,一句话,行政管理行为扭曲了,没有管理,只有罚款。
法制的历史告诉人们:法律只有经过具体操作,才能由纸面上的智慧转化为生活中的智慧。在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行政管理中,遇到违法行为,首先要向违法者敬礼,宣布对方可以享有的权利,然后才说明违反了何种规则、应当接受何种处罚。这在法律上叫做“告知”,遗漏掉“告知”程序的行政处罚根本就是无效的。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漠视程序和缺乏程序,加剧了中国行政处罚的乱滥局面。不告知,不教育,上来就罚,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野蛮执法、粗暴执法、欺辱百姓、甚至敲诈勒索时有发生;程序的混乱也造成了处罚的随意性。不仅不向被罚者说明理由,也不允许被罚者申辩,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谁要是敢辩白半句,非得给“上纲上线”加重处罚不可。“敢怒不敢言”,这已经成了遭受不公正处罚后的共同心态,然而,怨怒并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它必然损毁的是一个国家最值得珍视的威信,它必然伤害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弥足珍贵的情感。为了重塑那崇高的威信,为了找回失落的情感,新出台的《行政处罚法》为行政处罚精心设计了3种程序。
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必再搞复杂的调查取证,可以当场处罚,此谓简易程序。《行政处罚法》对此定下的基线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简易程序追求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同时也无形中保证了被处罚者的权益。试想,一个出租司机闯红灯,属于轻微违法,只要不是缺乏必要的理智,他是极愿接受当场处罚的,假如真要来一番调查取证之类,把他耗上半天,他恐怕会为耽误生意而叫苦连天、连连跺脚!
除简易程序可以解决的违法行为外,对其他违法行为要进行行政处罚,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还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查,此谓一般程序。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第三种程序——听证程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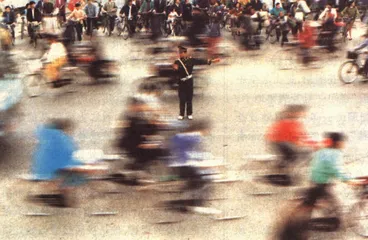 1946年,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确立了听证制度,规定:听证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所享有的权利,听证是正式行政程序的核心,未经听证的任何裁决均为无效”。随后,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日本、法国等都纷纷效仿,听证制度成为行政程序中极为重要的制度。
1946年,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确立了听证制度,规定:听证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所享有的权利,听证是正式行政程序的核心,未经听证的任何裁决均为无效”。随后,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日本、法国等都纷纷效仿,听证制度成为行政程序中极为重要的制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美国的听证制度已经日趋完善,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刚生效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只有197名听证审查官,1972年后,听证审查官改称为行政法官,进一步强化了听证的法律地位,到1990年,联邦政府已拥有1005名行政法官,分布在31个行政机关,其中半数以上在社会保障署工作。
听证,是行政程序法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得最集中的表现:
但听证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费钱费时,它在追寻公平的梦想同时,也可能牺牲了行政效率,加重了财政开支。在美国,行政机关制定规章也可能举行听证会,结果,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为了制定一个关于花生酱的规章,听证会从开始到结束竟达11年之久,记录达7700页,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证人的相互盘问上。有关联邦行政机关为了制定一个关于职业安全的规章,口头听证记录就有8500页,制定规章全部记录竟达25000页。
毫无疑问,良好的行政程序不仅需要公正,而且需要效率。为了既保障公平,又兼顾效率,中国的《行政处罚法》设计了严格控制下的听证程序,只对“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较重的行政处罚可以举行听证。以制度之矛洞穿腐败之盾
这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两件怪事:两年前的一天,笔者在外省采访,搭乘一辆个体小客车,客车驶上一条著名的国道不久,前方出现了一长排被拦截下来的车辆。
客车司机熟练地停下车,带上早已准备好的香烟,恭恭敬敬、满脸堆笑地走到一位交警面前,递烟点烟;又掏出两张“大团结”,在光天化日之下塞进了交警的手里。
那位交警大模大样地把钱塞进自己的口袋,又长长地呼出一串烟圈,然后亲切地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潇洒地一挥手,做了个放行的手式。
司机刚回到车上,笔者就忍不住问道:“你开车好好的,犯什么规了?”
“犯规?”司机一反刚才的小心翼翼,咬牙切齿地说:“说你犯规你就犯规,说你没事就没事,孝敬20元啥事也没有,不然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有一位老乘客插嘴说:“你是第一次跑这条线吧?这个卡子是有名的,车一到这儿,不管有没有犯规,准得给截下来,罚了款连个白条也不开。”
司机接着叹道:“唉,我就曾经给扣过五个小时,想讲几句道理,罚款就从100元涨到了200元,所以我现在也学乖了,车一到这儿,就主动意思意思吧。”
不知为什么,笔者当时油然生出一股豪情,不顾司机的拼死阻拦,径自下车找那位交警评理去了。
当听说笔者是记者后,那位本就警容不正的交警顺手把大盖帽又歪了歪,把敞开的领口又拽了拽,把胳膊袖口又往上卷了卷,然后狠狠地白了笔者一眼:“少管闲事,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老子不怕!上头给了我罚款指标,我完不成任务还罚我呢!我怕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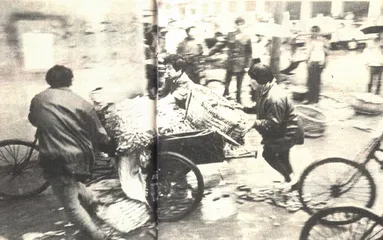 骂完,他再也不理会笔者,只是一遍一遍地挥动胳膊,不管路过的车辆有无过错,统统被拦截下来,然后是一番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识相的不要收据的供上20元“辛苦费”就可以立马开路,要收据能回去销帐的都“罚”到50元以上,那些想论个明白的犟脾气司机就惨了,一位司机被指责车前灯损坏,他当场打开灯以表清白,不料处罚者却强词夺理地说:“现在灯好了,刚才还是坏的,还得罚!”接着,这位倒霉的司机因不听话,罚款的“价码”涨了一倍。
骂完,他再也不理会笔者,只是一遍一遍地挥动胳膊,不管路过的车辆有无过错,统统被拦截下来,然后是一番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识相的不要收据的供上20元“辛苦费”就可以立马开路,要收据能回去销帐的都“罚”到50元以上,那些想论个明白的犟脾气司机就惨了,一位司机被指责车前灯损坏,他当场打开灯以表清白,不料处罚者却强词夺理地说:“现在灯好了,刚才还是坏的,还得罚!”接着,这位倒霉的司机因不听话,罚款的“价码”涨了一倍。
事后,笔者给那位交警的上级部门寄去了控告信,但终无下文。看来,那“老子不怕”的说法果然不是虚言,因为“上头”既然给了他罚款指标,就得默许他无法无天地使用职权,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
在西北某城采访时的遭遇也让笔者久久难以释怀。那是在一个农贸市场内,两名身穿制服的工商执法人员在市场里巡视。在一个卖瓜的摊贩前,他们停下盘问。
“有营业执照吗?”
“没有。”
“罚款!”
“我还没卖钱呢。”小贩恳求道。
“那就罚两个西瓜吧!”执法者抱起两个西瓜转身就走。
不久,在几步开外的一个卖羊羔的摊位前,两位执法者又如法炮制“罚”走了一只羊羔。
半小时后,在市场外的一家小吃店里,笔者又看到了这两名“不拘一格”施行处罚的执法者,他们正敞胸露怀,大嚼那缴获来的红瓤西瓜,而另一“战利品”——羊羔,已经由店里的伙计宰杀完毕,正在褪毛剥皮,准备下锅。
事实证明,执法者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行政处罚的滥乱导致的最严重的恶果就是这种最大的腐败。一些执法部门违反财经纪律,拖欠、截留、坐支、挪用、私分罚款,使本应纳入国库的罚款大量流失,源源不断地流入某些执法部门私自设立的“小金库”,成为“改善本部门工作条件、提高工作人员生活水平”的强大后盾,罚款等于奖金已经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式。
北方某大城市对违反交通法规的司机有个奇怪的处罚规矩:比如司机的单位在A区,他在B区违规后被罚了100元,按说事情已经了结,且慢!B区的交警会“恪尽职守”就把有关处罚情况捅到A区有关执法单位,于是这位倒霉的司机回到A区,又会再一次被罚款,而且是翻了一倍,变成了罚200元,理由是这位司机给A区“丢了脸”!同样道理,B区的司机如果在A 区违规了,A区的交警也会心照不宣地“照会”B区,让这种重复惩罚能顺利进行下去,该大城市共有十个左右城郊区,这种互相配合的罚款,你能算得过来吗?
湖南某市有一个治安整顿办公室,人员都是从有关单位借调来的,为了捞取利益,竟然非法上路拦车乱罚款,从这个办公室成立之日到被上级部门查获为止,43天内共乱罚款8万多元,并任意挥霍了7万元。群众愤怒地说:“治安整顿办成了车匪路霸!”
福建某市一个派出所7个民警“齐心协力”,短短几天内罚了11万元,并全部予以瓜分。
广丰县交警大队为了“创收”,滥罚款,乱收费,处罚单据是自己非法印制的“罚款单”,有时干脆就是打白条。前前后后,他们一共隐瞒截留了19.9万元,以“发奖金”等名义集体瓜分91.8万元公款,大队长范某一个人独吞了7.19万元。
深圳市宝安区龙城派出所滥用职权,巧立名目,向辖区内企业、居民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仅1993年4月至1995年4月的两年间,通过“三乱”刮来的民脂就高达513万元,全部流入自设的小金库,其中438万元已被挥霍,两年中仅大吃大喝就吞掉了80万元,原所长还购买了一辆昂贵的奔驰505豪华小轿车专供自己使用。
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要消灭行政处罚中的腐败现象,要纯洁执法者的权力,除了提高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更需要建立行政处罚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新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两个分开”的原则。
其一:办案的与决定处罚的分开。除当场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外,对其他违法行为,第一步由执法人员负责查明事实,第二步则由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罚决定;较重的处罚决定还必须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做出。
其二:除了在交通不便等几种特殊情况下,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外,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由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
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行政处罚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后又一部健全行政法制的扛鼎大作。约束权力、捍卫人权、民主至上、严而有度、崇尚监督……这些透过法律本身而闪耀出来的现代法律精神,体现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最好的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也是一场革命,它应当成为国家进步的铺路石、社会前行的支撑点,成为文明进程的精神之光芒、民众内心的信仰之火炬。
但愿未来的历史能够证明: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就是这样一种最好的法律。 行政处罚法文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