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与陈景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陈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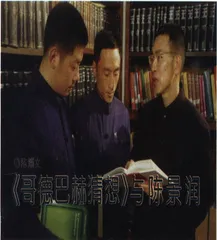
陈景润和他的研究生
记者:徐老,您认识陈景润在哪一年?
徐迟:1977年底,11月,当时我在武汉。《人民文学》通知我,希望我到北京采访陈景润。到北京以后,到数学所去了一次,见了个面。这之后我又到华北油田去了一下,再回来,12月开始写。第一个星期采访,第二个星期写作,第三个星期修改,第四个星期发校,很匆忙。
记者:认识陈景润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徐迟:关于陈景润这个人,当时已经流传了很多说法,都把他当笑话谈,有趣的事也很多。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被人当作一个怪物,一个疯子。我初见他时,就感觉他的形象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纯真的科学工作者。
当时我写陈景润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好多朋友说算了算了,写这样的有争议的人物,写不好没好处。后来我请教了一位长者,问他陈景润能不能写,他说,写,陈氏定理很重要,写吧。这样我就决定排除干扰、嘲讽去写。
做了一些准备开始采访。当时的数学所党支部李书记提供了许多情况。逐渐我就想到,众人认为是可笑的事,实际上是说明陈景润专注得比别人深。他整个人埋在他的研究里,我没见过其他的科学家能像他这样。所以我写的时候,带着很钦佩的态度。
记者:你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在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吗?
徐迟:对,当时他不让人进去,我们想了办法,才进去了。只进去过一次,当时他推着门不让进,很有意思。
记者:当时他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吗?
徐迟:我是在采访了跟他一起研究的杨乐、张广厚等数学工作者之后,归纳了几个问题,只跟他谈一次,大概两三个钟头。我问了3个问题,一是“猜想”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二是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三是突破在哪个地方?他把3段数学公式都抄给我了,我在作品中就用了这么3段公式。
记者:您的《歌德巴赫猜想》可以说影响了一两代人,因为当时正是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与您的其它作品比较,占什么样的位置?
徐迟:我只有一部分作品是写科学家的。60年代写了《祁连山下》,是写一个地质学家,因为这个,《人民文学》就让我写李四光。1977年8、9月写完《李四光》,12月写《猜想》。我18岁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有。我写得最好的报告文学是《祁连山下》和《猜想》。
记者:您写《猜想》时,想没想到会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徐迟:没有想到,陈景润拿出了成果,我只不过给他照了像。
记者:《猜想》发表以后,陈景润是怎么看的?
徐迟:他专门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了一次,感谢编辑部。他这人很厚道。
记者:这以后,你跟他谈论过这部作品吗?
徐迟:没有谈过。我们电话联系过一段时间,1979年以后,来往就少了。后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我是湖北代表,他是北京代表。他没来开会,我又没时间去找他,一直再没见面。
原来我还保留了一些素材,准备他1+1解答了以后,追踪再写一篇。后来跟数学家们一讨论,却认为这个问题非到21世纪才有可能解决,所以就放下来了。
记者:《猜想》对陈景润个人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徐迟:对陈景润,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当时因为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这次成名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尽管他可以不出席会议,那是因为国家同情他,同意他不出席。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很花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也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现在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只能感到遗憾。 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徐迟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