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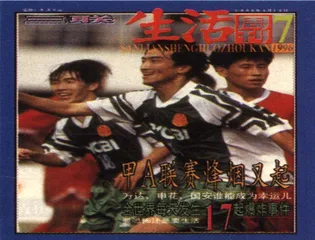
国奥队走向世界的又一次失败,给亿万人的足球梦重新投上了一层阴影。一个12亿人口大国,踢球的运动员总共才几千人,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实际很远。狂热与真诚不能代替现实。我们不应让虚幻的泡沫阻隔了对距离的思考。
武汉 黄亚东
妇女节目不仅仅是表现妇女
《生活周刊》编辑部:
我有幸作为某电视台妇女节目的评委,集中看了约30个小时的44个节目,感到妇女节目普遍女性意识淡薄,主要问题表现为:
1、将妇女完全融于社会,一些节目特别喜欢强调女性表现的“伟大的社会意义”。妇女帮助妇女致富,被概括为“无私奉献”;妇女们利用编织脱贫,被上升到“弘扬民族文化”。那么,妇女自身发展的意义在哪儿?作为一群体存在的意义又何在?
2、部分节目有片面强调女性与男性竞争关系的倾向。有的节目喜欢将女性置于与男人竞争的地位,鼓动妇女要“超过男人”。在一个节目里,记者曾总结说:妇女已经超过了男同志,是大半个天。身为女性,人生的意义不应是和男人竞争,而是通过寻找社会中合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传媒将男性视为竞争对手,就容易出现一种误导,即只要男人们能做的事情,女人们无论自己是否适合做,也都要求做。结果,女性将回避或否定自己的特征。
3、部分节目片面强调妇女“自我牺牲”精神,有一个节目甚至赞扬妇女“历来就有自我牺牲精神”。在节目内容里,妇女常是“母亲”的角色,或是为男人牺牲的“妻子”的角色,看不见她们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生活。如果有的女性认为她为男人牺牲一切是很幸福的,生活很充实,她也很满足,那是她个人的选择,她不应该成为“亿万妇女学习的楷模”。
在这些妇女节目中,要么妇女与社会、男人混为一体,要么女性特色被衍化为传统的、附庸的角色。实际上均是对妇女独立存在的价值的否定。
我想,应该警惕传统观念在妇女节目中的渗透。在流行文化中,对传统观念的传播已经够多的了。如妇女们总是在家庭厨具或清洁器械等广告中扮演主角,这就暗示着家务只是女人的事情。一个口服液广告曾经作出“每天给你一个新太太的承诺”,一个空调广告说:“某某空调,就像一个好老婆。”1995年,一家颇受青少年欢迎的报纸上赫然写着:“兄弟如手足,太太如衣服,不知道穿着T恤的男人会不会视T恤为另一个太太:依顺的、不作声地衬托出男人的自尊、地位、虚荣和满足。”这是典型的男权文化在媒介中的表现。妇女节目应特别警惕无意中传播这些传统观念。也许我对妇女节目寄予厚望,所以将妇女节目中的问题看得严重了。但我还是希望妇女节目多一点女性意识,多一些女性特色。如果没有这些,妇女节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北京 卜卫
疯狂的犯罪天才
《生活周刊》编辑部:
你刊登过的美国抓了18年没抓到的邮包爆手抓到了嫌疑犯,成为近来美国报纸杂志一大新闻。美国新闻隔一阵总能出现比编造还精彩的真实社会新闻,辛普森案还余波未完(还在民事法庭上继续打官司),现在又来了Unabomber(爆炸杀手)。因为悬念了许多年,结果比印象的还有趣。此人是当年哈佛毕业的名校生,在伯克利任过数学教授,是60年代的产物;25年前放弃现代生活,住在蒙大拿一所没水没电的小木屋里。他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被人称为“当代梭罗”,可是反工业社会采取侦探小说式的手段,又被人称为只有哈佛才产生得出来的“犯罪天才”。他的被发现是由他的弟弟检举的,其弟也是常春藤盟校毕业,80年代也有过一样远离社会的生活,不过后来还是重返社会了。两兄弟的故事给整个事件加上了家庭、兄弟关系的层面,其弟被称为“thebrother’s keeper”——“兄弟的守护者”,很爱其兄,可又怕其继续害人,所以举报。两人的姓是俄国姓——卡辛斯基,已被人像“卡拉玛佐夫兄弟”那样称为“卡辛斯基兄弟”,因为这故事中有不少陀斯妥耶夫斯基式道德、社会的伦理冲突。美国人一方面不能苟同他犯罪杀人,但他对当代工业社会的反感、环保观念,对资本主义大企业垄断的厌恶,又是不少社会中人都非常认同的东西。加上此公又是一个“疯狂天才”式的隐居者,所以人们对其的态度复杂,每天报上都有新消息,脱口秀也插科打诨。据说马上有3本有关的书在夜以继日地出版。以上情况,供你们的读者参考。
美国纽约 李昕
向关心周贲的人们致谢
编辑同志:
今年第3期《生活周刊》刊登了记者高晓岩的长篇新闻报道《碎玉背后的人间故事》,说的是1995年12月5日我的儿子周贲和他的同学马千里见义勇为,周贲牺牲、马千里受伤之后至1996年1月25日原定召开表彰会之间50天里的事。我看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报道社会上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方方面面的态度。总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简要精练,是对提高社会整体素质的一次呼唤。
但是,这篇报道却有一些不当之处,我作为周贲的母亲不能不作出说明。1月20日晚,共青团北京海淀区委书记、副书记等4位年轻的领导同志前来看望我们,在进行了抚慰之后,告知我们将授予周贲、马千里“五四青年奖章”。并说,他们虽不足16岁,但代表了青少年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海淀区青少年的骄傲和光荣,因此要给予他们最高的政治荣誉。对此,我表示了感谢。我知道这份荣誉不但代表了海淀区团组织对他们见义勇为的表彰,而且代表了他们的一份心意。但文章中,这段对周贲、马千里很有意义的内容却进行了一种低调处理,违背了4位年轻同志的初衷,对我的心理也是一种扭曲。
独生儿子周贲已经牺牲4个多月了。很多人在关心他,最多的是问及他的名份。从某种意义讲,除了对15岁孩子的深厚感情之外,不如说是关心见义勇为在当前社会形态下的价值。2月11日上午10时至11时,海淀旅游职业高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周贲送行的告别仪式。灵堂的横幅上写着“周贲见义勇为精神永存”,几十个单位赠送了花圈,挽带上讴歌了英雄烈士的壮举,校长的悼词对他的生前和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海淀区教委各级主要领导、亲友前辈、老师同学等数百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原定于元月25日召开的表彰大会,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提出延迟遗体火化(我曾联系遗体捐献,希望儿子骨架留于人间,作为他对祖国医学的最后贡献,但未实现),使大会推迟。目前海淀区教委仍有专人办理此事。虽然周贲、马千里这一事件并未正式定性,周贲名份也尚未确定。也未授奖章。但我期待着这一天。以上补充,以飨关心周贲的人们,并感谢他们这份心意。
周贲的母亲 李林
别让“中国音乐电视”虚假繁荣
编辑同志:
自戏曲音乐频道开播以来,音乐电视的播出时间大大地增加,除“中国音乐电视”外,还有“音乐电视60分”、“电视精品廊”等,时间累计5个半小时之多。这对喜欢音乐电视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各栏目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没多少新的作品,多半是一些老歌在反复播出,主要区别是播放时间长短而已。
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已播出50期以上,按平均每期播出6首,总计应有300首歌曲之多,但其中新歌不过20首,绝大多数是以前播过的老歌。新期的内容是怎样构成的呢?一是把前面播过的原封不动地照搬,如(169)同(140)、(178)同(166)、(170、)同(142)等等举不胜举;二是“重新排列组合”,即从前播过的期数中适当抽出一二首再组成新的一期,这种改头换面作法占主导地位。
我不明白,既然是重播以前的内容,为什么还要改头换面再冠以新的期数播放呢?我认为有新的期数,就应有新的内容,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能使人觉得中国音乐电视栏目的决策者和编导们似在愚弄观众,有制造虚假辉煌之嫌呢。在新的中国音乐电视作品不多的情况下,节目的播出周期可以拉长,比如从现在每天一期改为每周一期或半月一期。目前,如果内容不饱满,是否可再增加些别的文艺节目呢。
北京 刘波
重赏之下……
编辑同志:
春节晚会上,《九妹》新民歌轰动京城乐坛,使亿万观众耳目一新。中唱公司出重金借助新闻媒体寻求作者本是一件弘扬民族文化的善举,谁知,重赏之下冒出众多“勇夫”,那些自告奋勇的假冒作者居然会纷至沓来,真让人“赞叹不已”。这等人的“勇气”和“胆量”确实让人“钦佩”。因为,中唱公司毕竟不是当年不善辨真伪的唐僧;这帮敢撞大运的“勇士”想必也是知道领不到赏金肯定不会空手而归,不用说都会领走一顶无形的“厚颜无耻”的帽子。
所幸的是,真正的作者已于3月17日被确认,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勇士”前去亮相。我们将有幸见到真正的作者,但同时也不免感到有些遗憾:那就是不能欣赏一下那些“勇士”的风采;我想像他们也一定是“多彩多姿”,让人“赏心悦目”的。为此,我不知道该不该埋怨你们这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算不算你们的一次“失职”?如果“老记们”早先在中唱公司接待处设个采访点,对前去亮相的“勇士”依次采访,然后制成专题片或纪实性专题报道,在黄金时间播出或重要版面刊载,那一定会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来广告收入剧增,二来亿万观众读者也能长长见识。近年来,各类假冒伪劣品层出不穷,广大平头百姓对之厌恶之极,如能见到这些“活生生”的假冒,既可当作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话题,也可当作生动教材,让学生们在学习“重赏之下……”与“厚颜无耻”成语时加深理解其中含义。
北京 蔡曙光
孩子的可怜
《生活周刊》编辑同志:
我昨天经过北京双安商场,看见一群小学生在马路上散步。那时正是上午10点。我看见他们规矩而有序地从过街天桥的这边跑到那边,然后再折回来,反复好几次。他们的队伍不断地被过往的行人冲散,又不断地在口哨声中聚合,有几个孩子干脆趴在栏杆上看天桥底下的汽车排着长队疾驰,一派目中无人的气势。
阳光中的尘埃分外清晰,在孩子们身边扬起。我突然觉得这群学生很可怜——我小的时候在北大荒,我们的学校简陋而衰败,我们的黑板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爸爸捐送的呢。但是我们有一个又大又空旷的操场,课间操时候,全校师生站在国旗底下随着音乐做广播操,非常庄重非常美好。
我不知道现在北京有多少小学的小学生不得不在马路上做课间操。我觉得这种情况实在让人忧虑——不单是安全、健康问题,而且,这么一来,孩子的童年就少了一个程序;或者说仪式,一个庄重而虔敬的仪式。
北京 周薇
选文乎?选美乎?
编辑同志:
近年来各种刊物对稿件的筛选标准似乎一直发生着微妙而惊人的变化。除了文章本身的质量之外,还有“领导”稿、“人情”稿、“收费”稿、“职称”稿等等,不一而足。最近又出现新招,笔者暂定名为“玉照”稿。
昨天读到一份在成都小有影响的通俗杂志中的一篇名为《漂亮女孩与她们的文章》的短文,身为编辑的文章作者收到了一篇附有一张“玉照”的稿件,“如果照片是那女孩的那女孩的确很漂亮;如果那文稿是她的却不敢恭维不怎么漂亮甚至够不上发表”,于是这位编辑仁兄大动怜香惜玉的恻隐之心,“那么漂亮的女孩子能写文章就相当不错了,不必苛求”,结果“这文稿上了,连同她漂亮的玉照及玉照上得意而妩媚的笑”。
这位仁兄联想力可谓非凡——稿件的质量标准也可以随意替换,其质量虽然“够不上发表”,但只要“玉照”够靓也可通融。这位生不逢时的贾宝玉式的“意淫”者,所作所为令其宝玉兄自叹弗如——能够将其“意淫”意向通过杂志强加给读者,而不管读者读了这篇“文章”、欣赏了这张玉照后会不会作呕。谁说现在的编辑“素质”不高,凭此公敢于将“玉照”置于文章之上的“创新”能力,区区一介编辑是绝对地屈尊了。
这位投稿的作者,如果真是照片上的靓女,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别出心裁地将市场、官场上玩剩下的这一套小试于文场,的确出手不凡!从此选文改成选美,文化在这种“得意而妩媚的笑”声中是哭还是笑?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篇大文在结束时说“个别漂亮的女孩的文章正越来越浮虚、空洞、浅薄,……走向恶心和反感”,且不说这里与前面观点的自相矛盾,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更令人恶心和反感的恰恰是这类仁兄们,因为正是他们,铸就了这类感受。杨绛在小说《洗澡》中指出,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恶化与知识分子的自我作践不无关系。上述这类仁兄们与靓女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就同现今的文化困境毫无关联?
四川 苏志宏
本刊1996年第6期所刊《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印象》一文,作者为廖一梅。特此向作者和读者致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