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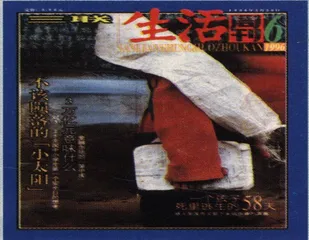
孩子问题最能牵动人心。校园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令人触目惊心。教育工作者没有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的意识,怎么可能遏制恶性事故?只有人人都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宝贝”时,孩子们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日。
武汉 林成清
该喝彩还是该叹息?
编辑先生:
我很感兴趣于西方的文化现象如何在东方的一本刊物里被提及和“重写”。它们看上去很新鲜有趣,尤其是因为有了距离感;但身临其境的话,您会知道这些话题并不轻松。
今天西方所获取的无限的个人自由是经由多少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社会、宗教、历史和自然对人的约束力的不断松弛。所谓自由,几乎就意味着这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切再也无权命令人们去寻求一己利益以外的东西。当这些力量松弛了的时候,西方文明的想象力出现了一块空白。而填补这块空白的,是对工业技术的无边潜能的信仰。我们现在进入了科技文明阶段,它振奋人心,它要求一种新的崇拜。尼采可能要为此大鼓其掌了:人的权力意志已无可匹敌。但其实,工业技术就是我们自己,正如哲学家乔治·格兰特所指出的,对工业技术的敬仰就是一种自我崇拜。自我崇拜尽管舒服惬意,却无力支撑人类所需的生命意义;它是一种出神的状态(preoccupation),最终会成为一种生活障碍。如今的北美洲是地球上工业技术最先进、医药研究和应用最发达的社会,但“扑洛载克”(prozac)和“利它灵”(Ritalin)之类的药(它们越来越受“过分活跃”的年轻人的钟爱)——说真的,实在是有点用意不明;它们造就的不是自由的生活。
以上这些牢骚,当然,并无反抗个人自由之意。
加拿大汉密尔顿市 格兰·弗莱彻(Glenn Fretcher)
纳税是个沉重的话题
编辑同志:
贵刊的读者来信栏目办得极富特色,它使我们普通人有了一个吐露心声的地方。最近刚宣判的魏宝林高工偷税案令我和周围的人很困惑,引出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写给你们,很希望能看到你们的有关深入分析和报道。
首先,魏宝林这笔技术服务费收入是1993年3月以前的,此后3年未见其再有偷税的行为,而在这段时间内曝光的偷税案无论是数额还是性质上都比魏工严重得多,却未见绳之以法的事例。中国人历来懂得“第1个”的含义,这次魏宝林首当其冲地成为中国首起公开审理的个人偷逃税案主角,多少让人觉得缺少说服力。
其次,魏工因偷税而违法,应该给予惩处,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该是表面文章,那么多名符其实的偷逃税大户,如某些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一次出场费收入就达几万、十几万;而一个工程师半年的技术服务收入不过10万元,与前者本不在一个等级上。
第三,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一点勿容置疑。然而,未纳税是否都是偷、逃行为,有没有漏的可能?前者是主观犯罪,而后者则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致错,漏税是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如果未主动纳税都该判刑的话,那么去年三峡走钢丝的科克伦先生应该客居中国监狱了。
魏宝林的偷税案令人追索:我们的税制是否合理,实施细则是否切实可行?地税官员说,他们不可能全顾上,况且中国现行的现金交易体制无法提供公民经济活动的情况,造成了征管难度很大。但出现了因故漏税现象,负责税收的身负责任的国家公务员是否也有责任?这如同乘坐公共汽车,乘客有义务主动买票,而售票员的职责是监票。乘客如无票乘车未被发现,是不是该追究未尽职守的售票员的责任?
我认为:要使国家税收能得到保障,除了继续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外,最重要的还是完善征管体制,合理设置税种及税率。改变一刀切和仅靠公民自觉纳税的现状,使公民了解应纳税情况,也能方便操作。据报道,国外税制较完善的国家,一个人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情况下纳税额是不同的。例如,同等收入条件下的个人,其家庭是一人工作还是夫妇都工作,有孩子、无孩子和有几个孩子税率都不同。合理的税制有助于提高人们缴纳税款的自觉性。另外,税收该有政策性倾斜,非赢利性的科技服务收入是否应考虑给予低税率的鼓励,因为其社会价值远远超过税收价值,而对经常性的赢利收入则该重点防范。
北京 辛言
购物为什么放不下心
编辑先生:
年年3·15都喊打假,但生活中的假货、劣质货却是越打越多。今年《东方时空》专门请出了乔装打扮的王海,乔装打扮的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意外的报复与伤害。在打假日让已成为大名人的王海戴上胡子和墨镜,是不得已,但实在也成了对眼下社会境况的辛辣讽刺。
现在时时处处见到质量问题亮起红灯。给孩子买了学习机,可消费者协会宣布,学习机、游戏机的合格率是零。家里装了煤气热水器,才用了一个月就点不上火;经常吃的“康师傅”方便面也被曝光不够份量。这些还不算什么,听说眼镜的合格率也非常低,这实在令我们感到惊慌。连医疗用品都存在这么严重的问题,购物、消费又如何能让人放心呢?
假货、质量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首先在于制造假货、不顾质量问题者可以很容易地获利而很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假货和伪劣产品可以以贿赂作为中介,在推销自己的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保护伞。消费者的反假、反伪劣却往往要经过很多繁琐的周折,不光要付出时间与精力,给自己带来情绪上的烦恼与不愉快,而且闹大了,像王海那样,还有人身安全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打假只会是一个人人都要高喊的口号。
我们也有有关的法制、法规,但当钱决定一切时,法制法规就无法健全。在法制法规不健全的前提下,就只能依赖人自身的道德与良心了。能不能说,现在的打假反伪劣,更多地是要唤起人们的道德心与责任心呢?
《生活》应多关心这些与百姓利益攸关的事情。
济南 何志成
有知识的人需要钱?
编辑同志:
读过贵刊今年第四期《流动的书房》一文,很有些感想。
我因工作原因,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要到外地出差,而“逛书店”似乎是每到一座城市乃至村镇所必需的“游览”项目。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途经上海到汕头,两座城市关于书店的变化,倒是给人以不小的启发。
上海南京路上的“新华书店”,其规模和知名度在全国也曾是数得着的大书店。而今的情景却令人感到面目皆非。书店原有的很大部分面积已出租或转让给其他行当(如服装、日用电器等)进行经营,而售书面积委屈得可怜,拥挤不堪,书的品种也有限。像上海这座人员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准、技术水平在全国如此之高的城市,书店如此的遭遇,岂不让人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担忧?
可喜的是我在汕头看到的另外一幅景象。5年前第一次到广东省汕头市时,为找一处好一些的书店,几乎要骑着车跑遍全城。而近两年汕头的老书店不断扩大营业规模,新书店更是相继出现,而且位置多选择在繁华路段,内部装修也越来越高档。在我2月初准备从汕头返回北京过春节时,忽然发现在汕头长平路东段的“三联书店”已开始营业,长平路本是汕头最繁华的城市道路之一,书店的位置又与汕头市未来的市中心区11号街坊相毗邻,“三联书店”的开张无疑为汕头经济特区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再看书店的内部,让人感到亲切而宽松,装修清雅而明快.且书的品种也很多,与我在上海南京路书店里的感觉完全两样。我又留心观察了一下,即使是路过顺便进店浏览一下的顾客,也很少有空着手出去的。也许再过一段时候,这里也会出现像《流动的书房》一文中所提到的“咖啡书屋”或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功夫茶书屋”了。那时,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文章的作者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是我们读书人的福气。
平心而论,汕头的文化基础不如上海,也许做老板和经理的人的比例更多一些。现在是不是“有钱的人需要知识,有知识的人需要钱呢?”。我想,大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一命题的本身,而是在于“知识”与“钱”两者之间,要有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样的社会才会进步。
北京 王晓阳
双向选择还有不公平
《生活周刊》编辑同志: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请放心,此信与本人求职无多大关系(我已侥幸找到单位),但我周围同学的境况却实在并不乐观。
白天大家或者排队给各单位人事处人事科打电话,或者守在系办公室生怕错过哪个用人单位的突然莅临;或者干脆包里背上3张协议书满京城地乱逛。晚上熄灯躺在床上,议论谁谁的表叔和某部某要人是同学,某某老师真没人味一科不及格留京指标没指望了,xx单位领导有眼不识泰山谁比谁牛走着瞧……
大学4年,腾出大半年的时间东跑西颠,实在得不偿失。由此想到贵刊1995年第5期那封《大学里需要就业服务中心》来信说得非常有道理,如有比较得力的中介机构专门在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牵线搭桥,能省不少事。现在实行的是双向选择,机会相对多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自己的能力正当评估运用自由,所以有的同学每隔几天找个新单位,半年下来找过的单位超过一打;另有一些同学守株待兔整天抱怨“还不如硬性分配呢。”
还有个问题是,大家对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并不那么信任——除了无可奈何中认同的四等公民说(一等北京男生,二等外地男生,三等北京女生,四等外地女生)之外,谁能肯定没有后门关系等等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其中作祟呢?
北京 康平
《朋友们》带动首饰潮流
《生活周刊》编辑部:
看到贵刊对美国流行电视剧《朋友们》的介绍。据我所知,《朋友们》目前正在带动时尚的趋势。以前,当人们谈及流行电视剧对服装流行趋势的影响时,往往提到60年代《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清纯的形象,纷纷模仿她在电影中的发型和服饰。时光流逝,人们对于服装和服饰的欣赏品位已情趣各异,因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而引起某种式样的服装或服饰大为流行的情况已越来越少。但《朋友们》却重温了一次《罗马假日》的旧梦——剧中女主角佩戴的Y型首饰正风行全美。
所谓Y型项链,就是当你佩戴该款项链时,项链下垂部分先聚到一起,并由一装饰物固定住,剩下的项链的两端自然垂直,呈Y型。珠宝设计师Ganard Yoska说:“每人都想佩戴这种款式的项链。虽然大家都认为今年不流行佩戴项链,但我在商店里看到的情况却是,当人们在《朋友们》和《Melrose Place》(美国另一流行电视剧)上看到这种项链时,都到商店里来询问是否有售。”首饰设计师Stephen Dweck则如此解释:“人们愿意天天佩带这种项链,是想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保持一致,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很舒服。”
但是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Y型项链并不是今天才设计出来的。与服装的流行一样,流行首饰也是循环往复,设计师们往往从过去的设计中获得灵感。Yoska说这是一种潮流的回归,人们或许能在自己祖母的首饰盒里找到它。“如果你找到了,你就戴上它;如果找不到,你就只好买了。”
提供以上信息,但愿对贵刊时尚版能有所帮助。
北京 赵经纬
打针折腾记
编辑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大夫让我打14天的针。第一天赶上三八节,我在家属院小医务室打完了第一针。可那里只在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开门,晚上不开,周六周日也不开。第二天和第三天是周末,只得骑20分钟的自行车到外面的一个门诊部去打。第四天在单位所在写字楼的医务室打了第四针。第五天,我怕挨训,找了一个跟公司有密切关系的科研单位的医务室。第五天的头一针还挺顺利的,可到了第六天和第七天,不愉快又发生了:我11点多去医务室就赶上了大夫们的午餐,接近10点又赶上了工间操休息……
折腾了一遛十三遭,14针才打了一半,治疗的成果也被所遭受的冷眼足足抵销了一半。这时才感到从不生病的人真是令人羡慕。但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呢?况且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生病的人永远不会少。我知道跟许多人的就医经历相比,我的这个小故事根本算不了什么,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并不奢望从医务人员那里享受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希望起码应当受到尊重的体恤,而不是在身患病痛的同时还要承受精神的伤害。在商业界,不是已经叫响了“消费者是上帝”的口号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有“保护消费者权益日”了吗?那么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患者何时才能得到应有的人道主义救助呢?——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北京 晓秋 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