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夕照
作者:戴锦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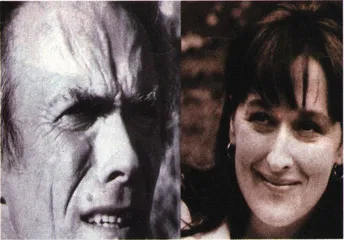
在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盛极一时之后,这部忧伤、温情而不无矫情的畅销书理所当然地候选并“入围”于好莱坞。一如所有“为流行而制造”、并确乎流行起来的作品,其真情所在与最后归宿一定是电影、电视。一部畅销小说的“电影版”出现,才意味着真正流行的开始。在美国,一部小说的畅销,常常只是未来影片的最初广告;而伴随电影的广告效应而来的,才是小说的再度风靡。
沃勒的《廊桥遗梦》在为好莱坞的头牌导演所争购、几经辗转之后,终于于1995年由“好莱坞活的电影史”、因《不可饶恕》(一译《杀无赦》)而荣登多重奥斯卡影帝宝座的林科特·伊斯特伍德执导拍摄完成。如果说,沃勒的原作刚好因世纪末的美国萦回不去的怀旧情调而流行,那么,伊斯特伍德与昔日影后梅莉尔·斯特利普(曾被美国《生活》杂志称为“角逐名垂千秋万代的美人”、而近年来却因为“老了”而被势利的好莱坞无情抛开)共同出演这一事实本身,便使其在美国观众心中“古”意盎然。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之后,影片于6月上映时盛况空前。
如果说,沃勒的小说因对60年代的文化记忆与历史的改写而成功;那么,一部影片所实现的怀旧氛围却不能仅靠被述年代而完成。影片的怀旧,不仅是故事中的忧伤与昔日温情,而且是以媒介——电影自身的怀旧来呈现。这部彩色宽银幕电影本身,不仅是对经典好莱坞情节剧的复原,而且是对经典的、陈旧的好莱坞电影叙事语言的复制。在原作称之为“有了能跳舞的地方”、“大路和远游客”两个段落中,伊斯特伍德反复使用在当代电影中已不多见的长叠化,将金凯与弗兰西斯卡在暖调的烛光中相拥共舞与缠绵做爱的场景,呈现在一种舒缓、甚至过缓的老式抒情之中。而作为好莱坞电影所必须的情节高潮,伊斯特伍德扩展了两人在雨中最后相遇的段落,金凯在滂沱大雨中固执地站在街的另一侧,任凭雨从头顶上浇下,深情地凝视着车中的弗兰西斯卡,而后者则透过雨流淅沥的车窗与他对望。接着,是一个极为经典的平行蒙太奇段落:十字路口,金凯的卡车在红灯时停在弗兰西斯卡和丈夫的车前,他摘下胸牌挂在前反光镜上,无声地最后呼唤女人。于是一段剪辑节奏渐频镜头切换,便在女人视点中的晃动的胸牌、金凯固执不动的身影与特写中弗兰西斯卡颤抖地放在车门把的手间交错展开。指示灯转绿,金凯仍停留在那里,驾车的丈夫开始鸣笛抗议,当女人的手终于压下了把手的瞬间,金凯的车缓缓驶动——未完成的“最后一分钟营救”。
正是由于叙述媒介的转换,电影尽管由确乎被称为“本世纪最后一个牛仔”的伊斯特伍德执导并出演,但它毕竟无法呈现安放于女性角色视点中的“骑着彗星尾巴来到地球上的豹子”之类的描述,于是影片成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好莱坞爱情故事,而不再是一个男性主人公的自恋之镜。但影片因此而同时失去的,是原作中将金凯作为一个“远游客”、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的抗议者的重要层面。作为一部经典的情节剧,一如原作,它再度实现了新好莱坞电影的重要功能:抚慰普通人。在一个非道德的道德故事中完成对现存生活与秩序的再认可。影片因此而保有并加强了原作中的倒叙与时空交错,弗兰西斯卡的一对儿女成为影片中更重要的角色。这部现代爱情传奇的意义,在于终于了悟了母亲的故事之后,兄妹重获了失落已久的温情;儿子奔回家中深情地拥抱平凡而被爱的妻子:而女儿则穿上了母亲珍藏的连衣裙,挂电话给丈夫,决计结束无爱的婚姻。影片的尾声,在雾中廊桥上撒落弗兰西斯卡骨灰的场景,在反抗愚昧世俗社会的表象中,再度认可了关于爱情、永恒、道德的“不朽信念”。廊桥夕照,再次成为一种询唤与整合,让你在热爱生活的同时,忍受不甚完美、或甚不完满的现实。 好莱坞廊桥遗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