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心灵谁来呵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程青 图·林慧 1995年11月15日,15岁的袁鑫两次自杀未遂以致高位截瘫。这血的教训,仅仅因为袁鑫太傻吗?
1995年11月15日,15岁的袁鑫两次自杀未遂以致高位截瘫。这血的教训,仅仅因为袁鑫太傻吗?
当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看到她时,她已静静地躺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的病床上。床头有漂亮的绢花和布娃娃,手中捧一本《傲慢与偏见》。
她叫袁鑫,北京15中初三学生,尽管已脱离了危险期,被转入普通病房,但由于胸椎横断性骨折,造成高位截瘫,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可能永远不能离开病床了。
袁鑫自杀的起因,仅为一句关于老师胖瘦的议论。15日下午,袁鑫与几位女同学在教室外看见一位女教师提着一袋梨。袁鑫说:“这么胖,还吃梨!”这位女教师听到后,便告诉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姜老师随即把袁鑫叫到办公室,令其站立一旁学习《学生守则》。袁鑫想解释一下,姜老师却对她说:“如果女老师告到学校,就要给你处分。”
那天恰好是家长会。家长会结束后,袁鑫母亲和姜老师来到办公室。其时,袁鑫已在办公室站立长达一小时。见到母亲,袁鑫未说话就哭了。姜老师对袁鑫的母亲说:袁鑫刚才骂了高三年级的一个老师。袁鑫便把同学李娜、崔敏等6人写的证明给姜老师看。证明上写着:“姜老师,袁鑫没说太过分的话,就说她有点胖。我们都可以证明,请您原谅她!”但姜老师看了几眼,就把这份证明推给了袁鑫,让袁鑫家长下周一上午9点半到学校,带着孩子向那位女教师赔礼道歉。
当晚10点多,袁鑫母亲带着袁鑫从姥姥家回到石景山家中,将此事告诉了袁鑫父亲。袁鑫父亲温和地批评了女儿,要她尊重老师。袁鑫只是站在一旁哭,并没说什么。当晚,她给爸爸妈妈留下一封3页纸的遗书,割开了左腕与左臂弯处的血管,唯恐死不了,又从6层楼上跳了下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有邻居见她躺在楼下水泥地上,跑去告诉她的家长,才送往石景山急救中心抢救。
袁鑫在小学连续6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小学毕业前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当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这所市重点中学。袁鑫的父亲袁金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鑫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自尊心强,功课也拔尖。小学6年没让家长操什么心,都考“双百”。上了中学,有点不适应,成绩也有些下降。但我们并不在分数上过多地要求她,不逼着她学,只是为她创造些条件。出事前一星期,数学测验袁鑫只得了63分,哭了。在饭桌上,我们问她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她说现在都明白了,我们便没有过多责怪她。
当问袁鑫父亲面对孩子轻生,家长对自己最自责的是什么时?袁鑫父亲沉痛地说:平常我们和孩子对社会上的事聊得太少。尤其是社会上不好的事,基本不在孩子面前说,怕她过早知道会沾染上。说心里话,我们最担心初中生早恋会影响她。其实她很单纯,个子虽说1.60米,但心态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另一方面,我们总对孩子说,老师说得对,要怎么做;却从来没有告诉孩子当老师、家长错了时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后悔的。平常袁鑫不是特别脆弱,也不是特别说不得,我以为她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自理能力也强,没想到这一回受了委屈却没能经得住。
关于袁鑫跳楼,学校科研室主任崔金君对记者说:学生出这样的事,学校老师、尤其是她的班主任压力很大。她的班主任并没对她说过要给处分的话,您听听这样的事够得上给处分吗?
也许任何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会顺着这位科研室主任的提示,作出正确的判断,但15岁的初中生却自己钻进了牛角尖。按袁鑫的说法:“我怕背上处分。学习再好,背上处分也完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是一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双耳失聪,靠助听器与别人交谈。袁鑫说平常他和学生沟通很少,大家心里比较怕他。这位班主任曾带着水果两次到医院看望袁鑫。事到如今,他只能无奈地劝袁鑫:“好好休息”。
面对如此痛心的事件,人们不仅要发问:如此一所重点中学,为什么不配备一些至少能倾听孩子声音、与孩子沟通的班主任?
袁鑫在给她父母的绝笔信中写道:我还没有报答您们却先走了,我也很惭愧。您们白白养育了我14年,真对不起。当一位年长护士问袁鑫:孩子,你后悔不后悔时,袁鑫点点头,流出了眼泪。袁鑫让记者告诉所有受了委屈的孩子们:“别像我一样傻!”
但这血的教训,仅仅是因为袁鑫太“傻”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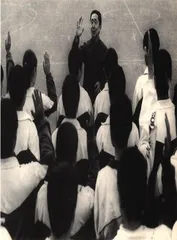
孙维刚用优越和清高为他的学生们筑起一道心理防线。他的学生一旦离开这道防线,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呢?
孩子问题已日益成为老师、家长、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说,这个社会太复杂、太多元,而我们这些被卡通片哺育出来的孩子太脆弱;也有人说,这一代孩子从五彩缤纷的社会里汲取的东西太丰富,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已无法适应他们心灵的发展;还有人说,现代社会已经造就了孩子们将来发展的多种可能,分数制却使他们无从选择。反正,孩子们是越来越累了:背上越来越沉的书包,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功课还需应付各种各样的智力和技能培养。教师、家长往往过多关心他们的成绩,有多少人关心过他们的心灵呢?
孙维刚是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学生的。这位北京市22中学的特级教师、国家数学奥林匹克的高级教练,对班上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真挚的父爱。班上哪个同学气色不好、情绪不佳,他都看在眼里。有年暑假,孙维刚带几名学生从成都集训归来,把自己的软卧让给学生轮流睡,自己在硬座撑了39个小时。有个学生父母双双出国,他就把这个学生接到了自己家里。当了33年老师,他从来没让忘了作业本的学生跑回家取,也从来没让做错了事的学生罚站。不管什么时候,学生犯了错误,他都会以宽容慈爱的目光看着他,并对他说:老师可以原谅你。而当他自己犯了错误。比如迟到了,他不为自己寻找理由,而在教室外的冷风中“罚站”一小时,用形体语言告诉学生:错误要自己改正。
孙维刚带出的班,在全北京市响当当。22中是一所普通中学,生源条件并不如重点中学那么优越。
孙维刚第一轮带的班,全班入学时的平均总分数为189.51分,当时北京东城区最差的一所学校的入学平均总分是192分。3年后,这个班中考平均总分为583.5分,而当年北京市最好的一所学校的校平均总分为567分。到高考时,全班41名学生,40名考上了大专院校。
第二轮实验班,全班入学时仅有4人达到市重点中学起分线,到1992年参加高考,全班除一名同学外,全部上线。15人考上清华、北大。到第三轮,孙维刚提出的口号是:“50%考上清华、北大!”他鼓励学生们成为“我们民族划时代的科学家”。
作为一名有33年教龄的老教师,孙维刚自创了一套“数学结构教学法”。他认为数学的内在规律性极强,通过题海战术、重复练习使学生掌握数学公式是机械、死板的,本身就是教学的失败。他要求学生们学得主动,向老师挑战。他不再采用传统的方式向学生讲解每道题怎么做,而是让大家先做。他鼓励学生开启自己的思维,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在思维训练中训练思维。
孙维刚注重让知识以系统的面貌出现。有时一堂数学课他可能上成地理课、哲学课、世界科学史课、甚至足球课。在思维训练中训练思维。在带第三轮实验班时,他3年中就给学生上完了中学6年的数学课程。不仅没增加课时,还减少了一些课时。
孙维刚向学生提出3条标准:一是做诚实、正派、正直的人;二是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三是做有丰富感情的人。孙维刚对记者说:第一条是立班之本。比如,目前学校普遍作弊成风,考试时一个班要分两个地方,就是为了学生与学生坐得开些。我们班的同学不作弊,从来不需要两个老师监考,老师发完卷子便可以离开教室。对这一条,我不仅要求学生们不骗别人、不骗自己,还要求他们对事实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认识。对第二条,我要求我的学生不光是考上大学、做博士等等,而是要他们为人类作较大的贡献。
说到第三条,孙维刚略带反省地说:“有一点我可以说是做得不够。我年轻时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而且从中获益匪浅,但我限制我的学生看小说。”问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怕阅读小说占用学习时间,孙维刚摇摇头,说:“还不完全是这样。我担心孩子缺乏辨别能力,会走弯路。即使像鲁迅的作品如《肥皂》那样的,学生也许都会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由于防患于未然,孙维刚这个班上没有早恋现象。男同学短短的头发,女同学不施粉黛,绝大部分着校服。孙维刚告诉记者:“班上男女生关系也比较单纯,除了学习和班务的一些必要交谈,男女生并不过多地在一起闲聊。我对同学们说过,如果是一名男同学帮另一名男同学解题,有的只是友谊和谢意;但如果是一名男同学去帮一名女同学解题,多次以后谢意之外也许会有另外一层东西,提醒他们平时注意避免。”孙维刚比较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班是不大有可能与外班或外校学生恋爱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班是最好的,他们有很强的荣誉感。同样,基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感,我希望他们在发型、服装上不要追随社会上花里胡哨的一套,他们都做得很好。
孙维刚在学校与社会之间,用拔高的方法,在正面教育、细节引导之外,在一个班级里,他用优越和清高为这些品学皆优的学生筑起了一道心理防线。孙维刚认为,社会对学生产生的不良影响,应以这道防线来抗拒侵蚀。在这道防线内培养出了一批单纯而又清高的好学生。现在这些学生纷纷获得了优良的成绩和品行。但一旦离开这道防线,他们能不能适应社会呢?他们长大成人后,熟记孙老师的,又是什么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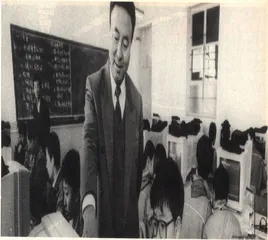 王晋堂认为,只有使学生懂得社会,才是关心孩子。他种了一块轻松教育的“试验田”,他的学生进入“大田”,又会怎样呢?
王晋堂认为,只有使学生懂得社会,才是关心孩子。他种了一块轻松教育的“试验田”,他的学生进入“大田”,又会怎样呢?
王晋堂是北京市第一中学校长。北京一中是清代顺治初年就建校的老学校,有350多年历史。但北京东城区7所重点中学,一中却榜上无名。
说到重点中学,王晋堂颇有感慨。他忆起一次在建平中学与美国华盛顿州教育厅长夫妇一起吃饭,厅长问何为“重点学校”?听说重点学校可根据考分优先录取学生,这位厅长说:“这多么不公平!”对于非重点学校来说,生源上确实存在着不公平。而对每个受教育的个体而言,我们的教育体制并非是因才施教,而是实行了一套“丢卒保车”的做法,淘汰制使100个学生当中可能有60个成为失败者,这是一种更危险、也更不容忽视的不公平。
王晋堂深深意识到,我们的学校不是按人的素质与成长发展去施教,而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不考的就像甩包袱一样赶紧丢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智育轻德、体、美育,智育中又是重知识轻能力,知识中又只重考的几门,忽略其他的科目。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会出现“高分低能”。一个优秀的学生可能完全不懂得社会,无法适应人际关系,心理脆弱,承受不起挫折等等。
如何改变?王晋堂于1990年推出了一个“12年一贯制中小学整体实验”计划。在中学设立小学部,实施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不必经过升学考试的新模式,称其为“踢破两道门坎,摆脱升学战车”,提倡让学生在“放大”的时空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
实验一实施,校内外看法不一,王晋堂的压力着实不小。首先是老师们纷纷跑去问他:真直升不考啦?紧接着就是:质量怎么办?高考升学率怎么办?家长也很紧张。别人家孩子上小学,语文、数学都要考双百,我们怎么好孩子才得了七八十分?一时间,都在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校内有议论,说教育局要派人来。王晋堂马上打电话去说不能来。议论归议论。但不能在思想上引起混乱。他提出“大胆干、不争论、允许看”,在实验最困难的1991年5月,王晋堂给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这位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对王晋堂说了三句话:相信实验有潜力、有成果;失败了也是经验;要重点保这一项目。
到1991年7月,这一实验经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列为市级“八五”重点课题。实验两周年阶段汇报时,已扎住营盘,渐入佳境。
中学里面办小学,听上去的确颇为新鲜,王晋堂提出“乐学早慧”。他说,为什么一个人看教科书几页就累了,读一本小说却不累;加班两小时疲劳了,打一夜牌却没事,关键就在于“兴趣”。“乐学早慧”就是抓住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在玩中学,学得轻松,学得主动。放松了才会有好成绩。
王晋堂的小学部又叫“实验部”,别的小学普遍7:30上第一节课,而小学部8:35才上第一节课。王晋堂说:“让小不点们多睡一小时。这一小时对他们身体成长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晚上一小时课,给孩子所带来的是,在胸围及体重的测定上,小学部的学生从5岁常模数据低于北京市7岁数据(因北京市和全国的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从7岁始,无5岁数据),到10岁时则超过市常模11岁数据,11岁超过12岁数据”。
免去了升学考试,又提倡轻松教学,学生们水平是否参差不齐?当小学部的学生即将到达初中阶段时,王晋堂推出了更为细致的“滑动学制”:按照小学5年级学生的整体程度分成两班,一班照常规升入6年级,另一个班超前升入初一年级。
鼓励在常规班冒尖的学生升上去。也允许在超常班跟不上的学生再滑下来。王晋堂把这叫做“板块滑动”。另一种叫“条块滑动”,即单科滑动。在4年级尝试了英语学科的分班学习,同样收效甚好。预计英语提高班的同学在6年级时可达到初中毕业的英语水平。
王晋堂说: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信这个实验不会垮。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家长的监督,接受着全社会的监督。有位学生家长看对门的孩子进了重点小学,用的是集中识字课本,一本书有400个生字,而自己孩子在小学部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全书190个生字,不由急上心头。但对门的孩子每天夜里11点还睡不了觉,自己的孩子看了电视、弹了钢琴,8:30就可以睡觉了。再把重点小学的题拿来考孩子,孩子也都会,家长慢慢也就释然了。有的家长甚至说:眼下少认一些字,难得的是孩子体格健壮了,而且学得高高兴兴。
王晋堂把学校与社会连成一片,主张自己的学生应当是“大田作物”,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全方位考验。遗憾的是,他试种的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实验用的“自留田”,他的“大田”也并没有真正与社会连成一片。如果王晋堂的学生因故转学,离开了这块“自留田”,能否适应别的学校的教育体制呢?至少,他们又会被结结实实地绑回到升学的战车上。
真正的“大田”,其实并不是王晋堂校长一个人可以操作的。 跳楼孙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