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渡过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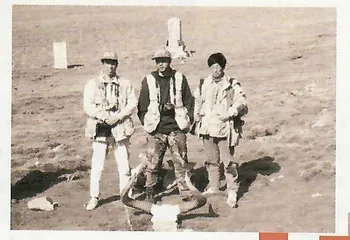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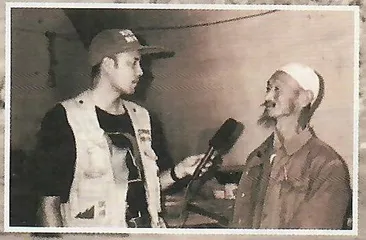
陈强与《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子李高健在陕北
结束了沿黄河流域历时二个月的集群式采访,陈强和他的“黄河的渡过”媒体工程队近30名新闻记者风尘仆仆回到北京。
离开时京城酷暑难当,两个月后已秋色尽染。而对陈强和他的传媒队而言,却觉得又过了一辈子。
初冬的一个下午,记者见到了陈强。
AGEPASS黄河的渡过
记者: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北京对你的作品议论挺多,褒、贬、疑问都有。
陈强:确实有不少议论,但对此我并不担心。一是我觉得这些议论本身就是作品的构成之一;二则我坚信我这一作品存在的理由和人们最终对它的认同。
记者:有种意见对作品的否定是根本上的,即怀疑它是不是件艺术品。
陈强:这个我早有准备。疑问的提出首先是个艺术观念的问题。人们大都以为艺术品无非就是一幅画,一个物体什么的,而“黄河”是什么呢?
这问题说来话长。
本世纪初开始,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画家开始在画布上进行拼贴。这对“艺术只能是手绘”的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突围。1913年,当法国画家杜尚把一个随处可见的小便池搬进美术展览馆的时候,人们无比惊讶地发现:艺术无需制作,只需命名了!
到五六十年代,一些艺术家所对 “艺术是视觉”这一命题本身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艺术不仅是视觉,文字、思想、概念,都可以成为艺术。
万变的艺术形式都是为了一个不变的艺术本质:精神创造的美感和交流。
我以为,以“黄河的渡过”为主题的这一大型多媒体艺术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汇入了世界当代艺术主流。
记者:能不能这样说,理解、接受你这部作品的“结”在于确认:作为一部多媒体观念艺术品,“黄河的渡过”希望传达的是一种思维美感,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取悦于视觉。我们 不能以看一幅画仰望一幢建筑的审美 期待走近它。。
陈强:正是。
我们该怎样渡过
记者:在人们习惯性的观念里, 媒体报道总是对某一艺术作品的评价 和追认,而你却让媒体直接参入你的 艺术创作,从一种工具变成创作本体。 能谈谈形成这构思的思想基础吗?
陈强:“黄河的渡过”媒体工程 队汇集了全国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数十家重要传媒的数十名新闻记者 两个月里,他们沿黄河流域从源头一路东行,跨越11省区,行程近五万公里,从黄河流域带回数十万字的文字报道,160本电影电视胶片,9000分钟的广播录音和近万幅摄影图片,并在科研人员配合下,截取到有重要水文、生态、环保、文化等多重信息的水样土样……。某一时间段里,这些文字、音响、图象等大量原生状态的宝贵资料信息,将随电视、广播、报刊传媒广为密集传播。这些信息作为艺术品,它传播情状的广阔、飘逸与多层次,受众容纳的无限性,不是任何一幅画,一部电影,一幢建筑可以比拟的。
记者:这样规模的艺术工程,它所需要的财力支撑一定也得相当坚挺.那么谁来投资?人家为什么投资?
陈强:不错!如果说,“黄河的渡过”是三足鼎立的话,那么商业社会的支持是其中重要一足。在人们印象里,商业社会是艺术的死敌。艺术家和贫穷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我要打破这一点。
“我有十亿人,长达一年的广告时空,你是否愿意加盟?”。这是我用作找资金、用以谈判的一张王牌。我觉得,艺术家要懂得如何把纯精神的艺术品变成一种流通信息、占有一定空间,再用这个空间跟商业社会进行交换。
记者:能否这样总结你艺术创作模式的基本情状,即艺术行为、多媒体传播、商业社会三者互动,使艺术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进入生活,进而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带来一个充满活力的循环机制?
陈强:是的。这种模式的确立和完善,是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最终理想。
高原·河流·人
记者:接下来我想问,你为什么 选择黄河作为这一艺术行为的思想载 体呢?
陈强:青藏高原我已去了八次。 很难在几句话里说清我对那片高原那 条河的情感。可以说青藏高原是我的 精神故乡。
记者:那个地方究竟以一种什么 样的精神特质投合了你的气质与品格 呢?
陈强:世界之大,在许多地方却 相互重复。而青藏高原却是唯一的。那种坚硬有质感的蓝天,那种四处溅射清澄高冷的原生光芒,那种紫花摇曳一路铺向天边的葱绿草场,都是唯一的。更还有祁连山宏阔险峻的悲剧感,甘南草原原始人性的膨胀,海西无人区上火星般寸草不生的戈壁,藏北高原上的牧人那古葵般沧桑顽强的脸,这一切都已幻化成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生命图景。每次上高原,都有一种海潮般漫上心头的家园感。只有真正懂得了青藏高原,你才会认识到只有这样的地方才孕育得出象黄河那样的滔滔大河。
记者:你刚才强调就个人对黄河的情感而言你选择了黄河,而黄河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特殊形态和地位恐怕也是它最后成为作品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陈强:是的。黄河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几乎成了一个民族的象征。
黄河最初对我的吸引是源于它的颜色。那种昏黄,那种浑浊,那种负载深重的流动,简直就是我们民族的自然呼应,它可以诱发人的很多想象。
黄河发源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从它最初一点一点地洇出草地,清澈透亮,到最后浊黄汹涌,恢宏澎湃,包含了一种生命由萌动到发展,到高峰的过程。
再则,黄河的人文意味也是世界其它大河无法比拟的。从源头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到甘肃宁夏区内的市民百图,再到山、陕、豫的农业文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最后是山东如日初升的现代市场经济,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社会的百年发展史。试问世界还有哪一条大河能折射出如此丰富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
这就是黄河,完整的一个过程,一个生命自然的,社会的,美学的,人性的,全在里面了。许多年来,我一直想以我的方式为它做一件事。现在我有一种践约的满足感。
一个人和一堵墙
记者:从项目构思到你对黄河及水体墙的描述,我觉得你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同时又有着深切悲剧感的人。
陈强:可能是吧。这两种东西也许都要归源于青藏高原的“地气”。那里的天、地、人教会我应当具有怎样的眼界和襟怀。所谓悲剧感来源于对人对命运的审视。
记者:你最珍视自己的个性是什么?
陈强:我很珍视意志的力量,它有时几乎可以突破一个人的生理极限。一件艺术品,其构思奇巧和艺术灵感是一方面,而最终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创造者精神和肉体的承受能力,即一个人的意志力。
陈强:跟你讲我在美国的一次经历吧。现代音乐大师约翰?凯奇在一次酗酒后死了。按计划,两天后,在现代博物馆有一场他的音乐会。那天我去了。因为他的死,到的人数倍于往常。我以为,音乐会开始前,一定会有人发表演说,以示悼念。
可没有。
音乐会开始。美妙的乐声象西海岸的夏风,在每一个人心中吹拂。
我发现,他的死丝毫没有妨碍他的音乐继续流淌。对于一个艺术大师,他的精神与肉体是可以分离的。人死了,可他的精神财富还会存留,还会象四季一样周而复始,还会被人们珍藏。当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就是艺术作为职业的魅力。
记者:最后,关于黄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陈强:我已经有了一个生命的承诺。我死后,将托人把骨灰撒进黄河源区的扎陵湖,让自己的身体残骸为我完成最后一次行为。再看看高原,再看看黄河,我会因此而安宁。 黄河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