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名家手中一卷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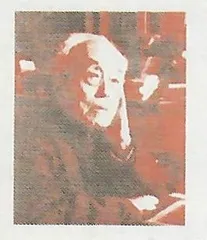
季羡林:常读《陈寅恪诗集》
陈先生的诗艺术性极高,但不易懂。我特别喜欢他说的: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亲、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季羡林 东方学专家,北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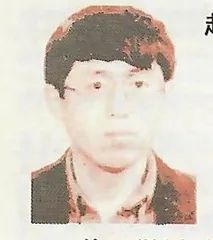
赵一凡:萨伊德和《文化与帝国主义!》
美国学界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后,有关东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文化论战进一步深入。与之相悖,左倾文化批评家萨伊德出力作《文化与帝国主义》,旨在揭示文化层面的殖民潜意识,批判欧美中心论与强权思想传统。但他作为阿拉伯和中东专家,依然无力涉及东亚和中国问题。而中国的半殖民抵抗经历,正是研究欧美东方主义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内容。萨氏深知此题尚未合围,结论有待与东方学者协商,因而呼吁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共存”观念。(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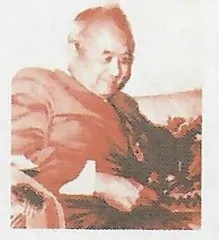
萧乾:为《挚爱在人间》流泪
这本小书害得我老泪横流。它不仅写了海峡之间一段真切动人的骨肉情,而且还勾勒出主人公由孤女而知青而干部的一段坎坷经历。文字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在二十四节图景中,前窜后跳,宛如一首悲怆协奏曲。(萧乾 作家、记者)

陈原:爱上了《贝多芬论》
因为“自我封闭”,孤陋寡闻,竟至于这部书问世两年之后,我才有机会看到再版本。“一见钟情”,我爱上了它。在人们所说的出版“滑坡”之际,居然有人肯编、肯译、肯写、肯出这样的书,真希罕。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间,肯定也不能出这样的书,因为……因为它“歌颂”了资产阶级,“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 “歌颂”了“反映资产阶级的青春”的贝多芬!这部论文集告诉读者,人世间充满了不公平,但贝多芬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从不在跳争中后退”。头一篇是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二七年在贝多芬百年祭纪念会上的演讲——光是为了这一篇(尽管其中的某些论点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这部书就值得拥有。读这部书是一次的真正的文化享受;更不必说去欣赏那一帙可爱的图片了(陈原 语言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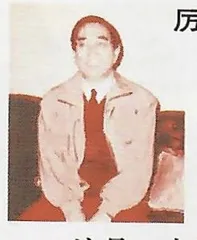
厉以宁:读不厌《宽容》
这是一本给人们以智慧的书,也是一本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信念的书。它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有深刻的哲理。历史的叙述和人文主义的阐发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文笔的生动和条理的清晰,使人百读不厌。从这里,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包括做人的道理和做学问的道理。从大学时代到现在,前后四十多年了,我总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手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享受。(厉以宁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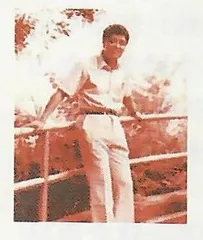
冼鼎昌:重读之乐
去年重读的几本书中,有萧乾的 《人生采访》和斯通的《梵高传》。我的那本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人生采访》,是当年做高中学生时在广州市文德路的旧书店里买到的。一般说来,采访报道的文章经受得起时间考验的不多,《人生采访》里的文章却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掩卷之余,我往往为这些年来这种水平的文章的不多见感到遗憾。不知道他的这本书后来有无再版?(已有再版——编者按)。至于 《梵高传》,以前只是在学英文时读过它的原版,译文确是第一遍读,但内容却读过不止三遍了。时下兴写传记,我以为,斯通写的传记以及对它们的评论,对打算写传记的人们是十分值得细读的。(冼鼎昌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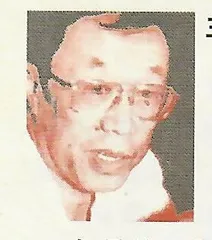
王蒙:绿叶
如果是一个星期以前问我:“1994年你最爱读的书是哪一本?”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罗宗强著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这本书我读起来太亲切了,心领神会,妙悟幽思,默契共鸣,长吁短叹,不免谬托知音起来。而现在,我又想举出金庸的《笑傲江湖》。
有通俗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包装也罢,有武侠小说的套子也罢,有大量篇幅写那些穷极想象、异采纷呈而又终于难脱巢臼的功夫打斗也罢, 《笑》书概括了人生的基本矛盾,不仅是江湖,也不仅是政治工农兵学商各界各色人等,战争与和平,事业与道德,成功与自由,务实与心灵……它们的悖论是怎样地折磨着人!刘正风、曲洋“二”侠之死令人泪下!一周之前,如果任何人断言王某人读武侠小说读出眼泪来,我是绝对不相信的。(王蒙 作家,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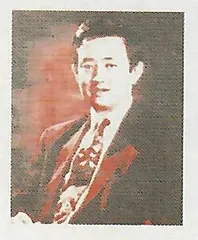
樊纲:财政也是科学
因为研究财政问题,所以要读财政方面的书。其中一本是由唐寿宁先生译成中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按布坎南的说法,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处于严格意义(“狭义”)的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的分界线上(“广义”的经济学现在包容政治学),是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它用经济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既分析个人的政治行为,也分析集体的政治选择,还分析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在布坎南之后,不懂经济学就不懂政治学。就财政问题本身而言,走出财政混乱的最根本途径是建立起一种“财政中的民主过程”。(樊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德伦:我爱读《读书》
我们中国人一向吃闭关自守、孤陋寡闻的亏,在极“左”思潮恶性泛滥时期与外界隔绝。几十年来世界上的文化信息思想潮流什么都不知道,真是闷得够呛。
近年来发现了《读书》这个刊物,通过它刊登各种书刊评论,使我大开眼界。近来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我深切的关注。有时刊登一些颇为隽永有关音乐的文章,相当耐读。是陈四益文配丁聪漫画则更为精彩。(李德伦 指挥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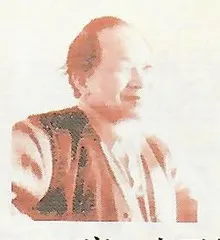
黄苗子:史为明鉴
唐?李百药著的《北齐书》,卷帙字数不多。它把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截取了一个短短的横断面(北齐王朝只有二十八年),从而使我们有声有色地看到帝王将相怎么从战争中发迹,发迹后又如何你死我活地去争夺个人权力。把从民间夺得的全部财富再变为豪门中血肉横飞的争夺目标,导致了中国老百姓长期的民不聊生,构成了两三千年封建史的缩影。这是十年浩劫中,我在静静的铁窗下,孜孜不倦地爱读的一本书。(黄苗子 画家、书法家)1994电影界十大新闻五人谈
年末岁初,我们邀请了电影界及评论界五位圈内人士,列举他们心目中1994年的中国电影界十大新闻。被邀请的人士为: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郑洞天;著名电影评论家邵牧君;中国电影艺术中心副研究员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余倩;《大众电影》杂志记者辛加宝。在他们推举的事件中,电影机制的改革显得尤为突出。按得票多少,这十大新闻依次为:
一、好莱坞大制作影片《亡命天涯》在中国上映。中影公司以分成模式发行“十部大片”,标志电影进口与国际体制接轨,《亡命天涯》在六城市上映一周票款逾千万元。人们对此忧喜交加,议论纷纷(五票)。
二、国家电影局有关电影机制改革的文件出台,发行权力下放。1995年发行市场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四票)。
三、对外合拍影片的管理加强。张艺谋因《活着》的遗留问题未解决而改拍国产影片(三票)。
四、中国电影精品仍然在国际上连续得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葛优、夏雨分获戛纳、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称号(三票)。
五、各国营制片厂施行大规模机制改革,以“准独立制片”经营为特征,创作人员走出自由职业化第一步(二票)。
六、中国开始出现以“创世纪影业公司”为代表的独立制片机构,社会集资形式在制片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并开始瞄准国际市场,向艺术片大制作发展(二票)。
七、“第六代”导演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阳光灿烂的日子》、 《头发乱了》等片引人注目(二票)。
八、夏衍获国务院首次颁发的“杰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他的作品展映揭开了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活动的序幕(二票)。
九、陈凯歌拍摄的《风月》、张艺谋拍摄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影片,掀起“旧上海题材热”,《风月》女主角数易其人,最后静等巩俐(二票)。
十、1994年没有又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中国电影在低潮中寄望于1995年(二票)。 读书文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