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苹果掉到你头上
作者:袁越(文 / 袁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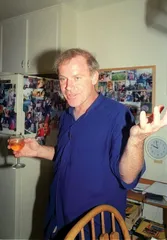
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苹果不会砸中无准备的大脑。很多科学上的偶然发现,背后都有一个像牛顿这样时刻准备着的聪明的人。听说过青霉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吧?当初那一粒青霉菌孢子确实是很偶然地落在了弗莱明的培养基上,但如果他对青霉菌株周围的透明圆圈视而不见,青霉素的发现者就不会是他了。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那么几项发明纯属运气,或者说运气占了很大的比例。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就是一例。他俩证明胃溃疡的病因不是心急上火或者爱吃辣椒,而是一种名叫幽门螺杆菌的细菌。其实这种细菌很早就被人发现了,但一直没能在人工培养皿中培养成功。1982年4月的某一天,沃伦把一块从胃溃疡病人体内切除出来的病变组织放在培养皿中培养。因为那天之后正好是复活节,依照惯例休假4天,沃伦把培养皿放在培养箱里就回家过节了。这多出来的几天假期让培养皿意外地在培养箱里多待了几天(而不是惯例的2天)。结果细菌长出来了!因为这一偶然的成功,沃伦终于得出了胃溃疡病因的新假说,并最终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俩的这项发现意义绝对很重大,但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那么高。历史证明,以这种方式成名的科学家往往沉不住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华。比如马歇尔和沃伦,为了显示自己当初是如何顶住压力,坚持真理的,他俩纵容媒体对医学界反对意见的夸大。其实主流医学界对这项发现的质疑完全是客观、有据可查的,不存在故步自封这一说(见上期)。
当然了,这种做法可以说无伤大雅,尤其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穆里斯(Kary Mullis)比起来更是小巫见大巫。穆里斯发明了“多聚酶链式反应”,又叫PCR。简单地说,PCR使得科学家能够不借助微生物,在试管里将一段DNA分子通过30〜50轮的复制,准确地扩增上百万倍。这项发明有多重要呢?举一个例子,笔者曾经在一家只有30多人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有8台PCR自动仪器,每台同时可以做24个样本。可如果想要用一次,必须提前一周预约!因为排队等着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这一技术,大家知道的亲子鉴定、DNA法医学、遗传病预测、古生物克隆技术等新兴学科就不会存在,而现今绝大多数生物实验室的工作效率也将倒退100倍。这么重要的技术,发明过程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吧?否。这项技术的原理早在70年代末期就有人提出来过,但一直有一个困难无法克服。因为每一轮复制都必须经过一步高温过程,而DNA聚合酶在高温下会失活,因此必须在每一轮复制结束后再添加一些酶进去。这样做极大地增加了成本,使得PCR失去了实用价值。穆里斯恰好在那段时间里看到了另一篇不起眼的论文,有人在美国黄石公园的温泉里发现了一种耐高温的细菌。于是穆里斯设想这种细菌的DNA聚合酶兴许可以耐受高温。结果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一种名叫Taq的耐高温聚合酶被提取了出来,PCR的成本因此得以降低至现在的几美元一次。
因为这个“小发明”,穆里斯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奖后穆里斯辞掉了工作,靠奖金开始满世界游山玩水。他酷爱冲浪,在加州圣地亚哥海边买了幢小房子,天天玩水。玩完水就玩女人,他家冰箱门上贴满了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照片,而这些女孩子都是看中了他头上的那顶“诺贝尔花环”才以身相许的。
再后来,穆里斯玩腻了,又回到科技界。不过,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才能,开始在很多领域四处出击,利用自己的诺贝尔奖头衔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比如,他不承认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也不承认卤代烷(一类化学组织的总称,包括甲烷)是造成臭氧层消失的原因。他甚至质疑HIV是造成艾滋病的病因,在科学界传为笑柄。
由此可见,科学家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那些运气好的人。他们最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万能的神,其实,他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往往比普通人还要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