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戏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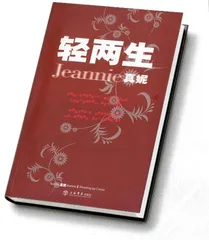
李敖风光大陆行,志得意满。不过他要是在书店里看到《与李敖打官司》(范泓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心里会有些许不快。这本书介绍了李敖与《文星》老板萧孟能的私人恩怨,作者明显同情萧孟能。私人恩怨,读者插不上嘴,当一段八卦看看而已,但李敖是个话题。
1962年,李敖面临选择:究竟是跟着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走,还是跟着萧孟能主持的《文星》走?跟着“文献会”走,他也许会成为一流学者,他的才气见识勤奋足够。但李敖绝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学者,钱太少,名太小,美女不会跟着跑。他最后选择了《文星》。从此,他寄身于媒体江湖,成为靠媒体安身立命,靠媒体扬名敛财,靠媒体发达的第一人。李敖行走江湖,惟一的兵器是言论,他以言论赢得媒体、娱乐大众。他文章不差,但并不能算作家;他书读得很多,但也不是学者。他确切的身份,应该叫言论戏子,或者叫言论明星,或者叫言论表演艺术家。
言论戏子和学者的做事原则大不一样。学者的使命是求真,求得真相,往大里说,求得真理。戏子的任务是出彩,娱乐观众,掌声怎么大怎么来,真理如果是沉默的,戏子宁可选择响亮的谬误。很多时候,言论戏子和学者的看法一样,不过一样看法其实还是两样人。在娱乐化媒体化电视化时代,言论明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知识分子,对凡俗大众来说,言论戏子也远比知识分子重要。不过明星再红也成不了圣人。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戏子一言而为天下笑。
李敖自《文星》亮相以来,一路的战法是说最极端的话,骂最有名的人。他祖籍东北,爷爷当过土匪,他有东北胡子不怕死的凶悍,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以言获罪,坐了五年牢。李敖常以这段历史自豪,把自己供奉成未死的烈士。就算李敖是烈士,也只是他言论秀招致的无妄之灾。作秀也有大风险。今年美国“艾美奖”颁奖晚会上,歌星献唱道:went to jail,got a show,that’s the way entertainment goes——一场表演坐大牢,娱乐就该这样搞。
李敖现在彻底老了,从言论小生变为言论老生。在垂暮之年,他以最低票数当选为台湾的“立法委员”。台湾政治的娱乐化,从一位老年戏子开端。

观书分看和读。曾国藩说:“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关,也不可混。”攻城拓地,铁骑过处皆降土,只要到过就算;守土防隘,百密一疏不为功,讲究涓滴不漏。这几年的新书,值得读,要费心费时强记深思的一本没有,能看看的倒不少。
看也有各种看法。几本书穿插着看,有时还能看出书外的世相。手边凑巧有三位作者的闲书,三位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和70年代生人,参差地翻翻,会看到很多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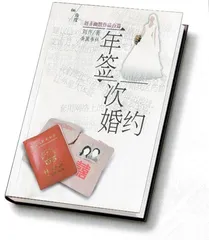
50年代生人(台湾叫四年级生)世故老到。人生已经混过大半辈子,想法越来越实际,有些还很肮脏,但表达的时候嬉皮笑脸,得罪人还不忘往回拉一把,挖苦自己几句。他那本书名叫《一年签一次婚约》(刘齐著,岳麓书社2005年5月第1版),同名文章鼓吹新婚制,婚期只有一年,男男女女每年都能去旧换新,用心十分不堪。但作者假托十几位人物,各方面的意见都讲一遍,不必别人骂街,自己先在头上洒满狗血。看你还能怎么玩?
60年代生人(五年级生)颇多哀怨。《迷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的作者巴宇特是正经的女学者,家学渊源,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岁月中青春作赋。恍惚间竟也步入中年,前尘如梦,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仅二三,文气苍凉。我最早看巴宇特的文章是她在《万象》上写邵洵美和项美丽(已收进新书)。新书叫《迷失上海》,现在的上海所以迷失,因为格局变得太小,小到已经放不下项美丽、邵洵美的奇情故事,让伤心人别有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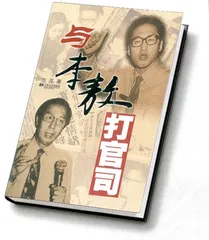
70年代生人(六年级生)目中无人。现在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最近一两年六年级生、七年级生的新书越来越多。新书的设计都不难看,文风也很相近,大都拉长了脸,有一股我行我素不管不顾的劲头。手边新书有两本,一本叫《轻两生》,一本叫《终两边》(真妮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同一个作者,我翻了一遍还搞不清楚这两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本来就没有意思。这类书的作者目中无人,一是没有前人,不在乎写作的起码传统;一是没有众人,不在乎花钱买书的看书人能不能看懂。或许看不懂才叫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