嗡声作响的出版工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于萍)
关于康泰纳仕的初始,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老先生在结婚周年纪念时买下一个出版公司,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而这位妻子不过想要本时尚杂志。关于故事的男主角,有两个版本:一说是1909年的Conde Nast,他买下的是一个叫《Vogue》的曼哈顿生活手册周刊,受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风潮”影响,这本杂志发展为倡导物质生活、强调阶级意识的时尚月刊,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康泰纳仕出版集团;另一说是1959年的富豪Samuel Newhouse,他买下的是整个康泰纳仕出版集团,并不断收购、创办新报刊杂志,将其扩张为国际出版集团。
故事的男主角是谁已不重要,时至今日,康泰纳仕已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集团,在全世界20个市场出版107本杂志,经营63个网站,每月读者数量达1.2亿。
对这个出版集团最顺理成章的想象是:有钱有势、财大气粗。他们通过一系列杂志高调倡导奢华生活,同时又十分具有警戒心,集团如何运营显得神秘莫测。美国《财富》杂志说:“没什么比嗡声作响这个词更适合康泰纳仕了。”但1998年的“《纽约客》事件”仿佛在这个出版工场的围墙上炸开一个小洞。《财富》报称,《纽约客》自1985年被康泰纳仕收购后,一直在亏损,到1998年,已亏了1.75亿美元。由此引发的是亲兄弟自相残杀(当时《纽约客》的主编汤姆·弗罗里奥被炒了鱿鱼,他的亲哥哥是康泰纳仕执行总裁史蒂夫·弗罗里奥),拜物派入主(《纽约客》新任主编蒂娜·布朗曾任《名利场》主编,著名的造钱机器,她被怀疑能否办好一个人文杂志),以及众多非康泰纳仕旗下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做出延伸报道:康泰纳仕实际上一直在赔钱摆架子。
但《纽约客》并不代表康泰纳仕,出版集团其他杂志的运营情况仍被藏得严严实实,惟一可以窥见的,是整个集团的奢华开销和编辑们的待遇。2004年,美国版《Vogue》为了拍摄一组图片动用了以下物品:80只小白兔,17只鹅,250只喷成金色的鸵鸟蛋,一盆巨大的橡胶手,一个放满白色雨伞的房间,20棵圣诞树,此外,他们发现租一辆劳斯莱斯还不如买辆旧的合算;戴安娜王妃在世时,美国版《名利场》付给海德公园博物馆100万美元,要求杂志记者在晚宴时刻能够坐在王妃邻桌,以记录她的一言一行⋯⋯Slate网络杂志曾在调查了39位康泰纳仕新老员工后,为这个出版工场的员工待遇列出清单:康泰纳仕负责员工的一日三餐,午后甜点;从出差的头等舱、接送上下班的林肯房车,到送给同事的生日卡片,统统由出版集团买单;集团所属主编每年有5万美元置装费;《GQ》主编有两栋超过各100万美元的房子;《纽约客》主编在曼哈顿区的豪宅价值370万美元⋯⋯考虑到康泰纳仕旗下杂志所倡导的生活,这样的报酬也许更利于员工展开工作。
实际上掌管康泰纳仕的Newhouse家族身家45亿美元,集团是该家族的私营公司。在外人看来,康泰纳仕赚或赔看热闹的成分居多,并不真正关心。而这几年Newhouse家族一直对外宣称,康泰纳仕的利润稳中有升,同时也不讳言奢华做派,执行总裁史蒂夫·弗罗里奥有句名言:“烧钱对创造力来说异常重要。”康泰纳仕保持一贯大手笔的派头,开拓了更多国际市场。今年8月,已在全球有15个版本的《Vogue》进入中国,创刊号有十多页写满了国际国内时尚名流的祝福赞美。

康泰纳仕国际公司现任董事长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是家族产业开拓者Samuel Newhouse的侄子。记者在9月2日见到了他。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康泰纳仕集团初始的那个著名故事⋯⋯是真的吗?这个故事曾被用来表明,你们家族在经营Conde Nast集团方面非常理想主义,不大在乎钱,却很在乎精神,你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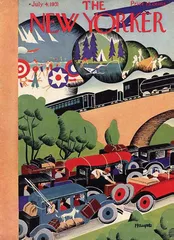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这的确是个可爱的故事,但它不是真的。我叔叔是个非常厉害的生意人,绝对不会因为情感原因投资一桩生意。但这个故事关于我们家族在乎钱还是在乎精神的暗示,基本可以说是正确的。我们的杂志一直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验,通过聘用最好的记者、编辑、摄影师来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帮助读者实现梦想。商业利益与之相比,位居其次。
三联生活周刊:你记忆中,Samuel Newhouse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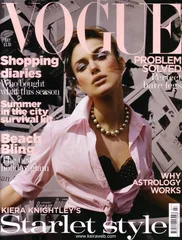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他是个让人惊奇的人。他非常硬朗,做生意直来直往,切中要害,同时也有一副热心肠。如果为他拍一部电影,我觉得让枪战片明星爱德华·G.罗宾逊来演最合适不过,既是个硬汉又很温柔。我的叔叔从小就很勤奋,并极有商业天分,吸引了许多人才。我25岁的时候,还在《Staten Island Advance》杂志工作,叔叔已经80岁了,还经常来视察,他每年要干的一件事是查看圣诞奖金发放表,然后总说同一句话:“我们要到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发奖金呢?”这话的意思是提醒我们要勤奋工作。他也是个直言直语的人,从不表扬别人,如果他不批评你,这就意味着一种表扬。他给整个家族定下了很高的标准,至今仍在执行。比如美国最近遭受飓风,受灾最重的新奥尔良有我们的几份报纸,家族成员会去当地查看,或者打电话、写信慰问,为他们提供帮助。这种忠于和关怀员工的做法正是叔叔强调的。
三联生活周刊:曾有报道说,你们的杂志不在乎发行量,却非常重视广告收入,你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有些公司认为杂志卖得越多越好,这不是Conde Nast的经营理念。我们的目标是选择性地吸引有品位、懂得欣赏美,追求时尚的读者,从而自然吸引广告商。
三联生活周刊:有报道说,《纽约客》杂志虽然受欢迎,发行量不错,却因为广告收入不高而一直在亏损,你怎么看?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按照公司原则,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财务问题,但关于《纽约客》的报道的确很多,这里破个例。Conde Nast集团1985年买下《纽约客》,最初确实不挣钱,但大概在5〜10年前,它已经开始赚钱了。
三联生活周刊:Conde Nast集团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主编,他们有的极有个性。一般你会雇用什么样的人?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我们有些主编非常光彩照人,有的却不那么让人激动。他们的个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业绩。我想那些知名的主编并非因为有个性我才雇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加入到Conde Nast集团,才变得很知名。如果概括我的员工特点,他们必须很勤奋,富有才华,理解读者的需求,同时具有团队精神,能吸引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他们的待遇很不错?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他们勤奋、能干,他们值这些钱。
三联生活周刊:意大利版《Vogue》很雅致,也很清高;美国版《Vogue》则很实用,中国版《Vogue》总体上会是什么风格?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中国版《Vogue》会接近美国版。不同市场有不同需求,意大利有非常成熟的时尚设计产业,这决定了意大利版的做法;而中国市场与此不同,在中国,《Vogue》将致力于为中国女性提供实用的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Vogue》进入中国市场后,与其他时尚类杂志的竞争?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我不认为存在竞争。中国已有许多时尚杂志,他们做的与《Vogue》做的并不相同。我不关心别的时尚杂志做什么,我只关心《Vogue》的品质,并力求做到最好。
三联生活周刊:除《Vogue》外,Conde Nast集团有将其他杂志投放到中国市场的计划吗?比如《名利场》、《纽约客》等。
Jonathan Edward Newhouse:我非常希望Conde Nast集团的其他杂志在中国进行版权合作,但这需要取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许可证,要花上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努力,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现在不能确定。■ 嗡声作响康泰纳仕出版工场vogue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