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财气见人性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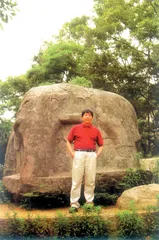
李零的杂文集《花间一壶酒》新近出版,虽然几乎没有新作,但结集出版好像是借着那一壶酒劲试一试身手,在专业之外讲一讲现实中的道理。
比起现在那些天天专注于社会状况的专栏作家,一般情况下,学者们的杂文并不那么讨好,或者偏酸,过于闲适,或者微言大义,不免空洞。原因可能就是李零说的:在学有分科的学术圈里待时间久了,出了圈儿那水平不一定比摊儿书高明。在圈儿内,李零是考古学家、古文献专家,《孙子古本研究》、《中国方术考》、《郭店楚简校读记》之类的专著是他的身份证明,有了这些之后他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说很现实的事了,不仅现在的事不敢讲,明清的、民国的事也不敢讲。就因为没做过研究”。“但生活现实中的历史和学问中的历史其实是同样的历史,因为专业的领地是很清晰的,那我就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书一开篇,他就明说了:这本书所关心的凡人小史都是“在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的”一些事情。这些出了他专业圈儿的事,由于脱开了学术规矩,他的叙述就显得直接,古今直接挂钩,有些地方甚至是简单地一笔扫过,但效果强烈。从“9·11”说起恐怖主义,就说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刺客,如曹刿用匕首劫持齐桓公,之所以成功地替鲁国要回了被占的土地,“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附带着说到在上海博物馆的楚简中发现了曹刿的“兵法书”,他借此说明恐怖活动和兵法不是对立的东西,“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而荆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千古绝唱,在电影《刺秦》里“主题很前卫,秦王要搞全球化,但太残酷,荆轲代表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这种傻问题”。
能看出来,李零在这里是想说一些立场和价值观方面的道理。他非常清楚“在公众文化那里,决定阅读趣味的主要是立场和价值判断”,而这种东西是不能讨论的,所以他只是因为关心所以表达一下。所不同的是,他更像一个冷眼旁观者。
虽然说是在学术之外的话题,其实在很多题目中,他还是非常温和地利用了他的学术背景,所谓“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的题目”。话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九州是大禹用脚丫子走出来的。⋯⋯什么是禹步?”这个看似是个小趣味的事情却来自最专业的考古新发现。“卜赌同源”、“药毒一家”里面,很让人联想到他的《中国方术考》,不过在这本书里,他讲的是人类的两大劣根性,读来即是家常道理,又在他的循典推演中长了见识。《避暑山庄和甘泉宫》一篇的话头应该是“当今世界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他就来讲讲中国古代的“五族共和”,汉朝的甘泉宫好像也是他考过的题目。我曾为汉朝宗教的话题采访过他,那时他一直欲言又止,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讲究,而在这些杂文中,他笔下的事情一下都变得中外纵横恣意,古今来往无阻。
这其中的转折也是经过他一番思量的。他的根据来自中国源远流长的通俗史,他说:“通俗史就是把古今混为一谈,这是中国说古的传统。现在畅销的历史书,如《潜规则》都用的是通俗史的方式。老百姓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人生活的历史尺度不一样,在通俗史里,不在同一个时间框架里的人就是能相遇,关公战秦琼都是有可能的。比如在历史戏里,学者在那儿研究服装道具符合不符合历史事实,观众根本无所谓,这些历史细节都可以忽略,人们一般关心历史都是文学化的关心,历史上越是被轻视的,在民间就特别被同情,比如李将军和卫青,卫青因为没有文学的同情,差不多被人忘了,李广则活在了文学里,就被世代传诵,成了飞将军。孔子也是同样的,‘文革’一批孔,现在他就成香饽饽了。这种方式虽然很不符合学术的方式,但也是很有道理的。专业的研究会得到很多知识,但也能造成一隅之见。知识和明白事理不一定一样,我想试着用杂文的方式在这二者之间穿透一下。”
即使在学术研究中,李零也做了一些不是他专业的课题,因为,按他的说法,学术有分工,但问题没有分工,学术分科就留下了很多死角,像房中术,医学不研究,文学不研究,宗教不研究,就成了死角,方术、战争等课题中的一些部分也是被学科划分漏下的。这些死角的研究倒也不是时髦于学界的填补空白,而是被他当成理解大历史的一些杠杆,这些问题可能和大的问题靠拢。房中术中的一些问题现在可以变成谈男女关系、性别研究;方术是为了讲中国的宗教传统。而酒色财气中研究人,能洞见人性。■ 人性酒色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