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酌无相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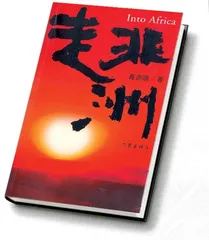
李零是北大的教授,当然的“知识分子”,当然的“学者”,但他以为比“知识分子”、“学者”更受听的称呼是“读书人”。他说:“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外国多,后者国内多)。”
他新出的文史随笔《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有些许酒意,无半点花色,大多是正经学问,不过《花间一壶酒》里的学问并不枯涩,好些段子能拿到饭桌上去聊。眼下能把学问做成掌故的,肯定是高人。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点勉强,但文章好玩,故事好玩,作者的发挥也好玩。他说到中国古代的兵家吴起,吴起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他被政敌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么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作者随后议论道,吴起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中国人用心深刻,有时候真是神鬼难料。
作者给自己的新书取名《花间一壶酒》,我猜他的牢骚是“独酌无相亲”。他虽然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心情却很差,“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北大教授,出校门混上一圈,差不多都会被尊为“大师”,只是到了李零笔下:“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
不管李零骂街是不是过头,现在北大——乃至全国,“大师”肯定比“读书人”多。

葛剑雄是中国历史教授,冯骥才是小说名家,几个月前,他们都有新书问世——《走非洲》(葛剑雄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民间灵气》(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但新书与他们的本业无关。葛剑雄的新书说的是他两年前在非洲的走马观花,冯骥才的新书则是他民间采风的记录。这两本书都是越界写作。
冯骥才的《民间灵气》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作者偏爱民俗文化,他的“田野考察”的表达方式却不是十分得体。人文知识的发布,要么用西式的学术论文,要么用中式的掌故笔记。论文什么问题都能说,但讲究出处、根据、源流,要让读者看到你的研究过程,不能做无根之谈。笔记胜在有趣,可以以道听途说为学问,写作姿态不必十分紧张,不过中国的笔记传统不尚空谈,从来不去触碰大问题大概念,用心只在小故事小心得小乐趣。现在最不靠谱的就是所谓“学术散文”,上下古今东西南北一锅烩,对文章里的知识来历不做任何交待,常常顶着学术的名义以浮谈欺世。坦率地说,冯骥才这本书多少受到余秋雨式“学术散文”的影响,把自己奔波得来的好故事放在一个尴尬的壳里。
作者在“自序”中还专门说到文体,他“发觉被文学研究者硬性地分类为散文、随笔、批评的种种体裁之有限。于是,在这次的写作中决心拆除各种体裁间的藩篱,将散文、随笔、研究、批评等等一起混用。我想,非此不能表现我这种复杂的内容”。
其实,混乱的文体并不能说明复杂的问题。如果《民间灵气》写成传统的笔记或游记,读起来会舒服很多。
葛剑雄的《走非洲》倒是一部游记。他是应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担任电视片《走进非洲》的嘉宾主持,参加了一次由媒体买单的非洲百日观光,新书就是观光的产品。
《走非洲》写得中规中矩,但并不精彩。这不能全怪作者,当下中国学者文人的悲哀在于他们出游通常都是别人买单,基本安排都由出资人控制,游记的私人性质于是大打折扣。花别人的钱写不好自己的书。■ 相亲独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