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力量的,充满灵感的,粗暴的 ——普拉达、库哈斯智囊团AMO、“Waist Down缪科雅·普拉达:艺术和创作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崔峤 王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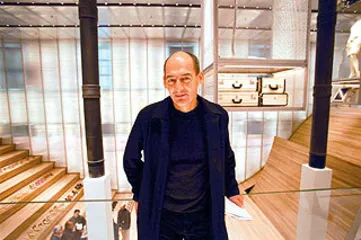
普拉达大牌的近亲艺术
普拉达在全球有176家精品店,并不算多,真正成为数一数二的超级名牌也是80年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女装部分始于80年代,男装更是90年代才“迟迟”起步。低调但极骄傲的特色在普拉达网站更是发挥到极致:网站只有惟一一幅页面,页面上比例完美地只挂着两幅最新一季的女装图片,仅此而已。
毫无疑问,普拉达绝对是当今时尚界的超级领袖,设计创新但简单实用,工艺及材料标榜“最精良”。相比于其他国际时尚品牌,普拉达最突出的地方是它的企业文化已经跨出了时尚界的小圈子,出落得更加“艺术化”。究其原因可以称得上非常个人化,第三代掌门人和首席设计师缪科雅·普拉达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物:政治学博士毕业却热衷于联姻各种前卫电影、摄影、建筑、艺术、哲学、科技;成立支持当代文化的非赢利基金会,并且在米兰拥有自己的艺术展览馆;资助威尼斯电影节和纽约Tribeca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期间为自己出品的艺术电影大搞迷幻Party,东柏林一个闲置的游泳池竟然有西斯汀教堂彩色玻璃般的迷幻效果。普拉达最为著名的是它开在全球各地的分店,都由库哈斯和赫尔佐格等世界顶级建筑师设计,每每落成就自动进入世界建筑史的必备条目、艺术界争论或者仰慕的焦点。库哈斯设计的普拉达纽约旗舰店2001年12月开业,斥资4000万美元,占地2100平方米,更像一座美术馆,“改变了零售方式的新途径”,把一个博物馆的空间、一个商店的空间、包括一个旅游者的空间完全共享了。在普拉达艺术帝国,科技、建筑、电影、摄影、艺术、哲学就像近亲,时尚产品也更像一幅幅视觉与装置艺术品。
普拉达有意在上海开设分店,并将其建成全球最大的旗舰店。赫尔佐格和库哈斯为此激烈竞争之际,由库哈斯智囊团AMO负责策展和实施的“Waist Down缪科雅·普拉达:艺术和创作展”在上海先行开幕。这个女裙展被命名为艺术展,沿袭普拉达的艺术哲学,故意和时尚展划分界限,在空间选择上就独具匠心:避开了传统的艺术展览馆或者时装秀展场。和平饭店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的沉着历史感和普拉达经典百款女裙的大气前卫相应成趣。饭店顶层露台凌驾于灯火辉煌的外滩上,参加开幕晚宴的国际嘉宾衣香鬓影,鲜红的巨大国旗旁你来我往,非常上海式的资本主义和糜烂有趣。
半个月的展览采取了半公开形式,嘉宾只有被邀请才能进入饭店的一楼大堂和走廊,左右挂着两列几十个2.5倍人高的绝美模特图板:身着普拉达女裙的大型下半身照片,灯光被图板背后的镜面反射,昏暗的通道便变得光亮起来。出了七层电梯,就看见几条内藏着小型电机的婀娜女裙不停地飞速旋转,如同骄傲飞扬的动感雕塑。套房门外的行李车上也悬挂着两条自动跳舞左摇右摆的裙子,舞姿优雅而保留,有如真人一样渗透着腰部以下动感的美丽。展室是在七楼的三个不同风格的套房:中国套房、美国套房、英国套房,不同的动感设计各自出位:真空压缩的三百六十度裙装像一幅幅抽象画;金属束腰模特的独立姿态曼妙冷静;观察细部的放大镜可以惊叹孔雀翎毛等材质的优良;如同摄影棚一样的灯光和投影可以衬托展品的剪影、透明和发光;坐在白色浴缸边的坐式模特也都别出心裁地穿着超短裙,双脚在肥皂泡里游戏;床罩和墙纸上也能仔细辨认出藏在同色花纹图案中的各款经典女裙。

OMA和AMO
这个展览最吸引人的其实是它的策展团队大都会建筑设计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简称OMA)旗下机构AMO和“处理”时尚的态度。库哈斯的OMA团队具备这个时代少有的敏锐政治触角和涉世意识,在具体项目的实践中,融入许多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市场、消费行为、媒体文化的观察和批判。而于90年代成立的库哈斯智囊团AMO被称为哈佛军团,他们的任务却恰恰是致力于建筑之外的独立研究,提供策略性的创新思维,延伸库哈斯本业之外的创造性。同时通过咨询、技巧、才干、创新的技术发明、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又反向影响了OMA的创作。

在专业上,建筑被定义为一种能为世界增加一些内容的活动,建筑学业界曾经被看作太具工艺性而“显得落后”,但是AMO具备了一种延伸建筑学活动的范围所需要的判断力和“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它的哲学思想明确地决裂于风靡这个行业的空间自恋、技术崇拜和材料恋物癖,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形态:通过对虚拟领域的信息运用彻底改变了建筑的这种思考方式。他们质疑组织机构,身份形象,文化背景,功能及编排,并在观念层次和实用操作层次上重新定义当代社会现状的新可能性,将之糅合成为没有钢筋混凝土的、非物质的“虚拟建筑”——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建筑”。现在AMO的研究项目:共产主义史的研究;为哈佛大学的文化发展建议概念性蓝图;普拉达时装店开发店内的应用科技;为《连线》和《幸运》杂志重新制订形象;由欧盟委托制作的欧盟视觉新形象和布鲁塞尔的欧盟展览。AMO为欧盟设计的展览更是“铁骨铮铮”:为欧盟重新设计了“彩色条形码”旗帜,用图片拼贴的方式展示欧洲野蛮杀戮的历史,更针对欧盟成员国所必须符合的8000多个条例设计了一本长达5米半的巨书,作为政治壁垒的隐喻:欧盟本是欧洲社会企图超越国家政治、杜绝地区冲突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这个美好理想的实现却充满超越所有想象力的艰辛和怀疑。
时尚与艺术的婚姻质量
库哈斯率领哈佛的研究生团队和AMO团队专门研究了三年“Shopping”:“对购物最好的比喻就是一头正在死去的动物——一头与死亡挣扎的大象才能做到自我完整和不被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会使人们产生饥饿感,建筑正用来填饱这种饥饿感,购物也可用来填饱这种饥饿,它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公共活动方式。”当今时尚界运用“迪斯尼乐园”般的经营方式,在轮番高潮的引诱下,消费者表现出的饥饿、真实、固执的确最能直指人心。
团队还发现了时尚购物和艺术之间的暧昧:各大美术馆的购物收入已远远大于博物馆本身的收入,MoMa的商店每平方英尺收入平均就有1750美元,而一般的购物场所每平方英尺才250美元。在今天,一般的消费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人们要求体验,要求被塑造,要求“发现自我”,要求“给我一点感觉”。豪华品牌店运用一系列绘画、实验材料和颜色的样品、照片、海报、幻灯、录像等形式,人们经常被偏移着引入一种超级消费情境。
新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有个名言:“美使人们感受到自身,使得他们更政治化,因为对于面前的事物,他们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力,一种潜力,一种理解。”设计北京奥运体育馆“鸟巢”的建筑师赫尔佐格也承认:“我们想使我们的作品有吸引力,我们想吸引人们。因此我们必须插入他们的系统中,变成他们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发展自己的一个聪明的概念,一个聪明的策略。如果你成功了,如果你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人们的感觉、直觉和智力上——吸引了他们,他们就能理解你的作品。这涉及到引诱他们,使他们参与进来,让他们兴致勃勃,打开自己的思想。这不仅仅是创造一个美的物体或美的表面。”相对于20世纪的“拥塞文化”,库哈斯推测21世纪是“传播的文化,分散的文化”,各类艺术形式的关系如今更倾向于互补,关注探讨各种可能性的融合。
建筑大师的思想工作
库哈斯和他的团队总是这样思想先于行动。跨越东西古今,建筑师库哈斯在当今的中国仿佛是千手观音和人头马的混合体,万花筒般奇异梦幻,无所不能。在更多时候,他的“疯癫和野蛮”,翻译成不那么含蓄的中文就是“天才和激情”。被《纽约时报》评为“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的库哈斯更能超越其上,他的理论建立在生活各个领域和广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堪称惟一把社会现实和当代艺术完全作为跨学科的课题来对待的建筑师。
库哈斯对待时尚和城市的态度如出一辙:看过太多喧嚣混乱的世界,库哈斯反倒能从容淡定地建议应该适应城市现状而不是革命性对抗,对都市的不可知性、不可维护性、不可管理性和不可尝试性的狂热超越了对都市本身状况的热爱。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城市的现实和突变,对创造“美丽”和标榜个人风格的建筑、隐蔽当代现实问题的“工艺性”建筑则完全不感兴趣,按现在的常规建筑观念来看颇有些“反建筑”,在业界毁誉参半。
“所有人都抱怨我们面临无差异、无特色的环境,我们说,我们要创造美、可识别性、质量和秩序。但也许,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城市就是我们所最渴望的,也许没有任何个性本身就提供了最好的生活环境。城市中的建筑代表的都是些欲望妖怪,城市就是欲望的约会。城市已经变成了无数零碎的、不确定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不美的,多元的细节。既然如此,我们还不如服从于城市的现状,进而参与到城市的未来。我原来认为是沉闷沮丧的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充满灵感,粗暴的。”
国外媒体比喻库哈斯是“圣坛上高大而憔悴的圣人”,有异端一样的外在形象和复杂经历,也有异端一般的超人感染力和万变能力:“建筑师心中要有一种欲望,并且要善于物化它。”身为解构派建筑代表之一,他更像一个街区里最坚忍也最粗暴的小孩,对待任何概念总像是一个绝对武断的“疯癫”思想者,他的妻子也曾经揭发“他有一套理论,并能将一切材料都纳入这套理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行动上同时具备超人的能力和现实性的暧昧。 非常充满粗暴灵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