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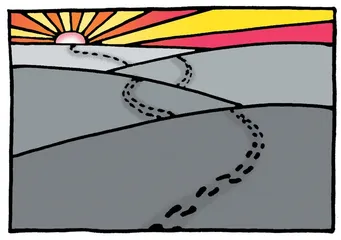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四海为家,倘得志,至少得搞上一次“锦还”;若夫日暮穷途,马倦人乏,中国人讲究的乃是“生还”。明人王季重先生曾欲于出入越境的必经之路西陵渡口(在今浙江萧山之西)的空阔沙埂上置二亭,一曰“锦还”,一曰“生还”以“憩归人,勉去人”:“凡稍得富贵,随其力之所及,以不负虚往者,憩锦还亭以劳之;即不得富贵,而尤能奉身以还,见其祖宗之墓庐者,则生还亭尤可憩也”。
总而言之,出来行,迟早都是要还的。若既不能“锦还”又不能“生还”,正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客死异乡之人,最理想也是入家乡的乡土为安,尸还。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亦世之常理,也不独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活人无国界,死人却有故土——和平崛起时代国人的理想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安排。其犹如持手机全球漫游,到缴费时,还得乖乖回到原居地的中国移动营业点。
道德人伦层面的事儿,好说,一落到技术层面,往往就比较复杂了。死人还乡,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仁至义尽的物流方式:
一、使用交通工具进行长途运输。有条件的,用飞机空运最为快捷,因为机上有专门装置,一路上还可保持冰鲜状态。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阵亡者被空运返美,这个大家在电视里已见得多了。没条件的,通常就会动用到飞机以外任何机动或非机动的交通工具。
二、以人力搬运为主,配合公共交通工具联运。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最近有报道说,湖南农民左某猝死福建,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61岁的同乡李绍为等4人,将死者遗体装扮成醉汉,乘火车准备不远千里将尸体背回老家落葬,在广州转车时被警方撞破。
这批老乡虽然都是衡阳一带的人,不过我还是觉得,某种意义上,“千里背尸”其实就是湘西“赶尸”的现代翻版。《清稗类钞·方伎类·送尸术》说:“西人之催眠术,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而黔、湘间有‘送尸术’,则以死尸而由人作法,进止听命,可历数月。”此种蛊术据说出现于清中期,作用是把客死四川的湘籍移民的尸体走水路运送回乡。行至三峡一段,风险极高,惟有上山,但那几百公里的山路极不便利于交通工具,遂有纯人力之赶尸兴焉。
死尸怎么会听话地被活人赶着走,据知情者揭发,赶尸利用的是尸体大关节上的残存弹性,“如髋关节,在外力作用下,(死后)还是能有小幅(20度)活动的,这就是Dead man walking的物理条件之一”。又,“把两个尸体,排好队,伸直前臂与地面平行,然后用细长竹竿顺着手臂以绳索固定,使两尸连成一个立体架子,不会翻倒(这就是为什么要两个死人的原因)。拿一个绳子连在第一具尸体上,然后在另一头用手轻微用力一拉,尸体在外力作用下,就像提线木偶一样歪歪斜斜地直立行走起来。事实上这样还不如叫‘拖’来得明白。故每次赶尸,必须有两具以上的尸体,不然就不叫赶,叫‘背’,找一个胆大的把死人背回去就得了”。另据报道,1949年曾有两名大胆的解放军在四川和湘西交界处持枪喝停赶尸者,经检查,结果发现尸体是真的,但“迷信”的奥秘在于赶尸者乃是把尸体“挂”在身上,再用一件长大黑袍罩上,只凭耳朵听前面另一名赶尸者指挥。如此这般,两名赶尸者轮流替换“挂”尸的工作。
没有人认为千里背尸乃是赶尸的重演,更没有人指责其为制造恐怖,制造骗局,因李老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机。除广州警方依法制止了这一行动外,广州有舆论盛赞千里背尸为“义举”:“尽管偷运尸体不值得提倡,分析了传统民俗对李绍为等人的影响后,我认为李绍为身上体现的,是中国农耕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美德:朋友邻里同乡之间要相互关照、侠义为怀、诚信为本。”
李老汉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城里人的喝彩声。再者,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美德也不止上述三种,浸猪笼、守活寡以及立贞节牌坊之类,也不能排除在外吧。当然,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上对农耕文明说三道四,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只是就赶尸或背尸一事而论,内行的沈从文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对于赶尸传说呢,说来实在动人。凡受了点新教育,血里骨里还浸透原人迷信的外来新绅士,想满足自己的荒唐幻想,到这个地方来时,总有机会温习一下这种传说。”看来,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来赞颂农耕文明,想必也道德不到哪里去。
李老汉说:“在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了赶尸确属湖南传统,活见人,死见尸,则放之四海皆准。否则,南亚海啸的救灾工作也不至于要面对那样艰巨的技术难题了。问题在于尸要怎么个见法,是活人去见死尸,还是死尸去见活人。沅陵是我的祖籍,身为赶尸术发祥地的后裔,我衷心地希望在技术条件尚未发达至人道主义同等水平之前,在哪里跌倒,还是以不要在哪里爬起来为好。至少,我死之后,千万不要把我“赶回”湘西。 还乡湘西赶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