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或游览
作者:王星(文 / 王星)

《达芬奇密码》推动了巴黎的旅游业,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非卢浮宫莫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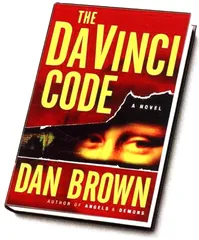
丹布斯小说《达芬奇密码》
说起来也是惭愧,在巴黎呆这么久了,居然还没进过凡尔赛宫。除了“书非借不能读”这层原因之外,倒也还有个理由给自己辩解,那就是其实我早就在游戏里把这个著名宫殿的内部转了一遍。那游戏中文名叫《凡尔赛:宫廷疑云》,很古老的游戏,操控不方便,人物和场景在现在看来也显粗糙,估计一般没人会玩。但那游戏的好处就是把调查案件和介绍凡尔赛宫结合在一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尽可以用鼠标随意点开某个大厅里的装饰油画、看看它的作者,或者是点选某个人物、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什么的。这比在实地挤作一团急不可耐的旅游者当中听导游声音时高时低的讲解从容得多。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游戏在操控方面的缺陷,迫使我一定要记住宫中各条通道,这样才能少走冤枉路。靠一个游戏证明自己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听起来不太可靠,不过我自己确实有亲身体验:做这个游戏的公司还做过一款名叫《紫禁城》的以故宫为背景的探险游戏。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故宫也不知去过多少次,但玩过这游戏我才知道“军机处”到底在故宫的什么地方。
当然,总有些东西是必须亲眼看到才能感受到的。这就涉及到巴黎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卢浮宫。卢浮宫里最著名的当然是那位《蒙娜丽莎》。第一次站在她面前,我的确有些震惊,不是因为她的微笑,而是因为她太小了。虽然我早就听说过她在这几个世纪里因为偷盗等原因被切割过好几次,但她的尺寸还是令我惊诧:市面上一般的《蒙娜丽莎》500块拼图都比原作的尺寸大。至于那著名的“微笑”,我的心里仍保留了早年在一本美术史中看到的那个微笑——尽管那本书的印刷有些粗糙,但蒙娜丽莎的脸总比那张在卢浮宫里隔着层保护玻璃再加以来自各个方向鬼鬼祟祟的闪光灯反射的脸显得真实也神秘得多。
作为博物馆的推广手段之一,卢浮宫也出过一个探险游戏,我没玩过。从游戏要求的电脑配置来看,估计也是有些日子的东西。但如今在卢浮宫可玩的最大的游戏仍旧是和《达芬奇密码》那本小说有关的。作为一个嗜好看侦探小说的人,这么晚才看这本热门侦探小说有点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我确实对当代的欧美侦探小说没多少信心的缘故。这本书作为“侦探小说”并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毕竟书中提到的圣杯与女性神崇拜什么的早就在弗洛伊德的著作或者《圣杯与剑》这些书里的说过了(书中没有把弗洛伊德也算作那个隐修会的成员倒是很有趣),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书中对巴黎和巴黎周边景点详细到炫耀的介绍,完全像本导游手册。事实上,也确实是在这本书畅销之后引发了一股美国人来巴黎旅游的浪潮。
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卢浮宫展开的。据说现任的卢浮宫馆长也并不反对游客捧着那本小说来卢浮宫玩“探宝游戏”。书中提到那么多的艺术品,真正让我产生共鸣的却只是一个厕所。正如小说所说:要想好好欣赏卢浮宫馆藏的艺术品大概需要五天,但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一种所谓“轻型卢浮宫”的游览方式,也就是只看卢浮宫里最著名的三大件,而看完三大件的最快时间据说是5分56秒。我没那么大本事,而且要考虑到被陪同游客本身的能力,目前只能最快在15分钟内解决问题。以自下而上的顺序走,一般我陪同的游客会最后看到《蒙娜丽莎》,回转后到走廊尽头要求上厕所、也就是小说主人公借机逃走的那个著名厕所。不经意间,我倒成了所谓“达芬奇密码主题旅游”的先行者之一。
《达芬奇密码》和由它兴起的各种游览项目更加深了我心里早就存在的一种怀疑:如果给我一个机会进凡尔赛宫,我是否真会进去。也许我会害怕里面的人潮破坏我在游戏中得到的那种伴以巴罗克音乐的有条不紊的感觉。我已经在尽力忘记卢浮宫里的那幅人头攒动中的《蒙娜丽莎》,如今卢浮宫真正吸引我去亲眼看看的大概只有一幅画:华托的《丑角》。我以前没想到它留在了卢浮宫,虽然在游览图上看到了它,但我第一次也差点没找到。它当然是在“轻型卢浮宫”的游览路线之外。当我终于翻转几道楼梯找到它时,它就静静地挂在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走廊里。它的寂寥如同它的标题,它的大小超乎我的想象——那不是一个游戏能承载的图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