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都是苦出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爱情有多伟大?爱情有多文化?不管爱过没有,答案多半会是天花乱坠,不知所云。
尽管CCTV的超级女声已将出现在奥运开幕式艺术表演第四幕上激光投射的DNA双螺旋结构解读为“人类在2000年发明了DNA”,不过她的前一句大抵不错:“历史也就进入了现代”。除了DNA之外,“历史进入了现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我认为就是生化科技对于“爱情密码”的破译,因为它终于完成了弗洛伊德未竟之工:LOVE=phenylthylamine+dopamine+nocepineohcine+enelocphin+vasopcessin(爱=苯基乙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内啡呔)——剩下的,大概就是文化了。
爱情就是这样一场化学反应。当然,并不排除这可能是所有化学反应中最有“文化”的一种。当男女双双都High起来的时候,我们深信自己是在飞行,然而一切从地面起飞的“飞行”无不以降落为终结,落地之后,我们难免会发现所谓的“飞行”其实完全符合《反斗奇兵》里胡迪探长对巴斯光年(后者当时对自己是太空人而非太空人玩具深信不疑)在室内表演的“飞行”所下之断语:Falling With Style——“有风格地坠落”,或日:“摔得挺漂亮”,“摔得有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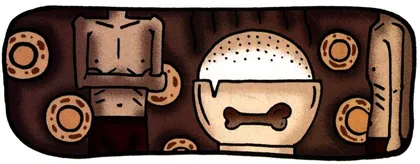
这一种摔法,是因无知而导致的自讨没趣。食色性也,在饮食一事上,我们似乎正因为“有知”以及越来越有知而越“飞”越有趣,越吃越有文化。现而今,凡称饮食,必定后缀“文化”二字,犹如杀人者接下来必定放火。中国饮食自不待言,此外,目前被公认为全世界最有文化的吃喝,无疑是日本料理。一团寿司,几片生鱼,若一时不能从中悟出一派禅机,至少也非得吮出几滴心灵鸡汤不可。吃喝的时候能这样想固然很好,至少结账的时候会觉得性价比极为合理,午夜梦回,回味起来尤能在心中狂呼超值,不过,偏偏有些日本人却并不这么看,他们说日本人是在亚洲粒食民族中惟一以寿司和饭团这两种形式吃米的,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形式,无非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一口饭能以团状完整地送入口中,保证每一粒米都不会被浪费。之所以悭吝至此,无非是“国土局促,资源短缺”这一类老生常谈。鱼生也是这样,海洋比陆地辽阔之外,与煎鱼、蒸鱼相比,谁不知道Sashimi的干活实在是最省油最省燃料的一种吃法呢?
粤菜鼎盛的时代,全国人民不仅都学会了“生猛”这个词,“生猛”后来还由口上脑,变成了广东人的所谓“文化性格”。所有这一切,说穿了其实都跟气候和保鲜技术有关。广州气候之湿之热,举国无双,而且有更湿更热的趋势。如此恶劣环境之下,吃东西若不一味求鲜活,就只能集体去做腐食动物了。至于粤菜在烹饪上的一系列独特的基本技法和理论、例如追爽滑、脆嫩,原汁原味,喜清蒸,爱生食,好打边炉,崇尚现宰现烹,等等,皆因对原材料在“鲜活”二字上迫不得已的刻意追求而生。就保鲜技术而言,过去不仅广州人没有电冰箱,全国人民都没有电冰箱。惟独广州人民拥有一样全国人民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几乎终年湿热的气候,人不能跟天作对,故于保鲜一事之上,广州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精力,最起码,广州人不能像北京人那样在冬季把大量的白菜储存在家里,好整以暇地慢慢“叹”,广州人命里就没那个福分。当北方人在饭桌上热情地高呼“趁热趁热”,厨房里的广州人,心里多半都在哀求似的默念着“趁生趁猛”。
广州人既不是烹饪上的天才,当然也没有存着什么“残暴”的初衷。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虽然广州人民后来和全国人民一样都有了电冰箱,但是饮食习惯却已根深蒂固,基因化了,改也难。说得严重一点,也算是一种“被迫害后遗症”。我最烦听到有人用“生猛”来形容广东人的性格,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直头就是扯淡。反过来说,如果广州人民在南粤王时代就家家户户都拥有了电冰箱,而且冰箱里的鱼也是像广告里神经质地跳将起来的那种,也许今天的粤语词汇里就不会有什么“生猛”之类的阿物儿了。
所谓“饮食文化”,美轮美奂,煞有介事,根子上无非是因为贫穷,因为短缺,因为窘迫,都是苦出身,都不容易——大抵发奋之所为也。若一口咬定非有“饮食文化”这回事的话,也应该是一种“节约文化”。过分的文化自欺使饮食成为皇帝的新装,因为我们已经证实。所谓爱情正是“穿着”那套新装的皇帝。一部烹饪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口腔的“被迫害史”以及“反迫害史”。
正在变得比粤菜更有文化的川菜,讲的无非也是同一个故事。我的意思是说,把菜烧得如此之辣,初衷其实也只有一个:多下几碗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愧是真的猛士,与此同时,丫当时无疑也真的很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