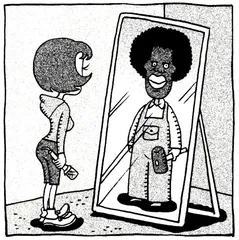生活圆桌(31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困困 江川澜 钟和晏 飞天猪)
三万英尺的盛宴
困困 图 谢峰
应该是1988年,我第一次吃到了航空食品。是长辈乘坐神秘的飞机带回来的,盛在狭长礼盒里,零零碎碎的,每样儿一小撮。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年份,是因为我把它带到学校时,正赶上一年级升二年级的体育考试。我在500米开始之前,溜回教室,欣喜发现果然一个人也没有!我朝自己的课桌扑过去,想到那盒美味就藏在桌洞深处,嘴里的口水都禁不住一荡。我抓了个什么含进嘴里,具体种类想不起来了,但肯定是奶糖或者巧克力之类的,因为那种香味真是生津润咽连绵不绝。
等我有资格坐上飞机,航空食品早没了装进礼盒的待遇。一般短途飞行,只有一次只装半杯的饮料与花生米供应。但也有印象深刻的,比如我熟悉的山东航空,由于该省盛产花生,所以每颗都饱满滚圆油分充足;而且沾满了大粒海盐,绝对富含碘质,不麻烦空姐送三次橙汁不足以熄灭嗓子眼的熊熊干火。再长的旅途会给顿饭吃:海南航空的水果种类丰富,虽然总像刚从罐头里捞出来的,但隐约可以分辨出那是其他航班上少见的芒果或者火龙果;四川航空的空姐与饭菜质量比其他的都高出许多,其中原因在于她们吹弹欲破的皮肤与手上递过来的一袋辣椒酱。
直到乘坐过国际航班,我才明白,这三万英尺处的盛宴是各国饮食文化的集粹。我吃过英国航空提供的国粹美食Fish & Chips,油炸鱼和薯条。不管口味如何,一定早早浇上酷似呕吐物的青豆酱,有时鱼的脸还冲着你,我善意地认为这不是为了让人噩梦丛生,而是帮助你辨别这真的是鱼而不是别的肉类;意大利航空也不会只端上好吃简便的比萨,与之搭配的,是分装在小碗里的前菜——阿尔卑斯山区的腌生肉(不明物种);甜点——仿佛糖不要钱的小甜饼。如果你胆敢要杯橙汁,那都是对该国饮食文化的藐视,因为搭配喝下的必须是凉到脚趾头的雪山泉水和只会让人头疼欲裂的餐后消化酒。我很庆幸没有乘坐过瑞士航空的班机,保不齐他们会提供该国最著名的Cheese火锅。冒着泡的Cheese散发臭豆腐的味道,涮锅的材料,想象中的蘑菇、牛肉一概没有,因为他们为了保证正宗与传统,一定只提供干面包。
所以在半月未尝中餐的情况下,回国班机选择中国航空是极明智的。将迎合国际友人的黄油、圆面包扒拉到一边,在餐巾纸小袋里翻找一下,一包可爱的榨菜探出头来。虽然上面没有标明产地,但撕开闻闻那味道,这才是真正的Made in China。连汤一起倒进嘴里,咸鲜美味嘎嘣生脆,任何其他食物跟它比起来,都是摆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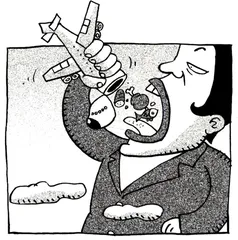
生命之书
江川澜
写作者,应该有意避开某些主题,比如残酷、暴力、激越之类,像戴厚英,写了《脑裂》这样的书,结果自己惨死于歹徒手中;比如唐敏,写了《女孩子的花》,说自己梦中的女孩永远不会来了,也不幸成了谶语。带着这样的想法开电脑,一下就看到张纯如自杀的消息。
第一次看到张纯如的书,是在仙台的丸善书店。英文版,她的英文名字Iris Chang.美丽的名字,彩虹或者鸢尾花。看了她的介绍,写作此书时29岁。心里还在赞叹,如此年轻就选择了这么沉重的话题。没有良知、责任,过人的勇气和才能,是无法胜任的。她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译本,但就是没有被翻译成日文。日本的右翼分子阻止了日文译本的出版。还记得当时的报纸上有一张她的照片,她在日本演讲,长发有点凌乱,台下有日本人试图冲过去阻止她的样子,她那年30岁左右吧,这种混乱的场面让她有种惊惶与愤怒的美丽。一个女人就是如此孤独地抵挡历史和现实的谎言。
南京大屠杀,有良知的日本人还是愿意直面的。我看过日本名记者本多胜一的同名书。张纯如的书摆在那里,尽管是英文版,我留心了一下,也有不少人在翻阅。
后来看到她的另一篇文章,谈到她在写《南京大屠杀》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搜寻到了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她当时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并力所能及地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女性的生命。但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却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了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我相信,张纯如也跟她非常尊崇的这位女性一样,牺牲于这场战争。她为这位战争中寂寂无名的英雄呼喊:“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共有的遗产?在历史中如果谁能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此人一定就是魏特琳。”
我注意到张纯如的一个生活细节:2002年8月,她的儿子降生。
站着、躺着还是趴着
钟和晏
纳博科夫说他是在书房里一个可爱的旧式讲台上开始一天的工作的。稍后,当他感到地球引力在拽他的腿时,便坐到写字台前一张舒适的圈椅上。最后,当引力开始爬上他的脊背时,他就躺到小书房一角的长沙发上去。有时候,三种不同的身体形态还决定了写作形态的不同——躺着写散文,站着写诗,坐着写学术文章。
我前一阵做过一个关于新办公形态的选题,看到一位名叫尼尔斯·迪夫伦特的欧洲设计师说:“我理想中完美的办公室是没有椅子的,在那里你可以做两件事情——站着或躺下,这是人体最舒服和自然的姿势。”
虽然汤姆·彼得斯在去年出版的《重新想象》中还宣称“几乎99%的工作空间都是非人性化的”,看来纳博科夫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到达了“完美办公室”的理想国。不过这个自称他收集蝴蝶花费的时间比写作还多的骄傲老头毕竟是“SOHO”一族,更准确地说是“HO”族,自然可以为所欲为。还有一幅办公室乌托邦的美妙图景是由维珍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提供的,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曾被英国媒体评选为“英国最聪明的人”是从他买下的加勒比海内克尔岛的一张吊床上开始一天的工作的。
后来,我在斯堪的纳维亚的Cell网络公司的办公室照片上又一次看到了那种诱人的吊床,这家公司将哥本哈根一个建于1921年的水上飞机棚场改造成他们的丹麦总部。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棚场最初可是用来停放水上侦察机的,如今里面被设计了许多高塔层办公室,还有一些吊床悬挂于钢铁立柱之间,让那些网页设计师晃晃悠悠地躺在上面构思创意。
.com时代开启了许多新事物,连办公室的形态也前所未有地花哨起来,比如“移动办公室”、“虚拟办公室”、“旅馆化办公室”以及“临时办公室”等等。纽约TBWA Chiat/Day广告公司现在已经退休的老板Jay Chiat最早在1993年提出“虚拟办公室”的主张,宣布要把他的员工们从那种讨厌的、千篇一律的隔间中解放出来,只要带上移动电话和PowerBook,他们就可以躺到海滩上去工作。在办公室里,Chiat取消了所有的隔间和私人办公室,用沙发躺椅、小桌板和几间会议室来代替。但结果是,TBWA的员工们个个都变得怒气冲冲,因为办公室里“他妈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就那个欧洲设计师所说“站着或躺下”的完美办公室概念,我在采访中间起潘石屹,他回答说:“瞎掰的。我还看到过有个医生说其实人最完美的姿势是趴着,跟狗一样跟猪一样趴着。他说人类容易得心脏病胃下垂什么的就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不完美,如果天天像狗一样趴着就不会得。你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公司的人都趴着上班呢?”
大概因为自己的有力反驳,潘石屹显出一副很得意的模样。
厄本,二本跟三本
飞天猪 图 谢峰
有次在出租车上,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百姓Taxi》杂志翻翻,结果看见一冰清玉洁,好像刚从高露洁牙膏广告里跑出来的姐姐在纸面上摆出个邻家MM的POSE——虽说有点造作。往下一看娱记的拍马文字,得知这可是号称一代“厄本小天后”的×××。“厄本”是什么的干活?这个问题在脑子里Google了半天,直到下车结账的时候也没搞明白,让人很郁闷。直到有一天,一个在某全球知名唱片公司做企宣的大哥充满同情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就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流行于美国东海岸黑人兄弟中间的“城市”音乐Urban,我才有点明白的意思。因为在我脑子里,与“厄本”发音相同的名词,只有“日本”,而且这还是湖南口音造就的结果。一位革命老人曾充满深情地回忆另一位地位更高的元勋在井冈山上谈国内外革命形势,频频听到“er本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结果好几年后才见识了这群罗圈腿,扛着膏药旗,嘴里老是“八个鸭鲁”的对手,我想象他当时的恍然大悟劲一定跟我差不多;再往下读,令鲁迅先生惊叹的中国式想象和幽默感就涌上来了,有些老乡说鬼子不能叫“er 本”,因为国民政府的长官常常咬文嚼字地把他们叫“义(一)本”,论资排辈,够得上“二本”的只能是《小兵张嘎》里点头哈腰的汉奸胖翻译;然后以此类推,《烈火金刚》里立场游移不定,号称“浑身36个关节72根转轴”,曾经替伪军当过差的谢老转只能算“三本”。那位企宣大哥看我掰着手指头在那里神游天外,就拿出孔乙己的认真劲头对我说“你可知道,这厄本音乐的形成过程吗?”,然后就对我一顿胡侃,大体意思就是当年黑人群众在底特律的没人性流水生产线上如何苦闷,然后就在现场扯开嗓子喊,然后再有一批社会游离分子在穷街陋巷里把这些劳动号子记录一下,加上个把配器什么的去唬唬唱片公司,对资本主义来个反剥削,然后再像铁叫子乐和那样来个“愿早日受招安,心方足”。今天的厄本好像已经成为了富人牙缝里的肉屑,除了展示一下生活的糜烂,其意义也寥寥,并且巴不得跟自己的穷苦出身划清界限。美国厄本音乐大拿usher在他的新专集《Confession》在上市前,为了怕吓跑精神脆弱的白人观众,还特地巴巴地把歌曲中那些触犯“男女大防”的歌词都删改了一翻,基本上达到了洁本金瓶梅的水平。在那个一脸幸福,丝毫不沾烟火气的杂志姐姐身上能有多少“厄本精神”?按照老乡们论资排辈的逻辑,她唱出来的东西能算“几本”?我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