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1998年11月16日,不当老师很久了的刘心武老师在今已不出报纸很久了的《生活时报》发表题为《如今时兴叫老师》的文章,言国人间以“老师”相称已成时尚:“到商厦买东西,售货小姐迎上来,蔼然可亲地问我:‘这位老师,您需要点什么?’不称我同志不称我师傅也不称呼我先生老板,可见如今时兴叫老师啊!……不知道过些时候,会再兴出些什么称谓来?”
在招呼人一事上,服务行业通常是最会赶时髦的,香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现在都把“自由行”们热情地直呼为“大哥大姐”,业务更熟练的售货员,在“大哥”之后尤能追问一声“您是打哪疙瘩来的?”就刘心武老师的个案来看,售货员之所以“不称同志不称师傅也不称呼先生老板”,虽然有可能只因刘老师看上去真的就像个老师,然而7年过去了,“老师”之外好像也没再兴出些什么别的称谓来。非但如此,“好称人为师”的风气反而愈演愈烈,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毫不夸张地说,现如今竟已达到“三人行,必有我学生”的地步,若把网上的书面称呼也算上,毫不吹牛地说,我沈老师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
刘心武老师还说:“我们每一个体生命,在人际网络中,实际都以他人的称谓构成我们的荣辱兴衰,我们的尊严价值,即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的部分体现在我们是否获得了一个‘美称’”。就本人这一个体生命来说,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从被称“老师”这件事情中“全部”或“相当部分”获得过如此之好的自我感觉。既不传道,又不解惑,我没干过一天老师,又因为第一次被我叫“老师”的那些人对我都怀有程度不同的仇视,故我从未循例地有过长大以后当一名人民教师的理想,更不喜欢别人循例称我为老师。然而,若是正色以拒之,纠错能力是得到了发挥,却似有嫌人民教师这一光荣称号不够光荣之或者真把自个儿当回事之嫌,所以,只好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笑纳之,“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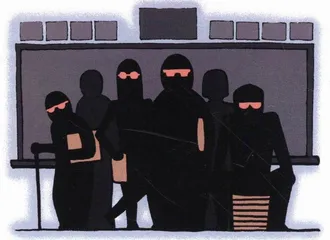
其实,厚着脸皮想想,既然现而今那些有几次没留神把人只宰了个半死的买卖人就都能大言不惭地以“儒商”自称或互称,我就大大方方地认了这个“老师”,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真有什么不妥的话,无非就是觉得该称呼应用某种特定关系的人之间、如冯小刚在家里也称他的爱人徐帆为“徐老师”时(见《我把青春献给你》),那种感觉确实不伦。直到有一天,夜总会新来的小姐也跟着在场的朋友以一种显然不很正派的腔调叫我“沈老师”的时候,不管她是不是穿了一身校服的张柏芝,我还是猛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查“老师”一词,实与科举制度有关,此乃明、清两代生员、举子对主试之座主或学官的称谓。尽管贾宝玉在梦中也称癞头和尚做“老师”,不过当时的“老师”主要还是《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里俯拾皆是的那种:“送钦差一笔钱,拜钦差为老师,钦差亦就奏派他一个挂名的差使”(《官场现形记》)。再往上,还有一种不用给他送钱他也不会派给你一个挂名差使的“老师”,耐是宋元时期专门对“小学”教师的称谓。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伯安入不敷出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至于真正够老的“老”师,则要上溯到先秦,“齐襄王时,而荀卿为最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专指“年辈最高尊”的学者。
早在70年代中后期,我就得知学校之外犹有一种并非以教师为职业的“老师”并且得以以非真实学生的身份称之,接触之。这圈子当时只限文艺界,包括演戏(比主叫方红)、写字(比主叫方多)以及做官(比主叫方猛)的等等。圈子之外,直到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之前,一直以“师傅”为尊称,上海民众甚至还有称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军师傅”的,而一切“师傅”中之级别或年事较高者,通常又被称为“老师傅”。所以我也怀疑,“老师”可能是“老师傅”一词在发言上的末位淘汰式省略。《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这样一忽儿被叫“老师父”,一忽儿又被同一个人叫做“老师”的。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至于我们的青年他们所说的“老师”,以上各种含意估计各有一点。不过就我个人混进人民教师队伍的情况来说,相信是因为一来上了点年纪,二来所上到的这把年纪又达不到享受“沈老”、“沈公”这类敬称待遇的级别,加上我又无业,故“老师”之称在忠于原著的同时,还顺便替我找了个正当的职业。老而不“师”是为贼,既防止了我的为老不尊,也算是老有所养。
总之,无端被称“老师”,肯定有问题,无端称人为“老师”者,问题可能更大。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沈老师日:“人之患,在好称人为师。”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这话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