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富人感到不安?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富裕阶层的呈现,让豪华车纷纷登陆中国市场
万元户到千万富翁,20年财富路径
“万元户”和“千万富翁”是否代表了中国两个历史阶段富人崛起的符号?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孙立平说,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是市场在改革初期所展示出的“平等化效应”,他说,改革初期开始逐步发育起来的“自由市场”给当时的弱势者带来了机会,早期进城的农民和城市中的无固定职业者、收入不稳定者通过参与市场经营获得收益,成为第一批“富人”,“于是就有了80年代前中期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但这个逻辑的生命力是极为短暂,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个趋势就开始逆转。用社会学方法观察转型期问题是孙立平很长时间的研究方向,他发现,无论是马克思或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还是新制度主义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特色的财富路径,“我们发现,市场和再分配在同一方向加速了财富分化的进程”。孙立平说,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拉大,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开始造就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但企事业单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再分配中的权力因素通过“官倒”和初步的瓜分国有资产开始造就一个初步暴富的群体,但再分配中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因素确保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底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经济学家邱晓华指出,80年代中后期,中国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使“特殊群体”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而下一轮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中,由于同样存在非市场化的资源调整,仅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就高达5000亿元。
“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90年代中期前后。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始积累中形成的私人资本,直接带来的是劳资关系以及劳资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第二,权力再次介入原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9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在上万亿元。超过70%的公有住房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出售给原有住户,而这些住房是劳动报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按照职级的高低在进行分配。一些掌握批地的官员在住宅私有化过程中获利最丰。第三,缺乏规范的股市则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
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屈宏斌分析,收入不均问题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力进一步加深。“政府开始意识到税收问题,个税的流失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说,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的比重2002年仅为6%,远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超过30%的水平,“灰色收入、不在岗职工的工资和稚嫩的税收信息系统都阻碍了税款的征收”。
孙立平认为,以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为基础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富人阶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阶层与国家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双重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这个富人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权钱交换的产物,是与国有资产的流失共生的,他们直接以对国家的利益的侵害和分割作为利益扩张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诞生就带着敌意”。
富人的不安,穷人的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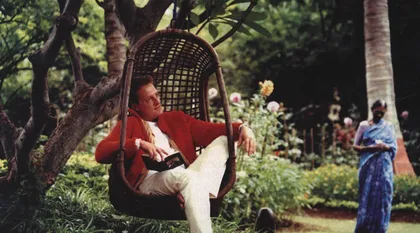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连续两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富翁们也均能在投资上获利

中国客户从德国最大游艇生产商Sunseekev购买的两艘游艇抵达上海
仰融是因产权问题而有争议的富人之一。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发生冲突时,因预感华晨集团的主要经济支柱金杯汽车的控制权迟早会落到地方政府手中,从而将华晨系资金抽调到杭州湾。除准备投资修建杭州湾跨海大桥外,还在宁波与英国陆虎汽车公司进行轿车合作项目。仰融事件提醒我们,对于富人的产生,不应该忽略的还有产权,这是富人形成的供给基础。
在体制缝隙中成长的一部分中国富人,因为财富原始积累的“黑色”或者“灰色”背景,也因为对国有与私人资本双重掠夺后构成的贫富差距急剧恶化氛围,对社会现状的发展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安。李强说:“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积累的资本才开始‘外移’,往外移向所谓‘避风港’国家”。而这种外移不仅严重影响到民间资本在国内的积累与发展,也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调控——富人所聚敛的财富本来应该通过税收或者其他调控手段构成社会结构调整的二次分配,用以补偿在富人聚敛财富时对穷人掠夺所构成的结构失衡。结果这资本外移出去,因为缺席影响了国家税收增长和相应的经济调控,贫富差距比由此不但得不到控制而且日益加大。而贫富差距比本来是市场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极关键的因素,这种资本的大量外移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又加重了富人对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感。”
高级经济师陈明星对目前我国民间资产粗略地进行了框算:1.目前城乡居民储蓄为10万亿元;2.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本为3万亿元;3.假设股市一半的流通市值和保证金为私人所有,为1万亿元;4.资本外逃的最流行估计为3000亿美元,即2.5万亿元;5.城市人口为3亿、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平均城市房价每平方米2500元,那么房产总价值11.3万亿元等。以此加总求和,目前我国民间资产的总量约为28万亿元左右。比较不久前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11万亿元的总值(8万亿元的经营性资产),目前民间资产已经占有了更大的比例或规模。而一项统计表明,这些民间资本中,每年约有2000亿元流到国外,目前已有3万亿资本流失。“如此庞大的资本没有安定感,是可怕的”。
这是中国富人对财产安全出现信心危机的一个征兆。尽管政府一直在考虑整体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再周密的宏观调控都往往赶不上其发展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何帆就此发表评论说,国内一部分富人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复杂背景和对宏观调控所造成的经济前景、经济体制、个人财产保护等诸多方面的信心不足才导致了一系列资本外逃的行为。这种资本外流也影响了一部分靠自己透明地积累起财富的居民与企业家。就外部力量而言,国外的拉力和国内的推力推动了资本外逃。国外的拉力主要是指利差等因素,国内的推力主要是指通货膨胀、税收差别待遇、“尤其是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
李强认为,—个社会在高速发展中来不及建立市场竞争中的公平机制和随之带来的财富良性的二次分配机制,也就难以有稳定而独立的个人产权制度社会,各个阶层的财产权都无法得到确实的保障,政治权力必然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如此才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权贵化色彩,加剧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感。而孙立平说,比较而言,富人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获得保护的能力要强,弱势群体缺少这种能力。“就是说,在缺乏制度性的权利均衡的情况下,事实上的不均衡就会膨胀。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左右摇摆、模糊不清的政策。”由于基础工作没有完成,加大的征税力度,强化了富人的不安全感,不够严谨的舆论和执行部门又把税收反过来变成穷人宣泄社会心理和情绪的工具。“结果会和政策部门的期望相反,缺乏制度化的保护,在弹性政策的影响下,弱势群体的状况不断恶化,这又得不断地‘杀富安贫’,给穷人出出气,导致富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富人没有安全感和穷人状况的恶化同时存在”。
孙立平认为,只有有了平衡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用不着“杀富济贫”、“杀富安贫”,富人的权利也名正言顺地给予保护,在这两个保护的基础上,形成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利益能够均衡是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这种博弈,没有对这种博弈的制度化保障,利益均衡和各个阶层的安全感是不可能出现的”。
尽管政府一直在考虑整体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再周密的宏观调控都往往赶不上其发展速度
富人救赎的N种可能
郎咸平是最早提议制度化处理富人原罪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对于早期富人在财富来源和权利分配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应该给予他们赎罪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多种可行性方案”,用“钱”赎罪的方法之一是郎设计的BOT方案。他举例说,假设一名企业家向国家拿了100元股本金投资,再透过银行借贷900元而将企业做大。五年以后企业的资产变成了1万元,而每一年的现金流是1000元。更为复杂的是五年以后又有一名股东投入了100元,而又向银行借贷了900元继续将企业做达到2万元,而每一年的现金流是2000元。他建议学习美国证监会的“轻罪和解,重罪司法”决策方式。如果900元银行资金是靠提供假资料和行贿得来,那么就可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依法处理。但是第一个100元和两次银行借贷各900元事属于不清楚的灰色地带,那么应引进遗产税制度进行和解。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根本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因此和解的真谛就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能力和维护国家的利益,最好的做法就是实施遗产税制度。
“具体做法如下,前述案例2万元资产里面,有1万元是非常清楚地属于新股东,因此这部分股东利益应该确保。我们将另外整笔1万元资产当成原罪资产。这笔钱如果辽宁省立刻收回,又形成了‘类国有企业资产’,这对于公众利益是有损的。但为了有效发挥民营企业家的创造能力并确保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先行肯定他利用国家财产所创建出企业王国的贡献——Build。这笔资产仍然交由他经营——Operate。等他过世后,国家可以利用累进遗产税的方式收回产权不清的部分资产——Transfer。但是累进遗产税的最高税率绝对不能超过60%,以维持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减低企业家在逝世前透过贱卖贵买资产方式转移资金的诱因。另外,累进遗产税的配套措施还包括下列数项条款。”他认为,第一、新股东的利益要确保完全和原罪无关,政府任何制裁行动若伤及新股东利益,则新股东可通过司法系统申诉。第二、通过遗产税清洗后的资产可将原罪完全注销,成为法律保障的清洁资金。第三、为防止资金转移逃避遗产税,在缴交遗产税以前的任何资金移转、买卖资产等均需申报。
上一个千年的50个富人
在上个千年结束时,《华尔街日报》评选出在这1000年中最富有的50个人,他们覆盖的范围从成吉思汗到比尔·盖茨。其中中国人有6名,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出生于1671年的约翰·劳与1732年的理查德·阿克莱特在这份名单上占据着分水岭的位置。前者是金融投机的创造者,而后者则是工业革命的奠基人之一。
在他们之前,巨额财富的积累只能通过战争、掠夺,权力与暴力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世界最富裕的人是成吉思汗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出生于1162年的成吉思汗,他当时的统治涵盖现在的中国、俄国、韩国、中南半岛、伊朗和伊拉克等地。如以土地来衡量财富,成吉思汗所拥有的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无疑使他成为历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至少在中国的财富史上,权力一直是最重要等价物:明朝宦官刘瑾被正法之后,据称所积敛的金银财物甚至超过明朝末期国库中的官方银两。清乾隆时期,和珅倚仗皇帝宠幸和主管海关税务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怂恿皇帝兴兵征讨,而从中扣取军饷,在乾隆去世后立即被捕,所有财产充公。出生于1769年的广东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
但工业革命和技术主义改变了财富积累模式,约翰·劳和理查德·阿克莱特俩人创造了新的模式:尽管你最初一无所有,却可能通过自己的智力,或是对新技术的运用来获得像王公贵族一样的金钱,它们多少意味着金融力量与技术力量的崛起。工业革命打破了静态的社会形态,财富增长第一次可以成为持续进行、也拥有预期性的行为。它还打破了权力均衡,财富取代宗教成为一支重要的调控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政治力量,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争相取悦当时最大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为他们的战争提供借债。上榜的惟一女性、生于1835年的投资人海蒂盖·葛琳,她在从事船运的父亲去世之后,继承了1000万美元遗产,美国内战之后,她大量购入政府公债,并以“低进高出”的基本手法在股市操作,但为人极其吝啬,有“华尔街女巫”的绰号,当她于1916年去世时,遗留的财产有大约1亿美元(相当于当今15亿美元)。
民国初期的金融家和高级官员宋子文,则是这个时期中国富人的代表,据称是40年代世上最富有的人。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跨入金融界,在中国成立了中央银行,他并因从事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等蓝筹股投资而获利,在1943年时,他的资产估计为7000万美元,现在约值6.6亿美元。但宋的背景仍然被强调:他是权势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