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打造“政治偶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于萍)

“流行偶像”的成功推出让独立电视台萌生了“投我一票”节目的灵感
7月,英国人罗宾收到了独立电视台(ITV)“投我一票”(Vote for me)节目组发来的申请表格。“你必须不是任何在英国和北爱尔兰选举委员会登记过的政党的成员,也就是说,你必须是无党派人士。”申请表格在前言用大字提醒说。罗宾一边将信将疑地将这事儿发到网上征求大伙的意见,一边紧张地备选:他必须写出500字的竞选演讲,200字的参选动机,200字的当选后计划。
罗宾参加的正是英国独立电视台新推出的名为“投我一票”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这个节目于2004年4月15日公布计划,4月中旬接受报名。只要是无党派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节目将聘请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政治事务专家作为裁判,通过审查书面材料,选出十名候选人;之后通过观众多轮投票的方式选出一名最适合当议员的“政治偶像”,这名偶像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英国2005年的大选。按照独立电视台的计划,“投我一票”节目将于今年年底制作完成,明年年初播出,并在首相布莱尔宣布大选日期之前停播,以免违反“任何候选人都不能在竞选期间做多于对手的电视宣传”的规定。
“投我一票”是独立电视台另一个名牌真人秀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的翻版。“流行偶像”于2001年秋天出现在独立电视台的屏幕上,吸引了大批梦想成为歌星的普通人报名参加,选拔的过程涉及竞争者的表演、裁判的评头品足和观众的一轮又一轮投票,最终选出一名“流行偶像”。“流行偶像”之所以被归类为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电视歌手大奖赛”,原因就在于它的业余与真实。节目一推出就引起轰动,报名人数曾达到一万,并已选出两届“流行偶像”。通过“流行偶像”成为明星的,除了最终获胜者,还有喜欢说刻薄话的裁判。乐评人西蒙·考埃尔就以评论尖刻著称,两届的“流行偶像”裁判,将他推上英国电视娱乐业首富的宝座,并在著名的伦敦蜡像馆争得一席之地。
“流行偶像”人造歌星的做法,以及裁判用语言对参选者的虐待甚至引起英国议会的关注。2003年11月,下议院10名议员联合签署一份动议,谴责节目裁判对年轻表演者外貌所作的无情评论。他们认为那些音乐专家的评论,是向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发出的错误信息,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流行偶像”节目制作人克莱尔·霍顿对此的反应却是:“这个节目竟然在议会受到讨论,太重要了,我感到荣幸。”实际上,克莱尔一点儿都不用在乎议会的议论。“流行偶像”为独立电视台吸引了一千多万名观众;2003年决赛甚至在平安夜晚间播出;该节目模式也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卖到二十多个国家。“流行偶像”已经让独立电视台的收视率与英镑滚滚而来,议会风波不过是一次免费宣传罢了。根据独立电视台的统计,2002年“流行偶像”节目的决赛中,共有约870万人参加投票,人数超过了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英国参选人数。大概就是这种比较让独立电视台萌生了推出“投我一票”节目的灵感。
可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人们对议会选举没什么兴趣,并不代表“投我一票”一定会吸引大批观众。而对政治的不敬,也使该节目遭到政界的批评。推出节目的计划刚出台,英国宪政事务部官员就讨论了节目的合法性,结论虽然是肯定的,但英国选举委员会对独立电视台发出警告:切勿利用节目对届时当选的“政治偶像”进行对其他候选人不公平的宣传。
独立电视台选在4月15日公布节目计划,也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4月16日,英国《卫报》提出质疑:“这该不是个愚人节玩笑吧?”实际上,独立电视台在4月中旬公布了报名电话和邮箱地址后,再没了动静。其后,传闻将要在节目中担任裁判的玛莎·莱恩·福克斯(Martha Lane Fox)又被传闻为并没有担任裁判的意愿。此人头衔是:200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青年财富排行榜最富有的女性、Lastminuet.com网站创始人。“投我一票”由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最近独立电视台澄清,该节目并非玩笑,但对裁判的传闻,他们“拒绝否认玛莎将担任裁判的传言”。独立电视台外交辞令式的解释与对节目的低调,完全不同于“流行偶像”时期的强劲风头。这似乎暗示着,独立电视台这次的真人秀节目,因为敏感的选题正经历着是否继续下去的尴尬。参选者罗宾显然已经被挑选为最后的十名候选人之一,但他依旧像大多数人那样将信将疑:“投我一票”真人秀到底还秀不秀了?
真人秀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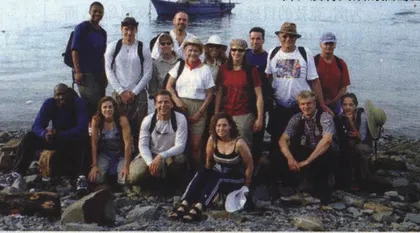
在《生存者》节目里,参赛者被送到一个相当偏僻、没有人烟的孤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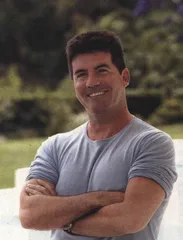
两届“流行偶像”裁判,将西蒙·考埃尔推上英国电视娱乐业首富的宝座
里查德是真人秀节目《生存者》(Survivor)的最终获胜者,他在拿到100万美元奖金的大结局时刻,潇洒地说:“这只是个游戏。”这个节目将16个普通美国人放到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上,远离世俗生活与惯常社会关系,随身只有极少量生活必需品。他们不仅要应对自然挑战,还要采用“除暴力以外的任何方式”来党同伐异。从某一天开始,每天采用集体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来淘汰一个人,最终存留者将得到100万美元的奖金。《生存者》中有众多的象征细节、仪式场面,也不缺少戏剧性、扮演行为,加上虚拟场景的设定和自成体系的规则,整个过程看起来的确像个游戏。但《生存者》的第一集就达到全美收视率第一,有5800万美国人观看此节目。制作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拿到了广告收入单集3600万美元的天价,而这只是收入的25%,另外75%来自贩卖节目模式的知识产权。这种结果,显然让《生存者》不再是只是个游戏:制作者赚了大钱;普通人成为“腕儿”;观众也对节目津津乐道,他们感叹:“那个卑鄙的人胜利了!”
没错,《生存者》对人性丑恶的展露,让获胜者里查德收获金钱的同时名誉扫地。而暴露人性阴暗与贪婪,也成为真人秀电视节目最广为争议的因素。同样遭受争议的还有打出“贪婪是成功要决”口号的美国真人秀节目《学徒》。此后真人秀电视节目对道德与伦常的颠覆屡见不鲜:《老大哥》对个人隐私的不敬,《诱惑岛》对爱情的嘲弄,《笨蛋乔的世界》对诚实的否定……真人秀俨然成为社会道德捍卫者攻击的焦点。但久经考验的电视节目制作流水线根本不在乎这些,因为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商业逻辑,简直无懈可击。拿《老大哥》为例,它具备了许多吸引眼球的“珍贵”品质:男女私情、性爱、勾心斗角、贪婪……此类种种,不断把收视率推向新高。抛开道德的因素,对电视节目制作者来说,这无疑是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不过最近却出现了一些让制作者不能不在乎的技术问题。拿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投我一票”节目来说,以政治为调侃对象,打选举的擦边球,这条路走得就不怎么顺利。按照传播学的理论,真人秀节目分为两种:竞赛类,比如《生存者》和“投我一票”;游戏类,比如《老大哥》。在这种模式下,可选择的主题随着真人秀节目的增多一个个在减少,当制作商扳着手指头将隐私、爱情、野外生存、探险、商界竞争、明星制造……一一剔掉后,他们暂时想到的政治调侃,但前途不明朗。而主题频道与主题节目的出现,也分流了许多真人秀节目的观众。一个右翼保守党的老头,不会觉得《老大哥》里的男女私情有什么大意思。按照达尔文主义理论,人的低级欲望是生存和性,高级欲望则是创造。真人秀节目依靠制作者的高级欲望宣扬人的低级欲望,再次证明了达尔文的“低级欲望在生命中所涉的面积还要大过高级欲望”。
最近《学徒》的雇主扮演者唐纳·特普朗(Donald Trump)也给真人秀节目出了个新难题。唐纳作为每期《学徒》的固定参与者,他觉得所得片酬已经与自己的大牌身份不成正比,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出每集1800万美元的价钱。真人秀曾被媒体分析专家称为“观众喜爱的便宜的节目”。2000年的《幸存者》也证明了这一点:一集成本不过50万美元,比普通电视剧的制作成本平均低150万美元。不需要支付大牌明星的高额片酬,没有脚本,无须布景……却有高收视,这真是酷死了。不幸的是,真人秀还是走回了电视业挥霍无度的老路。除了要求提高片酬的演员,有经验的制作人,选角协调员,甚至编辑都身价倍增。而在布景设计上,为了挑选更具奇异的拍摄地点、更美轮美奂的背景,制作人和投资人的钱包都筋疲力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低成本的真人秀再也没有了。”虽然目前真人秀仍然比传统节目便宜,但对制作者来说,《幸存者》时期天堂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我们自己的真人秀
2003年,有电视人自信地说:“2004年将是中国真人秀节目的成熟年。”但这一年已经过去大半,从制作者到观众,没人看到这所谓的成熟。野百合的春天迟迟没有来,欧美的正宗真人秀节目却也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尴尬
虽然中国的真人秀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早在2000年广东电视台就推出模仿《幸存者》的《生存大挑战》,之后陆续出现了《勇者总动员》,《走入香格里拉》、《英雄古道》、《非常6+1》和《谁将解说北京奥运》等。这些真人秀大都模仿了欧美真人秀的节目模式,却没学来人家的高收视率。
2003年8月,“中国真人秀论坛”在贵阳举行,众多学者媒体参与讨论,试图找出中国真人秀节目收视率萎靡的原因。他们断然否定照搬欧美节目模式的做法,却给模仿取了个新名——本土化改造。这样看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真人秀节目不行,那是因为没有本土化改造好。而摆在真人秀面前的本土化问题真是形形色色。
按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副院长尹鸿教授的分析,真人秀节目设定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有朴实性,也就是这个目标大家都关心;二是要有刺激性。以《幸存者》为例,竞技的目标并不是最终留在孤岛上,而是得到100万美元。钱谁都关心,100万也够刺激。但这种目标在羞于谈钱的中国人面前遇到困难:在镜头感很强的情况下,中国人不自觉地掩藏起贪婪,宁愿显露善的一面。这就让许多本土真人秀节目设定了其他的竞技目标,比如实现一个愿望;或者提供一次与异性交流的机会。但这种温吞的奖励让真人秀节目最刺激观众胃口的“博彩性”大大降低。
而真人秀节目对故事性的高要求,也对中国这个没有电影经验的民族是个挑战。我们讲起故事来总是差那么点劲,悬念、结构、视点,都差强人意。《幸存者》在一个空间与时间爆发出来的有团体与团体间的冲突,自己和朋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自身与道德感的冲突。但在《走入香格里拉》中,冲突只剩下人与自然。
而在道德感沉重的中国,性、隐私、欲望这些真人秀节目的卖点统统遭遇社会心理的抵抗。如何在收视率与伦理性、娱乐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成为中国真人秀难以回避的疑问。
真人秀论坛对中国真人秀的本土化之路做了种种不乐观的分析,最后却得出“2004年将是中国真人秀节目的成熟之年”的结论。一年已经过去,我们依旧没有看到成熟的本土化真人秀节目,而欧美的真人秀也渐渐显露窘相。老话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中国的真人秀节目要做出上乘的本土化改造,的确不太容易。
资讯
几个真人秀

《学徒》
《学徒》(The Apprentice)
每期从报名者中选出十六个“学徒”,在唐纳·特普朗扮演的雇主带领下,接受纽约职场“幸存”技巧的考验。
规则:由唐纳向他们下达任务,考验他们的智慧、创新能力、业内技巧以及脸皮厚度。任务一般是两个组被派到纽约工商界,在短时间内完成高难度任务。测试涵盖商业运作的诸多层面:销售、行销、促销、慈善捐助、房地产交易、财政、广告策划和设备管理等。每周唐纳都要解雇一名“学徒”,有时候因为没完成任务,有时候就因为惹唐纳不高兴了。
目标:成为最后一名“学徒”,担任唐纳·特普朗旗下商业集团的总裁。

《老大哥》
《老大哥》(Big Brother)
名字出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以英国的《老大哥》为例,6男6女共同在一座豪华大宅子居住85天。宅子里安装有25台摄像机,32个麦克风和40公里长的电缆,一天24小时地记录他们举动。这12个闲人每天白天在客厅闲聊或搞怪,晚上到固定的小黑屋对着“老大哥”说别人的坏话。
规则:每周六这12人投票选出最不受欢迎的两人,再由观众打电话选出最没人缘的那个。中标者出局。
目标:争取成为最后留下的那个,得到7万英镑奖金(同时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诱惑岛》(Temptation Island)
《诱惑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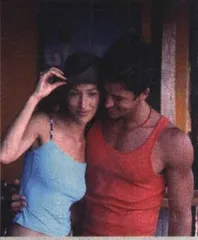
四对志愿者情侣,被放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孤岛。男女各与13名单身异性分别在岛的两端生活两周。
规则:除了集体活动,情侣们不能见面,见面也不能交谈。节目开始,情侣选手有权从他们的13个潜在情敌中选出一人赶出岛去。之后情侣选手分别与单身异性自由约会,频率是每人每天一个异性。一轮后,情侣观看自己爱人的约会录像,选出潜在情敌男女各一名出局。四轮后,每个选手选定1名单身异性,与其进行非常有深度的约会。节目的最后一夜,四对情侣重新会合,决定他们是继续厮守,还是另觅佳偶。
目标:发现“情比金坚”,或者又一次更换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