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孤中求有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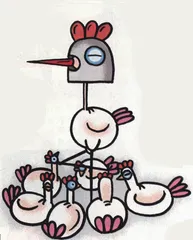
李敖有话说,说着说着,忽一日心血来潮不知怎地就把话说到了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头上。李敖说,蒋介石该骂,中国人不该骂,但是柏杨这个人不敢骂蒋介石,于是就不负责任地把全体中国人给骂了。
被李敖骂过的人也很多,钱穆先生亦不例外。在“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这类“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硬伤让李敖伸足了脚之外,钱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更让李敖起脚猛踢过一番。但是,我相信按照李敖的标准,钱先生尽管亦称不上品学兼优,但肯定是不会犯下柏杨那种罪行的,因为在“该骂蒋介石还是该骂全体中国人”这种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论透彻,学术上几乎无人超得过钱穆,犹如李敖之白话文水准五百年来无人可及。
《晚学盲言》有多处论及“少数与多数”以及“群与孤”的关系。钱穆先生指出,虽则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商业文明滋生了基于“孤”的人生,中国的农耕文化则导致了以“群”为主的生活,然而,“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往者转重群”,故“中国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以鲁宾逊和伯夷为例,采薇首阳与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惟鲁宾逊乃遇不得已……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
“在人群中求有孤”,大概就是“和而不同”。君子精神,圣人之书,向来是“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和而不同”一方面受到“同”的强大牵制,西风东渐,另一方面又受到“孤”之猛烈牵引。钱先生质疑:“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
虽不知其立论根据何在,但是逆向操作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吾侪之新人生,那是将个人的“孤事”或“孤立事件”想方设法或者不假思索地扩大化,推而广之以“求有群”。近来多起“有话说”的事件,莫不如是。挨了个别的骂,原因归结为“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个人在国外遭受个别的不公正待遇,扩展至“民族耻辱”,一场球赛之输赢,提升为国家之胜负,个人名誉受损,则把原本应属于个人的伤心放大成“伤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心”。
“从孤中求有群”之益,并不尽在推诿责任,也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以“法不责众”或“人多势众”来达到个人在道义和技术上的双赢。不过,若言以多胜少乃“孤中求群”之喜剧大结局,其悲剧便也相应地体现为以偏概全,害一船人被一竿子打翻。不管是“民族的惨剧”也好,“民族的闹剧”也罢,“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就有一个人泼了冷水就把他踹下去,难道我们民族就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吗?”这种表达方式,与“不敢骂蒋介石而骂全体中国人”实在是相当靠谱。
马雅可夫斯基总爱把十月革命称为“我的革命”,人或质疑:“你在诗中常常写我、我、我,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吗?”马诗人反唇相讥:“向姑娘表白爱情的时候,你难道会说我们、我们、我们爱你吗?”吾国的“求有群”人士在向姑娘表白爱情时,一定是说“我爱你”的,只是当他们一旦面临“被甩”而进行危机处理时,“我们、我们、我们爱你!”这种话相信也一定会脱口而出。此种有很强选择性的“集体主义”,其实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变态形式,或曰由“无我之境”转入“有我之境”过程中的极度不适应。朱自清先生写道:“(五四时代)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
变态个人主义,其实是既不搞“在人群中求有孤”,也不玩“从孤中求有群”的。试以性活动为例,此私房事,却因家族及国族需要而被传统中国文化视为“有群”之集体活动,故千百年来基本按“群中求独”的方针行事;至于本着“以独求群”精神之西人,又因而具有将此例行私事搞成集体活动的倾向。所以,群P派对不能不流行于全球资本主义商业中心纽约;所以,当地两位美女作家艾玛·泰勒和洛瑞蕾·莎琪就不能不在年中出版了一本《性爱礼仪》,其中有关群P派对的社交礼仪有基本守则四条,第二条为:“如果在派对上你不直接做爱而选择在一旁观看,那么注意不要随便起哄。”
出于个人目的,把属于个人的孤立事件无限放大推给集体,利用集体反集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个人一旦成功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同而不和”之境,不仅自己做成小人,而且还会因“随便起哄”而把集体变成集市,把团队变成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