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0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江川澜 元涛 困困 王淑瑾)
变节者与自由
江川澜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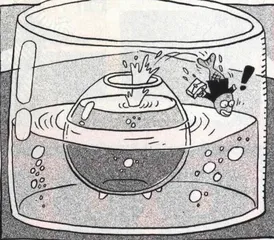
前些天在日本,电视新闻里总有20年前被绑架到朝鲜的曾我瞳一家。7月9日他们一家人终于在雅加达机场见面。妻子上前紧紧拥吻年迈病弱的美国丈夫詹金斯,两个混血女儿在后面饮泣。丈夫拄着拐杖,步履维艰,妻子与他双手紧扣。电视里一遍一遍地重播这个镜头,确实感人至深。妻子先回到日本,经过外交斡旋,一年零九个月之后一家人才团圆。作为美军逃兵的丈夫,要受到美国的引渡,只好先转道雅加达团聚。看报纸报道,日本政府特地包下雅加达一高级酒店的一层,以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之后一家人顺利到达日本,丈夫入院治病。此后每天的新闻就是曾我瞳带领孩子们坐车,购物,准备大学入学,学习日语。两个女儿一直戴着朝鲜国徽的标记。她们的表情和我见到的朝鲜人的表情非常一致。
詹金斯1956年从美军驻韩基地叛逃到朝鲜,当年的他还是个英俊小伙子,多年之后,面容沧桑,还要接受美国的军事审判,为了自己当初的投敌行为。他也深知自己到了日本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表示,临死之前希望家族团聚,支离病体,冒着引渡审判的危险过来了。镜头里的他,永远双眉紧皱,一脸倦容。妻子在镜头面前坦然自若,但全无笑容。
多年的生活磨砺,太多的悲痛吧。我想起更著名的叛逃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连娜。先到印度大使馆,再到罗马,再到美国。惊心动魄的叛逃历程。在美国,经历了与著名的建筑师赖特的女婿、弟子彼得斯的婚姻——这段婚姻确实可以用王尔德的话来做注脚:只有聪明的女人才会犯骇人听闻的错误。耗尽了她的钱财和活力之后,两人以离婚收场。苏联政府剥夺了她的国籍,阻止她和以前的儿子见面和通话,过了十几年才有音信:儿子想到美国来,而她全无能力。斯维特连娜带着最后一次婚姻的小女儿奥尔加到了英国,住在接近贫民窟的地区,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至理名言:没有一个变节者是自由的。
她的回忆录写得很精彩,《遥远的鼓声》。一个至情至性,精通艺术的女人的回忆录。
有人喜欢说,流亡是自己的美学。自愿放逐于异乡的人,或者被迫流亡,或者干脆叛逃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动机呢?多年之后,他们是否心生悔意,怀念故土呢?还是永远保持自己的信仰呢?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这些著名的流亡人士,某种意义的叛逃者,获得了赛义德所说的双重视角的人,内心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还是想起昆德拉讲的笑话:一个捷克人想要移民,到了移民局,别人拿出一个地球仪,他看了一下,问: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女生喝烈酒
元涛
韩剧中,偶尔会有暗恋无果的少女或惊窥老公艳遇的少妇,独个在路边小店据案酗酒,夜色还没来得及黯下去,一瓶白酒转眼间就见了底。
后来知道,她们喝的,是烧酒,韩国特产,虚冒着白酒的名头,入口却像用凉白开冲的糖水一样寡味。好酒的中国留学生几乎个个吃过它的亏,两瓶下肚,不觉兴奋,手就伸向第三瓶了。等到酒劲涌上来,吐都来不及了,这叫后返劲。纵然你筋强骨健,也逃不过明日一整天的难过,头痛,浑身肌无力。若是在中国,酒后出现这类症状,就要担心是喝了假货。相较之下,到底还是中国白酒表里如一,堪称品质一流。
这样淡而无味又上头的烧酒,是否值得拿拇指大小的杯子,两三人守着一瓶对饮?韩国多山,山中多溪,溪边常有闲人小酌。韩国人喝酒讲究,你给我倒,我给你倒,不可自满。礼数繁复,不免喝得提心吊胆,总觉摆谱的讲究强过喝酒的劲头。每次路过这样的酒局,总忍不住想:他们要把一瓶烧酒喝成酒道?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下酒菜。细细的几条鱿鱼丝,小袋的干鱼,若干粒花生,小袋的树椒,或几头糖蒜——不是全部,是其中之一二。
在国内时,有多少酒局要剩半桌子菜?想想真是忍不住心颤。尤其是婚宴,大盘的菜肴层层架构。
请过一位韩国教授吃午饭,预算打的是10万元左右。可是教授却拒绝喝酒,也就无需点菜,每人只叫了一份酱汤配白饭。席间,教授一度将韩国人中午不喝酒的现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说白了就是下午要工作。教授的研究室里等着一群学生娃,会社员工就更怕老板臭骂了。买单时,满心歉意,好像选在中午请客,占了人家不小的便宜。
韩国人中午不喝,憋到晚上一起喝,冲劲更足。黄昏刚至,就可以在路边发现有人扶墙呕吐了。如果不嫌恶心,你可以研究地上那一摊秽物的食品构成,以红色为主,应该是辣椒及其制成品。还遭遇过够段位的酒鬼,吐完,又晃进屋,继续战斗。我理解他。我也是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时还年轻,有斗酒的豪壮心气。酒至大半酣,实在难以下咽时,起身蹩到墙角,自己抠嗓子,吐出去,再喝。与此类似的,是中世纪时,贵族们无所事事,食不厌精,只恨肚子太小,不能一天到晚不停地吃。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呕吐法,用鹅毛撩拨嗓子,吐出去,再吃。为了方便与卫生起见,自己的鹅毛要随身携带,之后就演变成了礼帽上的装饰品。
韩国男人们工作生活压力沉重,晚上放纵喝酒,有光明借口。在家里苦等,就是本分女人的日常功课了。这样说来,韩国烧酒,倒真是适合幽怨的女人,入口入喉容易,等到后劲返上来,头昏脚软挥之不去间,正好可以将伤怀与伤情拖入绵绵无期。
四一度的性事
困困
电影《洛基》(ROCKEY)里,史泰龙的拳击教练拍着他的肩膀说:“姑娘会让你腿软。”雅典奥运会却慷慨地对运动员们说:“来吧,给你们13万个免费避孕套。”
据说这些避孕套由英国某著名安全套制造商捐赠。捐赠仪式上该制造商的一个经理说:“我们不想看到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因不安全性行为而担忧,因此捐出大批产品,希望能令选手们集中精力比赛并取得佳绩。”多么慷慨与善解人意。但捐赠商动人的口吻并不能迷惑头脑清醒的人们,这么搞行吗?
以前就有老顽固对赛前性生活持绝对否定态度。1994年担任德国足球队教练的福格茨曾对他手下的悍将说:“你们都老实点儿,比赛前谁也别胡搞。”而英国的短跑运动员克里斯蒂则很乖地说:“不行的,头一夜玩得太厉害,第二天腿就像灌了铅。”不过科学家们认为他们说得都不对。一个叫施勒弗的生理机能学专家根据科学研究表示:赛前一夜的性事对运动员次日的力量、耐力和其他生理机能没有任何影响。理由是太高的攻击性不利于比赛,而性事可以调剂这种攻击性。更有生猛的,一个叫奥利尚斯基的医生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大声疾呼:“赛前性生活越多,勇夺奖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真让人激动,不过奥医生说,他的倡导只对女性运动员适用,男的还是别想了。
可是一个可怜的男运动员在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得到女人,他该怎么办呢?经验告诉我们,他会DIY的;科学告诉我们,没错儿。《精子战争》里就有这么段话:“正常男性从青春期到30岁前后,每天大约要制造3亿个精子,每星期射精的次数为3~4次。这样,一名不到30岁的男性每星期如能性交3次(或更多次),他就很难会想到自慰。而如果这名男性每星期只有一次性交,他很可能就会每星期自慰两次。”这当然是种概括的说法,但出现在哪个个例身上都不好,如果恰巧他是个自行车运动员,事情就更糟糕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雅典奥运村的医务室已经大门敞开,13万个避孕套楚楚动人地等在那儿。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和职员,据统计有13000多人,这样计算,平均每人可以领到10个。这对为期15天的单身体育派对来说,不算多,不过调节一下体内的攻击性,还是够用了。
精神外科手术
王淑瑾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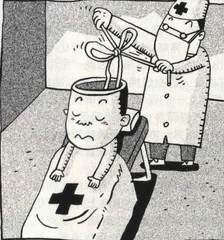
切开人的脑颅以切断毒瘾,这是最近上海医院里的新鲜事。据说,人脑有一种奖赏机制,某些事情能带来愉快,神经系统内就会形成一种反射,这就是所谓的欲望。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就是源于大脑的“病理性奖赏”,而手术就是要在茫茫脑海中人为地破坏这些提供“病理性奖赏”的神经细胞,切断他们输送“病理性快感”的渠道。据说,这种精神外科手术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大有一哄而上的危险趋势。
波德莱尔说过:“人生是一座医院,每一个病人都日思夜想调换床位。这一位宁愿面对火炉受苦,那一位觉得在窗边才能康复。”我的死党魏老师看得更加彻底,每每上街,总是用看神经病的眼光警觉地说:“侬看看侬看看,现在满大街都是神经病,医院里都住不下了,所以都奔到外面来了。”
在华山医院门诊部大堂,看到过一个被父亲追着痛打的男孩子。愤怒的父亲嚷着:“这小孩就是觉得自己浑身都是毛病,几个礼拜已经各个科室都挂号看了病,连妇科也去查过了!”在化验室门口,父亲揪着孩子的脖子:“侬这趟抽血,大便,小便,都再好好查一查!”无论怎样痛骂,男孩子总是不吭声,看腔调是执意认定自己有病在身,只是暂时没有查出来而已。撇开对医院正常秩序的骚扰不说,他真是先知先觉,就像林黛玉生来就要为自己的命运流眼泪一样,男孩子也好像生来就知道:人是有病的!
所以,尽管以上的精神外科手术是否可以被广泛应用,尚在争议之中,但是确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拿着一根直径1.6毫米的射频针插入头部,指指戳戳,调节几个频道,就可以彻底改变各种欲望和爱好,想想就爽!一年忙到头的CEO动个小手术,从此当真说服自己看到钱就吐,一到40岁就和《刺激1995》的主人公一样彻底“越狱”,跑到小岛打渔修船,看什么都是天堂,看到有人互相交送钞票就像看到蠢猪交尾一样狂笑不已。对于被一波波时尚潮流搞得团团转的女人们,最好也动个精神外科手术,从此看到LV新款包包就像看到自家卫生间里的水斗一样,只想非常科学严谨地研究它们的长宽高数字。此外,还可以把消极的人调节得稍微high一点,带着37.1度的体温看世界,热身起来应该会比较快。当然,对于太高调生活的人来说,最好也稍加调节一番,让他们平时只注视最强烈阳光的眼睛也能偶尔注意到阴沟洞里扭来扭去的虫豸世界。
不过,这些问题在我的一个佛教徒朋友看来,纯粹可笑。他对付自己各种虚妄欲望的办法是:打坐。他说,只要每天坚持子夜打坐,欲望就像万花筒里的几个破破的玻璃子,终于会施施然停下它们变幻的步伐,现出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