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栏目的本土生存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探索·发现》栏目推出的《哈尼梯田》

《土星探测》直播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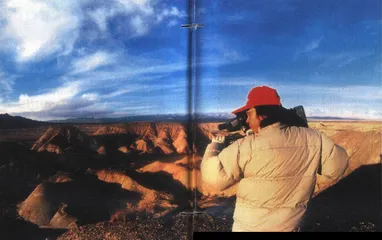
《外星人遗址》
“你们真像中国的Discovery”,这句话已经成为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工作人员相当不爱听的一句话。以至在采访中,栏目组外宣戴晶晶着意提醒:“你们是不是又要把我们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比?”
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人文地理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很容易被大众和发现频道、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联系在一起:和这些知名频道一样,这个栏目总是放一些“神神叨叨”的内容:火星登陆、东方金字塔、三星堆等等;栏目LOGO——长方框里加一把勺子的抽象司南图案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家地理频道的黄色方框。另外,也和这些知名频道一样,这个栏目一出江湖就呈现了迅猛势头:自2001年7月9日播出后迅速成为目前央视10套最受观众喜爱的栏目之一,并相继被西部频道、国际频道引入。三年来,栏目的观众流失率为零。
栏目主编盛振华在面对是否曾借鉴“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的问题时有些矛盾,他承认在节目创办之初,制片人和主创人员都看过许多这些频道出品的片子,也借鉴了他们的讲述手法和拍摄技术,但他强调:“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本土节目。”
外来的“催生婆”与本土特色
制片人王新建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和DISCOVERY比喻为催生婆。作为中国纪录片栏目化最早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之一,王新建于1989年创办过中国第一个长篇纪录片栏目《地方台50分钟》(后改为《地方台30分钟》)。90年代中期,王新建担任《祖国各地》制片人,这期间,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的人文纪录片通过有线台等形式进入中国,这些节目给王新建造成的观念冲击甚至像是一种打击:“在我以前的知识里,‘地理’就是中学里的《地理》。这些片子让我惊奇的首先就是,‘地理’原来是这样的,地理片原来可以这么好看。那个对你传统观念一下子的冲击,真是没办法形容。”
随后王新建开始尝试在《祖国各地》里一个10分钟版块《旅游探奇》里制作这类纪录片,但时间太短,效果并不明显。1999年,王新建开始酝酿一个国家地理风格的栏目,写了很多策划方案,但都由于缺乏时机而无法实现。2001年,央视10套开播,定位为科教频道,王新建的设想大受社教中心主任高峰的赞赏,《探索·发现》栏目诞生。
王新建非常明白,《探索·发现》作为一个央视栏目,面对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因此,《探索·发现》尽管从节目内容上来讲和Discovery、国家地理一样都属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范畴,但并不能成为这些节目的简单COPY,而要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本土特色。因此,栏目的宗旨被定为:“中国历史探索,中国地理发现,中国文化传奇、中国风物大观”。
“章回体”纪录片VS娱乐纪实节目
针对Discovery将自己定位为“娱乐化纪实节目”,盛振华将《探索·发现》的节目形态定位为“大众化、娱乐化纪录片”。对娱乐与真实的把握,就成为栏目的关键。
盛振华用“章回体”来形容《探索·发现》的叙述模式,强调多线索、分层次的叙述结构和简洁有力的叙述语言。
栏目编导在报选题之前都要填一份报题表,在表中,编导要写出该选题的主线、副线,还要从悬念点、故事点、知识点、新观点四个方面对自己的选题进行阐述。这也是王新建与盛振华对节目走向的要求。盛振华还要求,这四个方面的必须能用两三字阐述清楚,否则将不予通过,因为“用2000字才能讲清楚的东西还能吸引电视观众么?”“能让观众在选择频道的几秒种间隙内被吸引的题目才是我们要的题目。”《新搜神记·武圣关羽》在报题时强烈吸引了盛振华,因为编导的悬念点是这样写的:关羽作为历史上的常败将军,为什么能在死后的1000多年里成为和孔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
《探索·发现》的选题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现在的考古学界、科学界没有定论的,这些题材对观众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栏目组就要经常面临一个如何在纷纭众说中去伪存真,而且还要确保节目好看的问题。国外的一些类似节目为了收视率,往往会选择最耸人听闻的说法,甚至编造情节,愚弄观众。对此,盛振华的观点是:“猜想的空间有多大,《探索·发现》就可以展现多大。但我们会告诉观众:一、这是猜想;二、有多少证据支撑这种猜想;三、反对这种猜想的论点及其证据。”比如在《三星堆》的制作过程中,由于三星堆本身的谜团太多了,考古学界内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导演就尽量客观地给大家呈现出各个学者的猜想和观点,同时尽量避免朝某个导向倾斜。比如在“情景再现”中,美术师画出来的三星堆人头上缠着白头巾,高鼻深目,很像阿拉伯人。为了避免在人种问题上的刻意引导之嫌,导演让美术师把白头巾改成了黑头发。
盛振华说:“观众有知情权,应该知道最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作为把关人,一定要避免传播伪科学的观点。”
不是NGC,也不是DISCOVERY
当记者问到栏目运作中面临的困难时,盛振华说:那可太多了。随后他列举了一系列问题:经费问题,既懂电视运作又懂人文地理的人才难找,资料找不到,专家不愿意配合,一年260期播出任务太重等等。然后他说:“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被拿来和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比较了吧,因为根本不可类比。”
不可类比,不是指制作理念。盛振华认为,在节目制作理念上,《探索·发现》完全不输给NGC和Discovery。不可比的,是两者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境遇。
无论是NGC还是Discovery,它们的成功都离不开四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专项科学研究机构、独立制作人、科学基金会、主流媒体。比如NGC国家地理频道的背后是建立于1888年的国家地理学会提供的大量素材和相关专家资源,而大量由国家地理学会或各种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独立制作人可以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拍摄某一题材,然后提供给主流媒体播放。另外,无论是NGC或者Discovery,作为拥有独立运营权的商业机构,都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全球化的营销平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题材、制作人、购买节目、推销产品。比如Discovery 的“探索国际联盟”和自2002年开始在中国举办的“新锐导演计划”。“国家地理”也正在和新加坡发展局合作一个面对全亚洲选择导演和题目的项目计划。这些都保证了他们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原创性的资源。
显然,在这些层面上《探索·发现》根本无法和这些国际大腕抗衡。作为央视的一个栏目,没有独立经营权的《探索·发现》无法实现基于知识产权之上的一系列市场运作,只能在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人员、有限的愿意配合的专家、有限的运作空间与理想之间斡旋。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拿多少经费,做多少事”:由于经费和人员有限,《探索·发现》有一半的节目都只能利用央视内部的影像资料进行重新编排,给观众提供一个新视角。而《探索·发现》的DVD、广告收入也和栏目制作人员无关。
这样的日子又能持续多久呢?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段锦川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丝毫不隐瞒对“新锐导演计划”的向往:“他们的投入就非常大,同等的制作量,资金投入可以说是央视的80倍以上,时间上也宽松很多,这对国内纪录片人很有吸引力。”
当然,全球电视节目市场竞争有多残酷,《探索·发现》的制作人员心里很清楚。盛振华说:“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说,成立不到三年的《探索·发现》所尝试的是一个新片种,而BBC自然历史部、Discovery、国家地理、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不会等着你发展起来再和你展开君子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