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玄虚何在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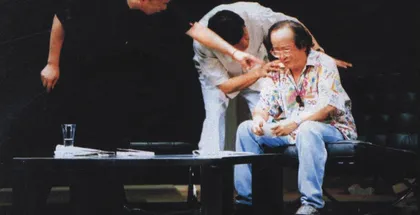
话剧《艺术?》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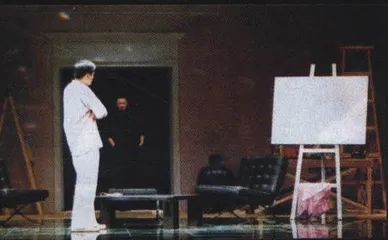
话剧《艺术?》和《生活秀》,一个在北京儿童剧场一个在北京保利剧场同期上演,两者相比,《生活秀》更容易接受,观后的议论多集中在几位演员的表演上。《艺术?》因为显得更玄虚一些,议论也就黑白分明得不像是在说同一场戏。
《艺术?》是导演魏小平译自法国的一出戏,他曾经以另一个版本在上海和北京的小范围内排演过,因为戏是从一人花了20万元买了一张画,而他最好的朋友把这张画贬得一钱不值开始的,所以他当时请了三位画家来演,而且在剧中用的是真实姓名,心理情景也从演员本人的经验里激发。但真正要搬上剧场演还得像现在这样请来了专业的名演员才像模像样。另一个《艺术?》由上海的一个话剧团几乎同时在上海演出,听说6月底即将搬来北京演出。
同一出戏有两个以上的导演动念头,往往显得耐人寻味,就如同去年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同时上演不同版本的《赵氏孤儿》,它不仅显示对戏剧的不同要求,更集中在对人、对生活的不同见解上。
《艺术?》是三个男人的一台戏,戏是从一幅画说起,一幅抽象画,画面全白,什么都没有,买画的人和朋友因为对画的不同见解,发生冲突。发生什么冲突?其实只是借艺术这个焦点而展开的复杂交情和观念较量,三个男人的心理才是让故事进行下去的动力。所以在这次重排时魏小平在“艺术”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大概是为了提醒大家点什么,其实大可不必。
原剧作者亚斯敏那·黑萨写于1996年的这出戏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都有上演。在法国它并不是以什么特殊的面貌在舞台上出现,是一出很情感化的戏,它的基本方向在略略谈论了一下那张白画之后,迅速落入了三个人的关系,三个人之间的情感,它更多的是在探讨友谊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语境中,直接谈论友谊之类的情感是不太合乎习惯的,很多细腻的情感更不宜直接诉诸语言,所以在魏小平的中文版里,很多争吵只能在艺术观念的冲突中进行,这一点是他做的一处本土化改变。
而且它的中心大意从友谊背后扩大到了人际关系背后,导演试图在这三个人的关系中能展现出人际关系的背后是权力的较量,哪怕是友谊、交情的关系,也许这是我们日常不愿面对,而实际上又冷暖自知的背后真实之一种。
剧中三个人物,老屁、铁皮、四眼,老屁是那个倾囊而出拿了20万买了一张白画的,铁皮是讥讽者,四眼是个没立场和稀泥的,但三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试图拥有控制三人关系的权力。铁皮一向以他的知识来压迫对方,以刺激的语言取得居高临下的优势,但他觉得老屁变得遥远了,他想了各种办法试图弄清老屁周围的情况,他无法容忍在老屁周围有一片晦涩地带,而这晦涩的地带越来越膨胀。终于,老屁从铁皮不熟悉的领域——当代艺术那里——拿来一张白画,也顺带拿来了一堆唬人的观念,本来他期待着用当代艺术就是要改变习惯、还要解构之类的话来取得优势,可是这些本来是艺术家骗收藏者的话没骗得了铁皮。铁皮也用很玄虚的话回应,比如,“藐视历史是你的权利,可历史粉碎后,你生存在哪里”之类。老屁又拿出福科来说铁皮,你之所以不懂这些是因为你没读过研究福科的书,铁皮也用福科的玄虚回应,“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
四眼儿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位,他从来是被另两人呵斥又必须帮助的一个角色,他的优势本来是哭,这是他获得权力的方式,以自取弱势给别人优越感而得到权力。而这一次,三人的平衡局面由一张画的出现改变了,任他怎么诉说他和后妈、亲妈、丈母娘之间的琐碎困境,另两个人都不再正面对待,在另两人的争吵中无论他站在谁的一方都会使冲突加入更多的成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当两个人终于动起手来,四眼趁乱自打一嘴巴,试图以他惯常的受伤姿态化解冲突,果然另两人一下恢复了对四眼的关怀,可惜只是一极短暂的一会儿,发现四眼并无大碍又回到了冲突点上。最后,四眼搬出了他的心理医生给他各种玄虚格言。本来,看心理医生是他试图摆脱自己不满意的处境,也是自取弱势的姿态,现在他在自取弱势也不能取得优势的时候,突然茅塞顿开地发现了另两个人的疯狂。他也要拥有居高临下的权力。
剧中有很多关于当代艺术的辩护,也有大量讥讽,尽管到最后还是用当代艺术的某种观念逻辑让他们的关系达到新的平衡,因为他们毕竟互相依赖,但导演显然并不准备在剧里讨论所谓“白画”的意义和价值。他要突出的是人之间的对抗怎样以观念对抗观念的外表演绎着,观念变成了权力,这就已经是对整个大环境的描述了,而并不只是三人友谊关系的局部事件了。在一个飞速变化着的环境里,人们经常遭遇到的是理性、观念的威胁,用感性经验与之对抗的结果,往往是感性败下阵来,理性观念永远有理,但像剧中人一样,我们对理性和观念的接受却是非常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