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9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困困 莫幼群 大仙 广广)
英国捉鬼队
◎困困 图◎谢峰
我当初租下这间房子的时候,就对墙上那面号称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镜子向房东抱怨过。我一直觉得镜子这玩意,熟读身体,化为影像,想来就很诡异。而我墙上这面,从那么遥远的年代过来,说不定哪天我对镜贴花黄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个张着獠牙的公爵,或者一个金发女郎缓缓将腰封解开——里面是一架滴着血的骷髅。
房东将我这绘声绘色的想象,完全当成缓解陌生的有趣闲聊,她给我讲述了英国著名的捉鬼队。她说,这个队伍曾经在伦敦的汉普顿宫捉住了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五任老婆的鬼魂。可以说,哪里有鬼哪里就有他们。说着,就在我的电脑上找出他们的官方主页。该队伍大号为:英国超自然研究组织。房东最终也没有将我的镜子换掉,倒是不停暗示,如果该镜子出现了什么超自然现象,我大可联系这支捉鬼队。
时隔大半年,我都快忘了捉鬼队这茬儿,竟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在行动——在英国皇家海军的邀请下,已经潜入普利茅斯一个海军船坞,来调查船坞里一个刽子手房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主绞索房的闹鬼事件。他们邀请了布鲁内尔大学的教授、数名科学家、灵魂学家同往。并在进入船坞之前,举行了一次“降灵”仪式,向鬼魂们说明来意。报纸上还说,捉鬼队员们随身携带了床及家居用品,准备在船坞里安营扎寨日夜追踪鬼怪行踪。而队员携带物品中,还有一些儿童玩具,是为了给那些不期而遇的小鬼魂玩的。而他们最大的目标,则是找到出现在船坞里的一个穿着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少女和一名蓄了胡子的水手。
这则新闻又勾起我对这个“英国超自然研究组织”的兴趣,找来他们的主页,仔细查看。“鬼是一种非实体的、不能与之沟通的东西。它其实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影像记录,并且在一定的大气条件下,以光谱的形式出现。它的移动轨迹是固定的。”他们尽量用科学来解释鬼怪现象。这个不喜大兴土木的岛国,应该处处皆鬼了——什么圣保罗威斯敏斯特都不要说了,随便一个教堂都辗转数代,而古旧庄园、百年小巷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历尽沧桑的实体上,得附着了多少那叫做“鬼”的能量的场呀。
但似乎这个组织“一言以蔽之”的说法并不能解释所有超自然现象,他们的许多调查报告就老实地说:无法解释此现象。鬼怪魂魄,或许有或许没有,我既不清楚也不敢断言,只是觉得这些东西,说到这儿该打住了。如同《大鱼》里的老布鲁姆对他儿媳妇说的:不谈论宗教,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亵渎什么。鬼的事儿,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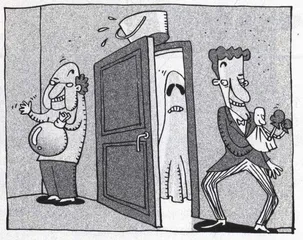
半糖主义
◎莫幼群
拴住了男人的胃,也就拴住了他的心——这话对一般人适用,对爱因斯坦就不起作用。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就经常给他寄来大包大包的甜点,当时爱因斯坦经常怀抱装着甜点的邮包,趾高气扬地在大街上走着。但爱因斯坦最后还是抛弃了米列娃。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怕是因为爱因斯坦后来去了美国,那里有更甜更诱人的东西等着他,瘦小的米列娃连同她干巴的小甜饼就不在话下了。
美国人对甜东西的消费量真是大得惊人,就连花生也要裹上粘糊糊的糖衣弄成“蜜制花生”。但他们吃得最多,对甜食的批评也最厉害。在批评者眼里,甜与咸有着本质的不同,咸是人的味觉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甜则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从来就是为满足人的贪欲而存在的,所以甜食是一种原罪,正如肥胖是一种瘟疫,让人避之不及。科学家甚至从巧克力中分析出了一种“糖毒”,来吓唬那些吃巧克力上瘾的小女子。有了以上道德和科学的武器仍嫌不够,还要祭出“品位”的法宝——保罗·福塞干脆说:“你可以根据每个家庭对糖的消耗量来划一条可靠的社会等级分界线”,吃糖越多的越不贵族。
美国人一半心虚一半自豪地认为,贵族还是在老欧洲,尤其是在他们的英伦老祖先那里。一位美国游记作家这样写道:英国人所吃的茶饼、软面饼、窝饼,味道总是那么淡,“你请他们吃真正有吸引力的东西,例如一片法式浓味的糕饼或比利时巧克力,他们总是会犹豫上好一阵”,最后“拿起块最小的,其表情仿佛是在做一件极坏的事”。这样子的扭扭捏捏,大概就是所谓的“半糖主义”。这词我是从S.H.E的歌中听来的,“我要对爱实行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女孩的心思不猜也能明白,这是把男孩当孟获——欲擒故纵。而我以为“半糖主义”应该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在物质生活的各方面加以贯彻实施:在吃饭上就要实行“半饱主义”,八分饱已是顶点;在喝酒上要实行“半醺主义”,千万不能做日本人“喝死也熊”;在运动和娱乐上要实行“半爽主义”。
然而夏天到了,满眼的冷饮和甜品对想要实行“半糖主义”的人构成莫大的诱惑。我主要是未能忘情于那种加了豆豆枣枣的冰粥。只是我吃任何有点脆性的东西,总喜欢吃出响声来——一个师爷级人物混在少男少女当中,还吃出那么大的动静,难免就有人侧目了。这时我会想起叔本华的一个故事。一次在饭店狼吞虎咽的叔本华见另一位食客老是盯着他看,便走过去说:“别看我,我的饭量是你的两倍,而我的头脑也是你的两倍。”这让近两百年后的我感激不已,感谢他喊了如此睿智而又响亮的一嗓子,维护了贪食者的尊严。
城乡结合部
◎大仙
随着外地务工人员大举进京,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在首都各条战线上勤劳工作着,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日益发达,农贸市场、建材市场、旧货市场、批发市场风起云涌,小贩小商们安营扎寨,当街摆摊,虽然分不清他们是“有照”还是“无照”,但确实给我们的生活以方便。柴米油盐、锅碗瓢勺怎么就不能有风花雪月?衣衫褴褛中,照样红袖飘香。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是一种工农相结合的生活;城乡结合部的浪漫,是一种话糙理不糙的浪漫。
在紫禁城的边缘,有我故乡的花朵。是谁写过“故乡面和黄花”?1981年,我在牛王庙奔向苇子坑上班的路上,就在颠簸的302路公交车中,写过“故乡炸酱面和交际花”。在周杰伦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早已用吉他把“东风”弹成了“破鞋”。孙河的一川逝水、酒仙桥干枯的河道可以作证,在清风徐来、青春兴旺的年代,我们唱着同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什么什么的事情。
我生于酒仙桥,长在大山子,工作于798,是城乡结合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当798成为一个艺术概念之后,我已放弃了艺术。1993年,我带着北京申奥惜败的遗憾,回家路过“大山桥”,借着酒劲儿差点爬到桥上,把“大山桥”改成“大仙桥”,就差一单立人儿,这桥就不是我的桥。
酒仙桥电子城,是城乡结合部的一面旗帜,后来被中关村夺走了霸主地位,我至今耿耿于怀。虽然我把青春献给了电子城,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是一“三无人员”,无电视、无电话、无冰箱。1978年夏天,街坊邻居中一个只有貌没有才的女孩,把我邀请到她家看中国第一次转播世界杯,我有幸目睹了现任中国队主教练阿里·汉一脚长达44码的超远射。中场休息时,女孩打开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喝的“青岛啤酒”,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才貌无法双全,从今以后,我发展貌,你发展才。听了她的话之后,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青梅竹马的召唤。于是,我把跟才华有关的事儿全办了,相貌上只能一无是处。
就在“西北风皇后”杭天琪就读过的酒仙桥中学对面,是著名的“电子溜冰场”,每到冬季,这里就成为“男拔份儿女展盘儿”的“碴冰之地”。我一咬牙,就把国产的齐齐哈尔长白冰刀换成了加拿大奥赛冰刀(用做冬奥会比赛的冰刀)。在月光与冰光交织的夜晚,在施特劳斯冰上圆舞曲的“轻hi”之中,在盘儿亮条儿顺的北京城乡结合部女孩一字排开之际,我们这些青年男工们在冰上疯狂兜着大圈,然后在所喜欢的青年女工面前一个急刹,伸出手,拉住手套中的玉手,把她们带入场中。女工用正滑的姿势走外道,男工用倒滑的方式走里道,男工对女工都说着同样的话:别慌,有哥们儿呢,要摔咱俩一块儿摔,要死咱俩……
美食当道
◎广广 图◎谢峰
好莱坞的知识分子伍迪·艾伦在他的一部电影里夸赞他的旧情人戴安·基顿说:“她是很棒的厨师。她的鸭子和茴香荷包蛋,荷兰式调味料的扇贝和菌块加甜面包,给你超级享受,让你躺在床上回味一个月。”言外之意是,虽然我们已经是一对老得不合脚的旧鞋子,但是由于这重要的一点,还维持着美满的关系。
千万不要小视伍迪的观点。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种美味关系的忠实拥趸。她的至理名言是:眉眼是一见钟情,厨艺是长相厮守。而且她还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这个理论。她的冰箱贴、她的穿衣镜、她的床头板,甚至她的抱抱熊身上,都密密麻麻地粘贴着顺手抄下的、打印出来的、从美食报刊上撕扯下来的——食谱。不幸这位美女最拿手的厨艺,仅限于在煎锅上做一只单面煎熟的煎蛋。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终身理想的追求——千万不要忽视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些触目可见的美食,最终会融化在她的骨血里。
不过,话说回来,吃真的已经融化在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那些我们景仰的名人,无一不是个中高手。众所周知,村上春树是一个好吃的家伙,从他的字里行间,已经归纳出数本畅销的菜谱;美妙的女作家弗朗西斯·梅耶丝说,《在托斯卡纳的太阳下》的雏形,原本是一个塞满了菜单的记事簿子;更有甚者,放浪形骸的安东尼·伯顿在他正在热销的《厨室机密》开篇指出,对他而言,“烹饪就像一场长时间的恋爱,食物一直就是一种冒险”。
总而言之,自从美味的食物诞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口腹,还为我们制造出美妙的人际关系。美食将人带回到最为原始质朴的那个层次,让我们享受到那种最单纯简单的幸福。一一这足以令我们对它顶礼膜拜,难怪欧洲中产阶级会将“慢食主义”进行到底。
然而,每天享受这样一口单纯的幸福,不是我们每个人所愿吗?在我们也成为一对老得不合脚的旧鞋子的时候,还能依偎着为彼此送上一口幸福,难道不是我们的理想吗?
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