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戴高乐机场事件与安德鲁中国“实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2004年5月23日清晨,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屋顶发生大面积坍塌。事发后,警方封锁了现场,有关部门随即清空航站楼,并成立了一个应急救援小组处理事故,就地展开全方位医疗救助
创意与风险
一个荣誉的标志转瞬成为一场事故甚至是灾难的代名词,安德鲁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境况。
从建筑师的角度审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耀东这样描述戴高乐机场候机楼: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并置,其中充满了多样、复合的建筑空间,它们一同把整个戴高乐机场塑造成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2E候机楼在这个复杂的建筑空间中和2F候机楼承担法国飞往北美和部分亚洲航线的联接作用——巴黎到上海、北京、香港的航线从2E大厅起降,也因此坍塌中遇难的4个人中,2人是中国人。
在这个被誉为有着“高品质的完成度和撼人心魄的感人力量”的机场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人们把着眼点放在其大跨度的空间设计上。有资料说,2E候机楼的基础设施是廊桥停机位,能同时处理17架飞机的飞行和降落,年承载客流量1000万人次。正因为承载运能大,所以安德鲁采用了钢结构混凝土的大跨度设计。
安德鲁就此的回应是:我不会花费任何一分钟来推测是什么导致了这起事故。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设计在很多地方是大胆的,但机场建设采用的建筑材料则是毫无创新的。
戴高乐机场的建设已历经30余年,当人们惯性地提到安德鲁和巴黎机场公司时,会惯性地把他们与机场设计联系在一起——他们积累有50余座机场的设计经验。为即将出版的《保罗·安德鲁的建筑世界》作序的吴耀东这样描述说:1967年在他(安德鲁)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等国际机场,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基本概念也出自他之手。他参与过许多大型项目的建设,像巴黎德方斯地区的大拱门、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等。在他的影响下,巴黎机场公司逐渐向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维敏由此说,建筑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实行的是终身负责制,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作为机场总设计师,安德鲁并没有最后摘除与此次事故的关系——质疑的声音指向他的创意本身,包括工程难度很大,施工人员必须将金属与玻璃结构结合在一起;涉及热学专业知识。比较起来,这些质疑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是创意的罪魁祸首,在事故原因最后确定前,更多责难指向更具体的工程实施过程,比如土质沉降度、疏松度等变化产生的安全隐患;比如工程实施速度要受来自法国航空公司和巴黎机场要求提前完工的双重压力等等。
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让人们更多讨论的一个话题是:面对新作品的煽动性,如何能够不盲目,除了考虑新奇作品与城市的构造、性格、传统相融,安全性是附加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实际上,以作品系列和建筑追求“非常独特”著称的安德鲁已经在全球兜售他的创意。在安德鲁29岁的辉煌之后,1996年,他在国际竞赛中拿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从1998年开始,每年均有收获:先是广州白云山体育馆,第二年是北京国家大剧院,第三年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吴耀东说:“一位外国建筑师,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先后进军素有京派、海派、广派之称的中国三大重要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主持设计的总建筑面积达50余万平方米,值得研究和关注。”
安德鲁们的中国行
明星建筑师们怀揣他们的得意之作进入到中国,几乎总要伴随相当大的争议。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建筑史中,80年代是贝聿铭和他的香山饭店,近期的代表则就是保罗·安德鲁和他的北京国家大剧院。
贝聿铭的到来显然有政府行为因素,他“被邀请、委托”做香山饭店项目。吴耀东说,香山饭店是有关中国建筑走向争论的一个开端,而安德鲁和他的国家大剧院将这个争论推进到一个空前激烈的层面。吴耀东说,这是中国建筑界思想上的大争论,是在北京坚硬的外壳上戳了一个洞,它有标志意义,就是我们的城市要不要面对未来。
这个标志性意义的再一个体现是,标新立异的建筑开始在一些重要项目中成为焦点。库哈斯宣称他为中央电视台新台址设计的那个西方式的高大建筑“不是传统的塔,而是一座由水平和垂直部分构成的连续的环状城市风景”。
这些国际著名的明星建筑师在中国到处参与竞标。在成都,一个项目竞标中也有安德鲁,有说法是,第一名不是安德鲁的方案,但当地政府知道安德鲁与国家大剧院、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相互关系后,就有选择安德鲁的倾向,吴耀东说:“政府决策不完全错,但有没有猎奇的成分在里面?毕竟是政府这只建筑看不见的手在决定城市的形象。”
库哈斯在去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他选择中国的理由时说,“9·11”之后,美国对自身越来越重视,这种内敛是普遍心态,而中国却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中国正是这些明星设计师们的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庄维敏说,曾经有些国外建筑师私下和他聊天表示,在中国市场非常好,创作环境更宽松,对他们非常适合。
从建筑师的角度,建筑就是某种冒险,吴耀东说安德鲁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建筑冒险:圆形、椭圆形、球形和各种柔美的曲线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再现,以纯净的几何形构成的建筑得以成立是有相当难度的,在安德鲁手中它们不仅得以实现,而且携带上了丰富的情感,反映出他独特的建筑直觉和控制力。“安德鲁的建筑充分体现出丰富的几何形体、对结构的大胆运用和情感的收放自如,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创作结果是不同的,共通的是作品中都充满着新的发现和求索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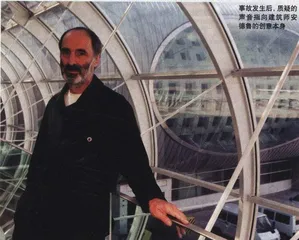
事故发生后,质疑的声音指向建筑师安德鲁的创意本身
库哈斯研究中国南方城市的一本著作的名称现在被通用于概括外国明星建筑师与中国的结合:大跃进。
盲目崇拜问题
吴耀东说他不喜欢人们谈到国外建筑师在中国是把中国当成“试验场”,“这是一个事件”,他说,“这里没有强行推销,主动权还是在中国这里,关键在于选择的人和选择的规章程序,中国自己的社会有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中国大的环境事实是,有学者说,目前中国还处于设计师可以任意发挥个人想象,开发商可以为了商业利益不顾一切。作为城市来讲,我们的政府还没有一个公共意识的提示,这等于是设计师自己给自己提供了实施公共空间的游戏规则,因此没有可参考的规则。
在这样的城市发展中,位置有些尴尬的是中国本土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朱小地说,目前工程设计采用国际招投标方式已司空见惯,在很多重大项目的国际招标中所邀请的境外设计公司数量明显多于国内设计单位,有些项目根本不邀请国内设计单位参加,如果要参加也得和一家境外设计公司合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境外单位中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庄维敏因此评论说,这是一个评价机制问题,对境外的明星建筑师,我们有一点神话,有一点盲目崇拜。
中国建筑师目前作为一个群体的弱势在于,朱小地说,我们的建筑师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敢直面建筑产品所特有的社会性,从国情出发面向未来的对策研究还停留在自发状态和起步阶段。种种因素结合起来,朱小地感慨说,如今大凡工程设计似乎如不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不通过合作设计来完成就建造不起来似的。由此合作设计很自然地成为一种形式,一种时髦。也因此我们的本土建筑师有一点失语,不敢表白,庄维敏说,不只是建筑师,甚至是媒体、政府、专家都存在这种倾向。

有难度的建筑作品在安德鲁手中得以实现,他的作品充满着新的发现和求索的欲望
作为建筑师的安德鲁
今年保罗·安德鲁已经66岁,他几乎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建筑师而存在的一一从在法国高等工业学校(EcolePolytechnique)毕业后,他进法国道桥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Chaussees)和巴黎美术学院(Ecoledes Beaux-Arts)学习,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候机楼而一举成名。
谈到自己的作品,安德鲁坦言说他始终对个性化和风格问题毫不关心,在他看来,建筑活动的最大原动力来自于建筑始终处在没有完成的感觉,使之完成需要将光、水、风等自然要素加入其中。他关注的是空间本身,关注自然光在空间中的演出,关注融解在光线中的结构形式。在这样的空间中,绝不有意非要加入个人的感情。他认为空间是无法预测的使用者情感的共鸣器。处在感性和理性世界中的建筑,可以说只是提供了演出的舞台。
安德鲁认为,建筑最初是建筑师的工作,在不同思想的交流中发展出来,在此基础上,他坚信通过与诗、文学、音乐、绘画和科学的交流,更能使建筑得到繁荣,因为在所有思考领域中共通的是这个时代基本的共振作用。建筑最为单纯和基本的方面应该是如何超越其物理意义上的需求。建筑深深扎根于技术和经济的世界中,当试图让建筑充满活力、充满其他期待时,是需要超越技术和经济世界之上的。
安德鲁的建筑鲜明地体现了其坚定的信念——不论在功能处理上还是在建筑风格上,都决不屈从于任何先验的规则,而宁可去寻求在功能、经济、气候等方面都适合于每个项目特殊性、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在安德鲁的作品群中,简单的几何学形状与复杂的形状同时存在,在同一建筑中,简单的部分与复杂的部分对立共生,不同的因素被组合成一个整体。戴高乐机场就是最为典型的实例。
现在,安鲁德刚从巴黎机场公司独立不久,他开设了自己事务所。在安德鲁看来,建筑若能尝试异质因素的共存是非常有趣的工作,当把自己认为已知的、已经明白的事物稍微变换一下角度,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来思考时,就会产生出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