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看西看:性,电影,反叛者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电影《梦想家》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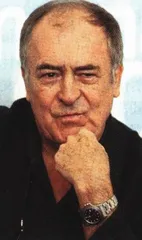
贝托鲁齐
有时候,我真佩服贝托鲁齐这种“老革命”,虽然他已不再像青春时代那样相信能改造世界,不过言语之间还带着梦想气质。有些极端的人认为贝托鲁齐因《末代皇帝》而成为好莱坞的“同流者”(《同流者》是贝托鲁齐的名片之一),所以不能说他是“老革命”了,不过在我看来他就够坚持了,在奥斯卡奖上他为了摆脱被收编的嫌疑,还把好莱坞称为“big nipple”,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在欧洲找不到的东西,又远走他乡到亚洲去找,到非洲去找,结果是《末代皇帝》、《遮蔽的天空》,也许并不成功,但是他好像还是真心诚意的。后来他终于逆子还乡,重拍欧洲题材的电影,好像有些倦意,都是比较私化平淡的作品了。
贝托鲁齐近作《梦想者》(The Dreamers),算是对自己1968一代的革命青春做个回顾。那时他27岁,在巴黎是狂热影迷,激进左派,性革命的一员。事实上,今天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年代”,他说一切都围绕三个主题:电影,政治,性。他的新片《梦想者》,就是把这三件事搅在一起。
在今天已很难想象电影对知识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而6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年代。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费里尼……他们的新片是欧美小资青年的必修课,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一切的中心又是巴黎的《电影手册》杂志和电影中心。意大利中世纪小城帕玛出身的小资青年贝托鲁齐,就带着朝圣者的心态,来到巴黎(以致后来他成名后曾经希望用法语回答记者的采访,因为他认为那才是谈电影的语言)。当然,他还向往革命,向往性(也许那属于自身革命),这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革命之前》中早已表露无疑。结果,那一年似乎有很多这样的青年在巴黎,1968年的春天,法国政府决定解雇电影中心负责人的决定,使得激情一触即发,从维护电影馆的艺术独立性,而引发了一场革命风暴,触及了法国社会各个层面。电影,政治,性解放,真的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后来贝托鲁齐的电影也经常触及性与革命的题材,《巴黎最后的探戈》震惊,《1900》是意大利版的阶级斗争。《梦想者》则是把他对电影的迷恋加进来了。
电影改编自一个英国人的自传体小说,如上所说的对电影迷恋的美国男孩来到巴黎朝圣电影,结交了一对孪生兄妹朋友,这对兄妹的父母出外度假,所以巴黎的那所书香公寓成了这三个大孩子为所欲为的伊甸园。窗外的街头在爆发革命,三个影迷一边聊电影,一边闹性革命,最后还是上了街。这片子美国的发行人要动剪子剪掉正面全裸,以PG级发行,后来贝托鲁齐据理力争,说在美国大众为什么能看非常暴力的电影可是不能看有性场面的电影,还真把发行商说动了,没动刀剪定为NC-17级公映。不过这年头离《巴黎最后的探戈》已经三十余年,所以不会引起那种轰动,但毕竟唤起艺术电影爱好者一些怀旧之情,对曾经的那个激情年代。不过,《梦想者》的切入角度是一种青春自恋式的,没有一点过来者的以今日眼光的自省自嘲—1968 一代的青春,是严肃,认真的,不带一点玩世不恭的,所以今天观众观后的反应是两类,或者是眷恋,或者是否定。
说实话《巴黎最后的探戈》的性表现我是从来觉得莫名其妙,第一遍看时听不懂英文看不下去,第二遍看时听懂英文了更看不下去,也许正是所谓时代不同了。贝托鲁齐还一直对乱伦题材有所独钟。《梦想者》中的兄妹就又有那么点乱伦的倾向,也许贝托鲁齐讲的是像他们这种梦想者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总而言之,《梦想者》中的表现性既然没有《巴黎最后的探戈》在特定时代的那种震撼效果,又没有特别的新意,所以并不特别令人欣赏,除了青春身体永远能引起的赞叹。至于两兄妹的“革命气质”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带有一种被惯坏了的骄纵,是一种负面法国性格的体现,不能唤起观者的共鸣。因为影片写性、政治、电影三主题,而角色正好是三个,所以当然有些象征色彩。这也是美国观众和欧洲观众看这电影的分别:美国人看全是道德沦丧,欧洲人看的是隐喻象征。

写闹革命着笔并不多,主要是个背景气氛。所以影片看着比较好玩的地方,还是影迷部分。它把很多经典电影剪了进来,让三个死硬影迷不断模仿名片,比如女孩子模仿嘉宝在《瑞典女王》片中的表演,比如戈达尔的《一伙局外人》中女孩子和两个男孩在卢浮宫狂奔,要“创造穿越卢浮宫的世界纪录”,而《梦想者》中的三个孩子也这么狂奔了一回,要打破《一伙局外人》中的纪录,镜头在《一伙局外人》和现在的三个孩子之间切来切去,是对戈达尔的致意,也是对影迷青春的致意,很是表现了一种电影为影迷带来的独有的浪漫。贝托鲁齐自己说,电影不是现实,电影是现实的影子(shadow of reality),也许这种现实的影子正是青春最热衷追逐的东西吧。贝托鲁齐的梦想,总是围绕着电影,改造世界,以及性。最终,是他对电影的梦想始终感染我们,因为电影把梦凝固在了胶片上。
贝托鲁齐在访谈中说,虽然影片有他1968年在巴黎经验的影响,但是那时他27岁,所以毕竟是20岁的片中人的哥哥了,不能说是自传,但是片中人为卓别林高还是基顿高之类的问题争论不休却是完全来自他自己的经验。说了半天,革命也罢,性也罢,贝托鲁齐是个艺术家。他在电影中做梦,他也还在用电影做梦。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少作《革命之前》。革命之前,那种蒙蒙胧胧的梦想是多么奇妙的状态,那是革命之后永远难以复原的状态。到过欧洲中世纪小城之后,多少对贝托鲁齐这样的艺术家有更多的了解。那种中世纪小城,我现在去了都容易做梦。
天主教的氛围,又让独立思想者对性的禁忌有一种特别的反叛。像贝托鲁齐这种具诗人气质的人(他是诗人之子,也以写诗起始),在这样的小城成长,最终成为一个故乡的逆子(不表明他就失去了对故乡的深情),一点也不奇怪。《梦想者》里,最让人喜欢的其实是那个美国男孩,也许有些贝托鲁齐自己的影子。影片也用了些60年代的摇滚经典,尤其“门乐队”(the door)Jimi Hendrix的歌,却是惟一让我感到血管动容的地方。而贝托鲁齐毕竟是在回忆青春,那是青春的影子,不是青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