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教英文的风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一则旧闻:“昔有书生携一仆入太行山,仆见道上碑字,误读曰‘太行山’。书生笑曰:‘杭也,非行也。’仆固争久之,因曰:‘前途遇识者,请质之,负者罚一贯钱。’行数里,见一学究授童子书,书生因进问,且告以故。学究曰:‘太形也’。仆大叫笑,乞所负钱。书生不得已与之,然终不释。即别去数十步,复返谓学究曰:‘向为公解事者,何错谬如是?’学究曰:‘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教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袁宏道《题陈山人山水卷》)
一则新闻:西南交大学生王军(报道中的化名)在某家教中心登记担任英语家教,按家教中心提供的电话号码与学生联系,接电话的是一中年男子。当王军询问对方学习英文的动机何在时,该男子沉默了一会儿答曰:“我也不想和你拐弯抹角,就直说了。我主要是想学英语口语,方便给客户介绍小姐。我每小时付给你人民币25元,你每周给我上一次课,要教哪些口语我到时给你说。”王军深感惊讶,尽管该男子随后表示可以提高酬劳,但气愤的王军还是当场拒绝了这份工作。(据《华西都市报》)。
太行山上,峨眉山下,两桩事体的共同主题可以归纳为“因一方拒不传授(正确的)知识而导致的被误导或求学不得”。当然,罢教的理由略有所异,昔者系因鄙夷求教者的“俗子”身份,今者乃出于对皮条客及其动机不纯之严重不齿——“宁可不赚那每小时25元,也教你丫终生拉不成英语的皮条。”
在单纯的技术层面,“动机”同样重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证实:一个人的动机对于他的外语学习成果往往起到至为关键的影响,即所谓Given motivation,anyone can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well.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Gardner和Lambet把外语学习动机分为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前一种,就是出于对该种外语及其文化的兴趣或者融入第二语言社团的冲动。后一种动机则以实用为本,即把外语当作实用工具,用之于应付考试、阅读文献资料、求职、改变社会地位,等等(据“中华英才网”去年发布的薪资报告,在我国,“熟练外语人士”与“外语水平中等”者的平均年薪差价达到17000元)。研究表明,虽然两种不同动机的学习者都有可能获取外语水平测试的高分,但值得提倡的还是“融入型动机”,因为后者不仅相对更容易成功,还能将成就更持久地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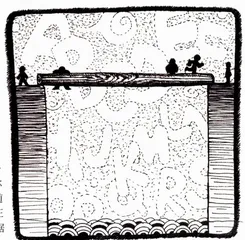
因此,“疯狂英语”里“学英语报效祖国”的集体咆哮,跟“我主要是想学英语口语,方便给客户介绍小姐”皆可归入“工具型”一类。也就是说,就学习动机而言,新闻中被拒绝的那名中年男子其实与大部分学习外语的同胞上具有技术上的完全一致性,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了技术性,动机通常还具有它的道德层面,不然,该中年男子岂不是可对“中年高玉宝”这一称号当之无愧了?尽管孔子说过“有教无类”,但他也留了“因材施教”的后手。王军在撂下电话之后的健康心理活动大概可以这样描述:皮条客当然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只是向这种“材料”施教的应该是在另一个特定地方上班的另一些特殊的教师。
道德考量本身是不分什么integrative还是instrumental的,如果非给它找个动机的话,不妨视之为一种requirement。以经济学观点计之,王军只是出于法律风险成本的考量而单方面中止了一宗交易,一旦转换至道德立场,顷刻间就会发现王军其实是办了一件大事。凡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中国学习过任何一门外语者,不管学好学坏,一句名言想必无人不晓:“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不管是德语原文中的Waffe还是英译的weapon,“外语即武器”,尤其是攻击性武器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是故向他人传授一门外语便相当于向他人授武,若以此收费,则等同于售武,如果不做任何道德考量,对于社会安全乃至人类文明都具有相当的危险性。王军说不,就是坚决而及时地阻止了一项既卑鄙又非法的军售活动。又有一段语录:“手段的卑鄙只能说明目的的卑鄙。”此说之所以是一项科学论断,皆因其可逆,也就是说,目的的卑鄙也只能说明手段的卑鄙。拉皮条无疑是卑鄙的目的,身为学生兼家教,王军的拒绝不仅确保了学习外语这种手段不至因此而在逻辑上被“说明”为卑鄙,捍卫了道德,也捍卫了科学——当然,一名大学生的英语水准能否满足皮条客在会话学习上的专业需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由此看来,教授外语,教授母语,乃至人类的一切教授行为,都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这种风险还包括:毕业后王军若选择教师为职业,很可能会活活累死;若不幸当了一名律师,估计就生生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