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二人转咋就那么火?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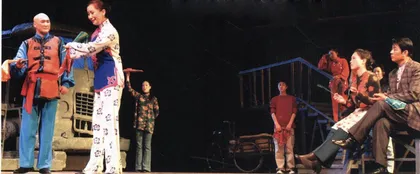
2月6日晚,一台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的北方风情剧《秋天的二人转》在南京上演,剧中穿插的现代二人转表演让观众耳目一新
对东北以外的人提起二人转,都会想到赵本山——这个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小品出名的演员用他的名气和影响力,让中国更多的人知道了二人转。二人转受到媒体关注的原因不仅因为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它内容上的受争议,当中央电视台在今年的相声小品大赛上发生的“二人转叫停事件后”,这个东北地方戏就更受到关注。时隔几天之后的“东北二人转进京大拜年”在北京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七频道也都在先后做二人转的专题节目……种种迹象表明,二人转已成了现在的一个文化热点,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以赵本山为中心。
赵本山在把二人转推向全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点:二人转在东北,有两个重要基地,一个是沈阳,那是赵本山的“地盘”;另一个是长春,相比而言,吉林省的二人转是最活跃最正宗的,而长春市的和平大戏院可以说是目前东北地区水平最高的二人转团体,甚至赵本山的那个二人转团体里就有9名从和平大戏院“转会”过去的演员。
和平大戏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现在二人转在东北到底又是什么样子?记者在春节期间专门去长春做了一次采访。
培养一对成熟演员要投入几十万
提到和平大戏院,不能不提戏院的总经理徐凯泉。徐凯泉今年46岁,以前是长春市演出公司民间艺人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年下海开了和平大戏院。徐凯泉任演出公司办公室主任时候,就常常和二人转艺人打交道,他发现,二人转这么个深受东北人喜爱的地方戏,发展越来越畸形,专业团体不景气,演出没有人看,而民间艺人表演团体常常被列入扫黄打非对象。出于对二人转的热爱,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二人转发扬光大。
现实中的徐凯泉是那种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为人爽快,说话实在。提起二人转,他一方面为他能亲手把二人转带向一个新高度而自豪,另一方面也为时常遇到的问题而烦恼。
徐凯泉和赵本山的思路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在做二人转,赵本山由于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他希望二人转能走出白山黑水,红遍大江南北。而徐凯泉则不同,他太热爱二人转了,以至于每往前走一步,都要想想是否会给二人转带来负面影响。他平时都吃住在大戏院里,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们家”(指和平大戏院),而那些演员在他眼里都是他的孩子。
谈到之前那次二人转进京,徐凯泉说没想到那么成功,但同时也有些忧虑,因为那次进京演出的成功,现在有不少团体找到他,希望他还能带些演员到北京。但徐凯泉说:“北京文化品位比较高,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殿堂。二人转在北京没有牢固的基础,万一有个闪失连个退路都没有。”徐凯泉还有另一种担忧,怕这些演员离开他身边,出门见了世面,回来就不听话了。去年演员去沈阳参加“本山杯”小品大赛,结果就有9个演员跑了。
徐凯泉的经营思路和很多人不一样,用他的话讲,“现在二人转演员收入非常可观,住的房子比市长住的都好,有车,有存款。敢说我带的人都奔小康了呢,这是事实啊。”他的戏院不仅有演员,还聘用了很多导演、策划、艺术指导等专业人员,通过这些专业人员来提高二人转的档次和艺术魅力。这样的结果就是演员在培养时成本增大,一对演员从进入戏院到最后能登台表演挣钱,戏院要投入几十万,所以,一旦演员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离开戏院,徐凯泉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不依靠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徐凯泉说:“我跟演员表面上就是签一个长期合同,如果他们真是往外跑,我也没啥招。但人都是靠一个感情,来的时候啥也不会,一大帮人住一个炕上,好几个人盖一条被子,穷的一天就能挣三四块钱,我一个月给他们开一千多块,大米饭、炖肉吃着,我教他们识谱,教他们乐器,教他们怎么做人,平时导演、艺术总监还给他们上课。完了你再跑了,那也太不道德,太不讲究了。所以就得靠感情,我干的事情都是反着的。你说我怎么控制啊?去打骂他们行么?如果我伤害一个,全国这么一传,我不就成了黑社会了吗。所以,就得去感化他们。他们要是人,有良心,就做点人事。哪个行当其实都是这样。只不过我这个行当难度要大一些,毕竟他们都是艺人,有的没什么文化,我们家不识字的有得是。”
徐凯泉靠感情这个在今天看来已经很脆弱的纽带来维持他与演员的经济关系。有的演员做手术了,他会拿出手术费,还要补贴点营养费,天天去医院看望。有的演员想谈恋爱,他中间撮合。虽然在市场经济下,这种感情投资相比法律约束显得很脆弱,但在东北这个地方却往往能收到效果。比如,有地方想把艺术总监梁学田挖走,对方的位置一直给梁学田留着,但梁学田一直没走。还有“老翟头”翟波,从徐凯泉创业那天就跟着他,赵本山拍《刘老根》,老翟头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赵本山想挖他走,但老翟头没去。徐凯泉说:“只要我不死,他就跟着我,我们俩签的是终身约。”刚刚走红的新秀孙小宝还没有跟大戏院签约,但徐凯泉说:“跟签约没啥区别。”赵本山的搭档高秀敏想收孙小宝做徒弟,孙小宝没答应。甚至,中央电视台请孙小宝到北京做节目他都不愿意去,他就跟定了徐凯泉。徐凯泉告诉记者:“我每年的感情投资要扔进去80万,而且一点响儿都没有,今年在这方面的投入还会更多。”

二人转在长春已经成为社会最主要的文化现象和旅游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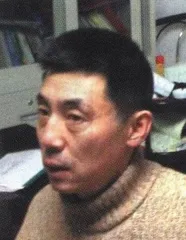
徐凯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会这样,北京有很多夜总会请和平大戏院的演员表演,在这些地方演出,演员每晚最多时候能收到6000元小费,想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夜总会老板一句话的事情,这种诱惑对于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演员来说的确太大了。结果就是演员从外面回来之后就不好管理了。对此,徐凯泉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说:“有人对我说,凯泉,你创业时候还想面向世界呢,怎么走到北京就不走了?我说,咱们去沈阳拍个电视剧,把魏三给得(音“的”)瑟跑了,而且演员中途还有逃婚的,这不是劳民伤财么,我还赔了好几十万。可说是这么说,做还不能这么做,你就得让他出名,出名再走,走完再来,就是滚动式的。干这一行应该要有相当大的承受能力。”但即便如此,徐凯泉还是投入大笔资金在后备力量的培养上,他投资四平市的一所艺校,专门培养二人转后备人才。由于媒体对二人转的报道逐步升温,到徐凯泉这里要演员得越来越多,有的去了还能回来,有的就一去不返,所以这事让徐凯泉非常挠头,“都要演员,我只好招兵买马,现在东北这地方我都满足不了,别说北京了。最近赵本山要在长春打他的品牌,我的演员要是走了,他们不就趁虚而入了?竞争很激烈,轻易我的演员不能动,我啥时候把他打败了,我啥时候再说进京的事情。”
荤口与脏口的困扰
另外一点,徐凯泉总担心二人转被人误解,尤其是央视的那次“叫停事件”,更让他变得谨慎,“我以前专门主管娱乐场所的,二人转是这个市场当时最受歧视的、最受打击的。我当时就发誓必须要把它弄好。现在报纸、新闻里说我是二人转的领军人,那是现在我整好了,要是整坏了呢?”
记者在长春采访时发现,和平大戏院的演员在表演时,的确很注意,从头到尾没爆脏口,而其他剧场,虽然在门票背后印着“绿色二人转”字样,但是在表演时的确时常会出现一些脏口,长期以来,二人转的脏口问题的确成了它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困惑。二人转是流行于东北农村的民间艺术,长期以来,由于它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多段子都是不雅的,而它一旦从乡村进入城市,脏口问题就愈加显得有些麻烦。可是,二人转几百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就是不荤就没人看,那么徐凯泉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在和平大戏院的舞台对面,有一盏灯,平时不亮,这盏灯由值班经理控制,如果演员在表演时出了脏口,这盏灯就会不停地闪亮来提示演员,如果演员几次被提醒,就会有相应的处罚。除此之外,戏院领导和演员还经常在一起研究,一方面要适当保留二人转的荤口,另一方面还不能有脏口,这个尺度的确很难把握。徐凯泉告诉记者,他们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哪些词、哪些话不能说。
说到绿色二人转,徐凯泉说:“我认为二人转没有什么颜色,啥叫绿色、啥叫黄色?就是好看好玩,再有就是原汁原味民间二人转它必须要有这些荤口,你像省民间艺术团,那就是灭亡了。它曲调优美,服装漂亮,那么演它就失败了。它必须说说停停,跟观众去沟通。民间的东西就这样,你随便把它改了能行么?这是最关键问题。赵本山提倡的绿色二人转没有问题,净化舞台,这个我们家早就实施了。上台骂人、做下流动作我们都是不允许的。有些包袱的荤口怎么掌握尺度,含而不露,擦边球,这就需要演员动脑子琢磨,我们主要在这方面下工夫。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这个尺度很难掌握,文化管理部门也是很挠头。形势紧了,就抓,形势松了,演员就放开点,就这么回事。”
记者曾就二人转的脏口问题采访过现在东北最红的二人转艺人魏三,他说:“二人转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有争议才是对的,老艺术家对新型二人转不理解。头几年我的表演也有些庸俗的东西,不了解二人转的人以为它很俗,脏口不是艺术。现在中国缺乏讽刺性艺术,在舞台上表演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我的小品有时候就说得挺过的,但我觉得比较直白,它就是新型搞笑艺术。我演的傻子系列,就是因为聪明人都不说实话,只有傻子才说实话,我就想借这个讽刺一下社会问题。”
支柱与版权问题
现在和平大戏院的二人转到底火到什么程度?据记者在两家和平大戏院的剧场观察,演出从晚上7点半开始,到10点半结束,三个小时大约有四五对演员表演,如果去得稍晚一点,好座位基本上就没有了。门票基本上是10元到50元之间。演员基本上都是在赶场,有时候由于后一对演员还没有到场,前一对演员就不能下场。一对演员平均一年能演出1000场左右。观众什么样的人都有,年轻人和中年人居多,据戏院负责人介绍,外地人大概占一半左右。徐凯泉自豪地说:“我们家就是常年爆满,我不懂什么叫旺季和淡季,往年就是年三十休息一天。观众什么地方的都有,都是慕名而来,感觉就是看完了太开心了、高兴、解乏。我们家都形成品牌了,天天满员。”和平大戏院一共有三家分院,最初只有在商业街重庆路上的一家,后来一家装不下了,又开了第二家、第三家。回顾当年创业的情景,徐凯泉说:“从创业到今天,都是从零开始,点点滴滴,用自己的心去感染对方,一开始是4个人合开的,开始赔,后来合伙的人先后都撤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从当初一天挣几十块钱到现在几万块钱,我们是这么走过来的,后来人装不下了,又扩建了好几次,到后来还装不下,就开分剧场。”
艺术总监宫庆生曾经告诉记者:“二人转在长春已经成为社会最主要的文化现象和旅游项目,二人转之所以火是因为它没有更多的束缚和程式化,土生土长,随着观众的欣赏口味在变化。二人转非常贴近观众,还有专门的一批人深入民间,写了几十个剧本,创、编、导、演一条龙,以前二人转是写啥就演啥,现在倒过来了,观众喜欢啥就唱啥。”

赵本山用他的名气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二人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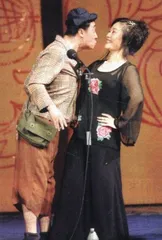
二人转有一个特点,演员表演的段子基本上都没有版权,尽管二人转演员比较多,但是表演的节目都差不多。这主要是有些演员自己创作出一个段子之后,很快就会被别人学去,别人在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加工修改,让它越来越符合观众的欣赏口味。对于一些笑料、包袱,你加一点我加一点,最后就出现了众多版本,虽然现在是一个版权意识很强的时代,但是对二人转来说,它还保留着传统的民间传播方式,那就是,每人都有权利去对一个作品进行二次加工,也正因如此,二人转才越来越活跃、丰富。拿目前在东北比较流行的二人转段子《擦皮鞋》来说,它最早是宫庆山创作的,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每个版本都不一样。甚至一个小品,每对演员表演也不尽相同。比如赵本山每年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很多是从和平大戏院的演员学的,和平大戏院的人很自豪:“赵本山今年说的那些,我们一年前就给说臭了。”徐凯泉就是这么一个人,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让二人转花样翻新。因为他只有这样,“我们家”才会越来越红火。
徐凯泉还告诉记者:“我家做饭的都能演戏,有好几个服务员现在都已经成熟了,我们服务员还联合给演员演过一次节目呢。”

“电视相声演员”大多表演新创作本子,这样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相声段子的“民间底色”
这一夜,谁来说相声
苗炜
多年前看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新奇于他用两个贬义词来描述戏剧,一个是僵化,一个是粗俗。他说的僵化是指英国剧团演出经典的莎士比亚,放到中国来说,很可能是人艺演出那种北京味道的戏,从《茶馆》到《天下第一楼》,演得炉火纯青,一点毛病没有。彼得·布鲁克还说粗俗是戏剧的一种生命力,这个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不知道咱们这里什么东西是粗俗的。
按照彼得·布鲁克对戏剧的定义: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进一个空的空间,这就是戏剧。那么,相声、评书、二人转等曲艺形式都可以算是戏剧,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把它们归到某个艺术门类中去,而是说,从某些相声和二人转的表演中,可以看到粗俗的力量。换一种说法,它们具有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两个月前,赵本山的弟子在全国电视小品比赛的颁奖晚会上演出的节目被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喊停,据说是因为作品的格调不够高。由此,二人转是否粗俗、该怎样改造又引起一番讨论。“小品叫停”这个场面倒让我想起一件旧事,据一位老相声艺人孙玉奎的回忆文章,1949年10月1日,有一家大工厂为了国庆,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有两个演员说了段《反正话》,但因为“格调低下”,这两个演员被轰下了台。随后,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四篇文章,说相声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政治作宣传。这样一来相声出现了危机,撂地的也没有人听了,剧场也不上座儿了。1950年1月,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孙玉奎、侯宝林等相声演员都曾拜会过老舍先生以探究相声的“改造问题”。1950年2月,老舍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谈相声的改造》,他认为“贯活”相声较易改造,比如《地理图》,可以参照原本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新民主主义的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然后把各国地名按这两系统介绍出来。再比如《报菜名》可以加入营养常识,如菠菜有什么维他命,豆腐有什么维他命,菠菜豆腐打倒山珍海味,提倡节约。
相声评论家张蕴和认为,相声改造形成了当代相声与传统相声的割裂。其实,我们能依稀看到另一种割裂,那就是李伯祥、马志明为代表的一帮天津相声演员与姜昆、冯巩等人为代表的“电视相声演员”之间的割裂。天津的相声演员也借助电视扩大他们的知名度,李伯祥也说过“我看红岩”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但他们是以传统相声获得认可的。“电视相声演员”大多表演新创作本子,这样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相声段子的“民间底色”。
相声演员李金斗认为,相声应该坚持在剧场演出,少上电视。台湾“相声瓦舍”的创始人冯翊纲先生也认为,相声是最适合“驻演”,同一套作品,在同一场地连续演出。冯翊纲先生说:“最初相声是非常俗的,历经时代变迁,越走越雅,越是追求相声的高雅,越是将它挤向牛角尖。”
“相声瓦舍”曾经表演过传统相声《黄鹤楼》、《大改行》等等,在《大改行》中,他们将另一个传统段子《卖包子》融入,把“周信芳卖包子”的段子改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小小的改动不免让人产生更大胆的想法,谁要是能把《连升三级》、《知县见抚台》这样的段子改在现在的官场里,那该是多有意思。冯翊纲说,相声的思想层面,基础定位于讽刺,无论褒贬,最后都将走入嘲讽。
辛辣的讽刺性的相声是很难在春节晚会或别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的,相声的历史有100多年,但走到今天却时刻要受到电视制约,这种“时空错乱”的病症是没法儿治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爱我家》这样的情景喜剧在很多地方借鉴了相声手法,而赖声川表演工作坊在台湾曾推出过数百集的《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个时事讽刺剧也是师法相声。
传统相声中的众多“臭活”已经消亡,即使在《传统相声全集》这样的书里面也找不到《怯嫖》、《怯寻宿》这些相声的文本。在赵本山演出的磁带里还能听到他讲顺口溜: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不到歌厅不知道自己老婆多老,但在电视晚会上,我们看到这个来自民间的艺术家越来越被糟糕的剧本和表演规范所限制。
如果赵本山一直在铁岭一带演出,那对全国许多观众来说少了个乐子,但是,另一方面,李伯清在四川好好用四川话说他的笑话不是很好吗?真的有必要以能不能上电视、能不能承载宣传目的为标尺吗?今年的春节晚会,我们看到小品这个形式正步相声后尘变得无趣,但只要四川的茶馆、东北的剧场里还能传出笑声,我们就能见证那种粗俗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