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以下是《喜剧之王》里的一段台词,当时尹天仇和飘飘一觉睡醒,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电话给洪爷:
尹天仇:喂,洪爷,现在外面夜总会的小姐过夜大概是什么价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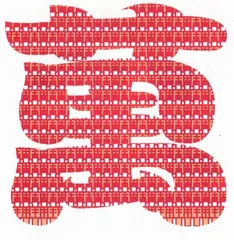
洪爷:普普通通的大概要1 000到1 200块吧。
天仇:如果素质好一点呢?洪爷:怎么个好法?天仇:我敢说是极品的素质。洪爷:100多万到1000多万不等了。根据我个人对香港各类夜总会的观感,与其说小姐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如说汉语对于数目字的表达实在是骇人地模糊。按照剧情,洪爷话音刚落,尹天仇手里的电话就掉在了地上,于是立刻着手筹资,所筹得现金、实物包括:一些钞票,若干毛票,一块手表,一个红包,再加一本简体字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接着躺到床上冲里装睡。飘飘见状,只收了钱和手表,然后穿好衣服推门而出。由此又可见,汉语对于数目字的表达不仅是骇人地模糊,甚至已骇人听闻地模糊到令人丧失了对于自我以及他人身份、价值的分析判断能力。
汉语历来就被视为一种缺乏“数学思维“的语言。这话也得看怎么说了。以我个人一贯比较公平的立场来看,准确地,汉语缺乏或故意缺乏的其实只是“小数”思维,相反,在“大数”思维上,至今仍然独步天下。除。一寸光阴一寸金”略显斤斤计较之外,像“飞流直下三千尺”以及“白发三千丈”还不够好玩,一定要玩到“万岁”、“万万岁”、“亩产万斤”甚至“100多万到1000多万不等”这等5位数(或以上)金句才算过瘾,才算有气势、有意境、有诚意。“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三言两语,从个位数直接跳到4位数,最后坚挺地挺立在“万”字之上,意犹未尽。凡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以上者,皆无人蠢到会去究竟这些数字的准确与否,否则,就真个要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到“缘愁是个长”了。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愁”字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想会是,一万年。
小学老师说,这些不尽可信的数字只是在用于文学表达时,才是美的,因为是美的,所以也是更可信的,更有说服力的。这个我信,而且直到今天仍信。而且,我想略作补充的是,当这些不尽可信的数字被用于文学以外的其他表达方式时,也是可信的。因为可信,所以也是更美的,更有说服力的—至少,我相信这些活动的策划者对这一点皆深信不疑。我觉得,他们的心中都有一股共同的美学冲动,就是非要把汉语中的那些修辞学上的数字统统变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非得把那些虚数一一坐实了不可,一洗汉语“不精确”的百年耻辱。比方说,“万人空巷”这个词在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指的其实都不是有一万个人离开了他们居住的巷子,但是,为了响应第15个全国爱牙日,深圳就组织了比“第15个”听起来数字更大并且更为如假包换的“万人齐刷牙”活动,1万名中小学生“万人空巷”地走上街头,同时正确刷牙3分钟。紧随其后,台北市也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万人活动”—这次不玩刷牙了,改玩跳舞。万名台北市民步调一致地在公园里载歌载舞。一刷一跳,两项前纪录的创造者一是美国,一是澳大利亚,都是大国。故这些纪录的被创造以及被打破都很容易理解,也算是靠山吃山,靠人吃人了。虽然搞的都是人海战术,然而其中仍有一个重大区别:美、澳的创纪录人数分别是3872人及6275人,破其纪录的中国人人数则同为1万。
以上只是无日无之的“万人活动”之万里挑二,看这阵势,全中国的“万人迷”们一旦下定了决心,很可能真的就做好了排除一万个困难的一万个计划。其实,“万人齐刷牙”本来想要表现的无非就是“有很多人一起刷牙”的意思。如果报导由李白来写,最多也就写成“万户捣牙声”这种。既然现在大家都倾向于相信那些修辞学上的数字应该都变成可数并且可信的,并且相信因为可信,所以也是更美的,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对“多”的美学做出重新审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过去我一直相信浦东的“东方明珠”是不美的,最近则已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如果有一万个东方明珠杵在那儿,它(它们)看上去就是美的,更有说服力。拉斯维加斯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多”从来就不是本意,它的美学核心在于表现了动作/行为以及理念的整体划一性,数量越多,越能表现,“万”大概碰巧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数字,我们大概也很难戒除对它的迷恋,因为按照苏珊·桑塔格的看法,对“多”以及“整体划一性”的迷恋,源自于人类的“内在的法西斯美学冲动”,而这种美学冲动又直接源自于性压抑,它“暗示了一种理想的情欲形式:性能量被转化为精神能量”。
量变引起质变。人人都把Less is more挂在嘴边上,其实赖死一死摸,摸一死赖死。话要说成这样,才是一句顶一了一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