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米歇尔·雅尔:我要在中国实现一个梦想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1981年,刚步入唱片界的法国音乐家让一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以中法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来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两场音乐会。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流行音乐。22年后,雅尔再次来到中国,他看到的是很多中国音乐家像他当年一样在做电子音乐。雅尔是一个在电子音乐界非常与众不同的音乐家,他把电子音乐的通俗与抽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听众带来最大限度的感官享受,曾经创造了一场音乐会250万观众的世界纪录。这次,雅尔为明年在中国举办音乐再次来到中国,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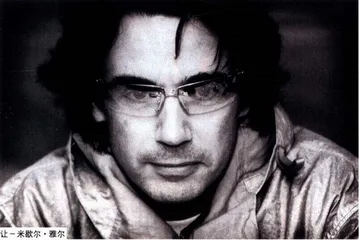
让一米歇尔·雅尔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选择电子音乐?
雅尔:我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在接触电子乐之前我也搞过一些摇滚乐队,同时在那个时期我也在学习绘画,当时电子乐研究中心在巴黎,我在这个中心第一次接触到电子乐时就兴奋得不能自己,我觉得这种音乐可以像绘画混合颜色一样,也有点像厨艺,我可以把在绘画和厨艺方面的创意通过混合音频来实现,当时我就认为电子乐将来可以成为一种创作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古典音乐对你后来的电子乐创作有哪些帮助?你的音乐和当时的Kraftwerk、Tangerine Dream这样的音乐有什么不同?
雅尔:从音乐结构方面来说,电子乐还是来自古典音乐这一面。我的音乐和Kraftwerk、Tangerine Dream最大区别在于这两支乐队在我眼里像机器狂人,他们的创作理念是尽量让机器搞创作,而人的因素尽量少。我正好相反,就像画画不该停留在刷子上一样,应该尽量发挥作曲家作曲的这一部分,《氧气》在很多听众看来都不认为是电子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了你1 976年录制的第一张唱片《氧气》,我非常喜欢这张唱片,我想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创作这张唱片的?
雅尔:对我来说,《氧气》是具某种跨时代意义的唱片,我一点没有觉得《氧气》带有任何时髦色彩,虽然后来的专辑有了一些进化,但《氧气》中的概念还是比较独特的。当时创作这张专辑时,就希望能够创作一张跨越古典音乐和电子乐,不太强调科技尖端色彩的专辑,而且和摇滚乐不同,不那么直接来自于体能和物质,而是来自于流动的、从地上到空间的这种感觉的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1 997年,你又出版了《氧气》(7—13),和20年前的《氧气》感觉上不一样,在后来的这张专辑里,你的概念又有了哪些变化?
雅尔:最早的那张《氧气》本来就希望是一张很长的专辑,1997年的这张又回到了当初那张的故事线上,希望能通过数字化的设备延续当初那张专辑。第一张《氧气》当中也有一些环保的主题,但停留在人对自然的破坏和人对自然的污染上。第二张《氧气》试图探讨污染是发自于人的本身,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信息、影像、声音对人也是一种污染,我试图探讨这方面的环保问题。坦白地讲,现在再回头看,我不能确定第二张专辑的想法是不是个好主意。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电子音乐已经变得很时髦了,跟70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现在也有很多音乐家在尝试着做这样的音乐,你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前辈,对中国从事电子乐创作的人有哪些忠告?
雅尔:我第一次来中国给中央音乐学院一个电子合成器,并给他们做了演示,4个月后我回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已经在这个合成器的基础上制造出第一批合成器了,并且音乐学院开设了合成器班。这次我来中国,再次去那里访问,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教学楼,很多学生给我演示了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很自豪。在电子音乐系学生给我演示的作品中,我发现很多作品对我来说都足够抽象。作为忠告,就是不要复制,尽量在自己的文化本源和个人根源中发掘自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