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眼中的“生财有道”
作者:程磊(文 / 程磊)
“我为什么不愿意给中国开药方?”
—专访约翰·凯教授
记者:您对北京印象如何?
约翰·凯:北京的交通堵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的立交桥有126座,路很多,现在基本上能和洛杉矶相比。
记者:您的另一重身份是社会学家,在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很多英国学者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最好不要保留那么多国营企业,中国现在对129家国有企业的保护,是否是良性的?
约翰·凯:我已经决定不再为中国问题开药方了,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想说在管理国营企业的问题上有许多事情需要注意。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在建立自己的商业活动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私营企业,要过多考虑跟政府的关系,而不像私营公司,只需要考虑跟客户的利益。
记者:每个国家政府的政策效果都不一样,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您倡导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角色,怎样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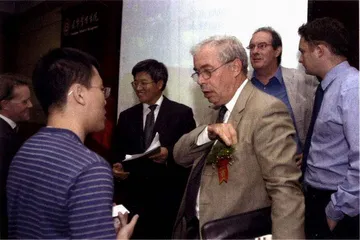
中外学者的生财有“道”研讨会(本刊资料)
约翰·凯:传统的美国模式包括必须要保证你获得产权,必须要强化合同。但是我认为,政府要发挥的作用大大超过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例如怎样把自己的产权搞得更安全,其中还包括公司运作的稳定性、公司管理的透明性问题。对于私人公司也是如此。
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绝对不能为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决策,应该给予他们更多自由。比如一个公司怎样发展才能获得成功,应该朝什么领域扩大才能获得成功等等。这就回到我早些时候说的话,我们认为有序的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大家都不知道市场经济的问题应该怎样回答,只有通过不断小规模做试验,通过我们犯错误,积累教训和经验继续往前走。
记者: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经历了民营化浪潮,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约翰·凯:英国民营化浪潮的历史有20年了,可能强调的领域和现在所强调的不一样。英国的国营企业不像中国国营企业有很多综合性的社会责任要承担,包括给工人提供的很多社会责任。通过私有化、民营化浪潮,一些私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数量降低了,这是一件好事。另外,公司的工资结构有所变化,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工资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国营企业要承担很多技术培训,成功的私营企业没有这样的工作。总之,英国民营化浪潮的结果有好有坏,比如公用事业公司的经营还是不如私营公司成功,结果好坏参半。
记者:您有没有对潜规则做过研究?我们说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公司,可是如果碰到潜规则怎么办?
约翰·凯: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确实很不容易,解决潜规则很不容易。在英国和美国,由于这两个国家文化问题,对潜规则充满敌意。因为你把人际关系运作到商业运营中,或者运用到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很不道德。有一些商业成功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意大利,意大利非常注重家庭关系,跟中国一样,他们认为家庭是非常受人尊重的经济单元。在这个国家中,个人的关系网在商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运作的模式多种多样,有些模式之所以运作成功原因非常复杂的,潜规则也是可以允许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到中国来给讲课、开药方的原因。
“中国公司更适合走欧洲路线”
—专访威尔·赫顿先生
记者:现在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国内,公司丑闻不断,您认为这种丑闻是文化上的还是制度上的原因造成的?
威尔·赫顿:一百个人中总有一两个人做坏事,对公司也是一样,一百家公司也总有一两家爆出丑闻。令人担心的是,丑闻的数量、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已经不是一种偶然。所以像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期间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很多公司迫于华尔街对它的压力,也就是说华尔街要求公司有很高的利润,这个利润率上升的幅度非常高,而且是不合理的高。比如如果美国年均的GDP应该是3%,生产增长率也是3%,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利润应该是6%,而它的利润结果是要求高达12%。公司勉为其难,只有采取一种欺骗的手段或者欺诈的手段达到目的。
我想中国应该做三件事情,能够尽量减少公司欺诈行为的发生。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建议,中国股市应该遵循欧洲股市的模式,尽量受欧洲股市影响;第二个建议,应该建立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公司治理系统,尤其是公司治理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来自工会、金融机构和一些其他利益相关者,独立性地进行监督和管理;第三个建议,我想是最难做到的一点,有关信息披露和高水准审计,中国现在的审计公司以及中国相关的金融财务方面的信息披露,有人认为或者据我所了解都是比较原始的,应该在这方面做很多改进。
记者:中国的许多公司都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前曾经有过模仿欧洲的职工持股会,后来也引入美国的非独立董事,请您给中国的公司提一些建议。
威尔·赫顿:我认为中国现在可以有两个基本选择,一是在公司治理方面选择欧洲模式,如果真的选择欧洲模式,要想成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一个独立的工会,进一步发展比如养老金、金融机构、银行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加在一起起到监管委员会的作用,来代表所有股东长期的利益。我想强调的是,这里的工会是独立的工会,他们应该向监管委员会派独立代表,这是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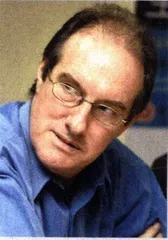
威尔·赫顿(Will Hutton)
2000年,威尔·赫顿加入产业协会(TheIndustrial Society),也就是现在的做工基金会(The WorkFoundation)任首席执行官。威尔刚开始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及投资分析师,后来到电视及广播部门工作。就在加入产业协会之前,威尔担任《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主编以及《卫报》(TheGuardian National Newspapers)主任。现在,威尔还在继续为《观察家报》写每周专栏,继续在《卫报》担任董事职务。此外,他还是伦敦国际戏剧节(London Intemational Festivalof Theatre)主席,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LAMDA)主席,设计协会(Design Council)千年委员会(Millennium Commission)委员等。

约翰·凯(John Kay)
约翰·凯是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产业结构变革以及企业个体竞争优势分析中经济学的应用,同时包括企业战略及公共政策。他是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ofFiscal Studies)的创始人,任主任,该研究所是英国最富盛名的智库之一。之后,他当了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以及牛津大学教授。又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首任院长。1986年,他创办了名为伦敦经济公司(Londan Economics)的咨询公司,任公司执行主席直至1996年。在此期间,该公司成长为英国最大的经济咨询公司,约翰·凯也是至今为止惟一一位获得英国学院(BritishAcademy)院士这一学术荣誉的管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