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司法进程的事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1987年:包老头告官案
事件:1987年,浙江温州苍南县县城灵溪镇老人包郑照因在河滩建造了三间三层楼房与当地县政府发生争执,苍南县调动70余位武警及县区镇干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了封锁,采用爆破手段连续爆炸17次,对包郑照的房屋实施了强行拆除。当年年底,包老头状告县长黄德余。成为中国第一起“民告官”案。此案经温州市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包郑照最终败诉。
影响:从包老头告官开始的12年中,光温州就共发生各类民告官案件5000多起,绝大多数问题主要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行政部门加重农民税收负担和不合理地征用土地。在民告官无法可依的窘况下,两年后《行政诉讼法》被催生。迄今为止,行政诉讼案件约有66万起,在农村接近50%,而原告胜诉的比率在40%以上。“包郑照案”后,国外有的杂志撰文称:“农民可以告县长,中国法制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988年:沈阳“9·21”扣押邮件风波
事件:1988年9月21日零时,沈铁公安分局接到举报,称沈阳火车站的搬运工人在卸货时发现邮袋中有香烟。公安当天组织60余人对邮件实施突击大检查,连续20多个小时,开拆了860多个邮袋。沈阳邮政局接到通知后,质疑沈铁公安分局行为,认为扣押邮件行为是违法的,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通信自由权利,也违反了刑诉法中有关扣押邮件的规定。双方各执一辞,沈阳市副市长任殿喜出面调停无效,此事迅速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公共舆论和司法界的焦点所在。
影响:司法究竟应重实体,重程序?还是二者并重?关于人与法、权利与权力博弈的思考,到90年代初开始、90年代中形成高潮的审判方式改革大讨论及立法变革、司法实践,都是沈阳“9·21”扣押邮件事件大讨论的延续。这场发生于80年代末的沈阳“9·21”扣押邮件事件及引发的争论,成为建国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司法观念转型问题的重大事件。
1995年:刘秋海事件
事件:被救者陈小俐与救人者刘秋海之间多达七八种诉讼关系的对簿公堂成为“刘秋海事件”被广泛注意的关键。1995年3月12日晚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人陈小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经过北海北郊时被撞伤,随后,时任雷州市政协委员的刘秋海、冯昌炳等人路见,将陈小俐送往北海市人民医院,并留下600元医疗费后驾车离去。陈小俐出院后与其亲戚廖文斌将刘秋海以“交通肇事逃逸罪”告上法庭,因为此事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最终刘秋海败诉。事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著名律师田文昌、著名律师韩效忠、交通事故专家王欣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诉讼法研究室主任杨忠民等法学界人士专门为此案举行了“法学论证会”。
影响:以口供为中心构成的证据链能否成为断案的关键?法院审理在一个以公安交警部门为被告的案件时,他们能否超越某种当事人的影响或者当地权力的影响,来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刘秋海事件”让事实性证据的重要性和司法独立性被司法界所重视,一年后“交通肇事罪”判定中,司法鉴定和“物证”被要求作为必不可少的证物出示。
1997年:张金柱醉酒驾车伤人案

事件:1997年8月24日晚9点多,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的张金柱驾驶一辆白色“佳美”轿车撞死了苏家父子苏东海和苏磊,逃逸中将伤者拖出1500米。这桩沸沸扬扬的公案最后以张金柱被枪决而大快人心地告一段落。几乎是民意和舆论将张金柱推上了断头台,张给中国司法史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是被记者杀死的。”
影响:在“诛杀公案败类”的强烈声讨下,张金柱到底是在醉酒状态下伤人还是故意伤害的事实变得不再重要,“司法仍如此轻易地被人左右”成为张案后司法界人士反思的主题。1997年,也是中国法律史上立满里程碑的年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法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法治”所替代。而张金柱案件的另一个作用是开启了1998年后舆论对警务人员恶性犯罪的一系列曝光。
1998年:杜培武冤案
事件: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轻伤。在刑侦队里杜培武终因难以忍受折磨,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1999年2月5日,根据警方的侦查结果和检察院的指控,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直到第二年一个特大杀人盗车团伙的破获才找到真凶,让此案拨云见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影响:新《刑法》已经确定了“疑罪从无”的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在履行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是杜培武案的真正元凶。此案也让“刑讯逼供”问题浮出水面,为有效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案件所在地云南省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提高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的意见》,提出了10项措施,是公安系统对于自身执法程序的首次反思。
1999年:綦江虹桥垮塌事故

原中共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对綦江虹桥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件:1999年1月4日18时50分,一座刚刚架设的新桥虹桥突然整体垮塌,造成死亡40人(其中武警战士18人),轻重伤14人,直接经济损失628.22万元,这就是“綦江虹桥垮塌案”。三天之后,事故调查组查明,垮塌事件属于重大工程安全事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这起事故中涉嫌职务犯罪的问题依法进行调查,对林世元、张基碧、孙立、赵祥忠、贺际慎立案侦查,并以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媒体迅速介入此事报道后,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庭审直播”。
影响:作为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参量之一,公开审判因此事被重视。此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以确保实现司法公正。另外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的最终审判引发了刑法学界对于受贿罪量刑的讨论,有专家认为,受贿罪应当独立确定量刑标准,而不应比照贪污罪量刑,因为贪污罪所侵犯的,是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刑法学上所说的“数额犯”,而受贿罪的后果,却难以仅仅凭数额判断,受贿的人,常常要为行贿的人牟取非法利益,由此给社会造成受贿财产以外的、更大的财产甚至生命损害,特别在建筑工程和其他重大权力部门。所以,受贿罪的处罚,除了应看受贿数额,还要看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有多大,综合量刑。
1999年:惊动高层的“三盲院长”
事件:41岁的山西绛县法院副院长姚晓红原是绛县供销社一名固定工,后来调到法院开车,以工代干当上了法院办公室主任,1995年当上了绛县法院副院长。被称为“三盲”院长(文盲,小学没毕业,却有大专文凭;法盲,不懂法也从不学法;流氓,对群众发淫威)的姚晓红在绛县法院组织了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短短几年非法拘禁群众300多人,法院的树上、水泥柱上、楼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捆绑、背铐、悬吊并惨遭毒打折磨的群众。姚自己成立了一个“经济审判二庭”,这个“经二庭”自成立之日起直至姚案事发,没有立过一次案,也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审过一次案,它的作用就是以暴力殴打或非法拘禁方式为姚“追款敛财”。1999年9月,山西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姚晓红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以贪污罪、非法拘禁罪对其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
影响:“三盲院长案”震惊高层,直接引起了一轮对掌握司法审判权的法官素质的全面整顿,一年后,《法官法》修改,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加强法官素质的考核。这是司法界对执法主体公正和主体素质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思。
1999年:“学位诉讼案”
事件: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北大认为赞成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1999年9月24日刘燕文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大推上被告席。这一中国首例“学位诉讼案”一审北大败诉,二审刘败诉。
影响:在教育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此案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司法进入大学意味着任何公民在权益受损时有了司法救济途径,这是一个成熟法治国家的表现。当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穷尽了所有的途径,再不给他一个司法救济的途径,非要等着条文的变更,这是不公正的。此案的受理开辟了一个途径:在法律无明文禁止时,我们都可对法律的精神作一个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理解,对法律的本意做一个最大合理的宽泛的理解,并授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实现司法救济,扩大司法救济途径。
2001年:乔占祥状告“铁老大”

乔占祥
事件:2001年1月17日,从石家庄赶往河北磁县的乔占祥,以17元的价格买到了一张火车票。“比平时多了5元钱,”这位供职于石家庄三和时代律师所的律师说,“22日我从石市赶往邯郸时,票价同样高出平日4元。”一个月后,乔占祥向主管部门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对该部发布的《关于200 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提出异议。该《通知》称:2001年春节前10天及春节后23天,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等始发的部分直通列车实行票价上浮20%至30%。当年3月19日,铁道部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票价上浮通知》。于是,乔占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乔占祥成为中国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质疑春运涨价的公民。
影响:形同于无的“听证制度”作为引入行政行为中的一种司法手段开始深入人心,随后一些国家部门纷纷举办“听证会”,让“依法行政”的原则得以体现。
2001年:麻旦旦“处女卖淫案”

卖淫嫖娼不适用当场处罚
事件:陕西咸阳市泾阳县一民警和派出所聘用的司机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出示证件就到一居民家中将19岁少女麻旦旦带到派出所轮流单独讯问一整夜,其间将麻吊绑在屋外的篮球杆上,扇耳光,辱骂麻“卖淫的”。凌晨4时许,派出所所长彭亮将麻带到办公室,关上门“做思想工作”长达30分钟。最后,麻旦旦被迫在“招供材料”上签了字。派出所认定该少女“卖淫”并做出对麻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裁定。此后,麻旦旦将泾阳县、咸阳市两级公安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审判结果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公安机关赔偿麻旦旦的74.66元钱是麻被非法传唤23小时的直接损失。
影响: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在保护谁?此案的深刻在于它揭示了公权存在的价值问题。政府权力和公民的权利是不是应该平等?如果平等,国家赔偿法必须是针对保护弱者而不应是袒护享有政府权力的行政主体。在行政司法领域,法官很难有作为的司法现实让此案成为讨论现行《国家赔偿法》修改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3年:杨志杰案

杨志杰(右)
事件:1991年2月9日凌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牛民好家发生爆炸。牛家4岁的儿子被炸死,牛民好和妻子、女儿受伤,其中牛妻重伤致残。因为同村村民杨志杰的岳父与牛民好的姐夫十几年前有过纠纷,杨志杰的内弟又因琐事与牛民好发生过矛盾,所以1991年3月4日,时年34岁的杨志杰因涉嫌作案被收容审查。随后吕富荣和其弟弟也被收容审查。吕富荣被吊打13个日夜,只是让她承认爆炸那天晚上,杨志杰出去过。从此,杨志杰被一关12年,在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被超期羁押7年后才被起诉,进入审判程序后又被关押了5年之久。2003年6月,杨志杰被释放回家,但仍被有关方面密切监视起来。
影响:杨案集中体现了司法执行中的制度缺陷:没有司法审查机制,公安机关得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做什么和怎样做,缺乏监督,而检察院对该案根本无法插手,法院更是对案件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对公民权益进行保护,执法者往往能够恶意利用法律规定将超期羁押变为普遍的现实。杨案成为清理超期羁押的开始。
缩小公安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访公安部法制局局长李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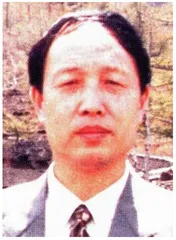
李忠信
记者 金焱
三联生活周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看起来只是公安机关对内的一个约束性文件,但它的发布却引起极大反响,新浪网上两天内网友的评论就有80多页,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广泛的关注率?
李忠信:这次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不是一个内部文件,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公安机关不是简单的办案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向法治迈进,尤其在提到人权的司法保证方面,公安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些都与老百姓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比较引人关注的几个条目包括对卖淫嫖娼的有关规定、对非法证据获取问题的规定等条目,也有人将这个规定的出台与前不久的刘涌案相联系,这个规定出台的真实背景是否有刘涌等个案的因素?
李忠信: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以前办理行政案件不是没有程序,而是散见于其他文件,现在有些条文我们进行了细化,有些进行了新的补充,比如你刚才说的非法证据的问题。但是刘涌案是近期的事情,而我们围绕这个规定的出台已经做了四五年的工作,它的大背景是,我们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调查取证程序不规范,我们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工作还有一定距离。公安部门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公安的职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去“抓人”,现在这一点在淡化?
李忠信:警察或者确切地说“公安”的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侦查,一个是进行行政治安管理,后者包括户口的管理,复杂场所的治安,交通的管理等等,这个量比我们要处理的刑事案件的量要大得多。我给你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这个比例远远超过3∶1,像当场处罚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所以执法为民是一个首要问题,它在体现政府的管理职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立法意愿如何实现呢?
李忠信:立法意愿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它与实际具体操作还有一定的距离。其实程序规定是一个比较难操作的东西,无论你规定得怎样细致也是会有弹性的。依我看来,到明年也就是2004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后,老百姓会注意到我们公安机关充分讲理了。不过它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还要一段时间,可能要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公安机关的一系列自我约束行为中不是起点,这种变化还有哪些体现?
李忠信:对于行政案件我们有两道把关:一是不出公安机关的行政复议;一是行政诉讼,也就是民告官。这两年我们行政诉讼的维持率由十几年前的50%提高到现在的60%。维持率也就是等于完全支持公安的决定。另两个衡量标准是变更率也就是部分否定和撤销率,就是全部否定。你不要小看这10个百分点的纯增长,我们公安队伍比较庞大,不包括司法的狱警等有160多万的警察,在一线执法的就有100多万警察。全国这么多警察在一线执法,这10个百分点的增长就是不小的成绩。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待前不久出台的30条便民利民措施和这次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区别和联系?
李忠信:30条便民利民措施是公安机关从审批的角度中退出来,是一个点;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行政管理模式的改变,是一个面,而且它是有法律义务相伴随的。但是这二者的核心都是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我们是让老百姓错也错个明白,申辩也申辩个明白。
三联生活周刊: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会不会有一些现实的压力存在呢?如何衡量方方面面的不同利益?
李忠信:我们基层的一些干警是有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么严,老百姓愈来愈不好惹了,案子办起来费时费力。程序严了办事就麻烦了,但是执法就是要严,不这样,执法人员的素质就不可能提高,公民的切身利益也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提高。我们注意到,老百姓看到公安机关态度冷横硬,实际上老百姓不满意的不只是态度,关键是执法的不公。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中国公安机关的权力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应职能部门的权力要大很多,这一规定会起多大的限制作用呢?
李忠信:我们先后出台过《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机关行政复议程序规定》,加上这次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这三大处理行政案件的程序构成我们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希望到2005年能初步建立公安的法规体系,这是国家大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重实体轻程序,公安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着素质不高、执法水平不高,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这次之所以不是内部文件,要向社会公开,就是要探究警察权力的底线,使“警察说打就打,说罚就罚”没有发挥空间。或者说我们想以此限制警察随意执法的空间,尽量不给他们留这个空间,为保障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提供一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