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国是一个事实
作者:李鸿谷(文 / 李鸿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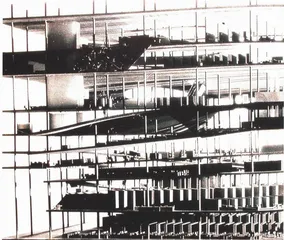
1992年,库哈斯为朱西厄大学设计的图书馆
这是一个脚柄可以活动的眼镜,左右两个脚柄不规则地交叉着,仿佛等待它的主人来继续把玩。在记者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身高1.9米的库哈斯很安静地坐着,他选择的不是交谈而是倾吐,翻译需要迅速记下他的要点,才可以将他长长的句子与段落翻译出来。中断他长段落叙述的,比较戏剧——“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库哈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手势暗示我们,他必须打这个电话。
选择中国,对于库哈斯“是一个事实”,“我们这个事务所120人,有80个在为中国的项目工作”。
中标CCTV新大楼项目后,库哈斯及其大都会建筑师事务所(OMA)又参加了北京CBD核心区的竞标。眼下正全力准备的,是获得资格以参加奥林匹克会展中心项目竞争。北京CBD核心区的竞标,在接受采访及随后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时,库哈斯都坦陈,“它被拒绝了,这在我们意料之中”。库哈斯为这一项目所做的方案,没有进入评审委员会确定的三个待选方案。
与CCTV大体量的建筑相比,至少让记者吃惊的事实是,CBD核心区的方案显示了另一种极端:地面最高的建筑仅两层楼。这一幢幢类似中国四合院的建筑群,实际是六层高的低楼,即使这样,六层中的四层在地平面下——不是地下室,是掏空的地面,使地平面下的四层楼,也能被阳光照射。“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太过超前。”这一方案的参与者,OMA的建筑师刘密说,“正因为太过超前,在做方案时,我们大多数都认为它不太可能被选择。”
库哈斯并非不知道建筑师们的疑虑,“他坚持要这个方案”。中标的CCTV与被拒绝的CBD方案,在库哈斯的同一张幻灯片里,承载的是他对摩天大楼的反思与结论:解决各自独立的摩天大楼群的平庸模式,在把它们(各自独立的摩天大楼)变成超级大楼与更加分散网络化建筑之间,有无数种选择。简单地看,对应库哈斯建筑思想的两个作品,CCTV新大楼是超级大楼,而CBD是更加分散网络化的建筑——“他把这两极,都做到了极端”。
作为建筑师,库哈斯对摩天大楼的设计,大约在十多年前,“他为曼谷设计了一个高达1公里(1000米)的超级大楼(hyperbuilding)。”OMA的一位建筑师告诉记者,“当然,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施。”正因为没有实施,库哈斯这一因为高度(是全世界最高高楼二倍的高度)而惊世骇俗的建筑,没有引人注目。稍后一些时间,库哈斯为韩国人设计的摩天大楼,“采用了捆绑高楼的方式”,如三角架一样,几幢高楼被捆绑在一起。这一方案后来也没有实施。“韩国方案中的‘倾斜’作为一种元素,进入了CCTV新大楼方案,开始的央视大楼电梯有5~6度角的倾斜,后来因为成本过于昂贵被放弃。”
“我很幸运,在哈佛有一个教席,不带课却可以带学生研究。”库哈斯向记者解释说,“从1996年开始,我的城市研究就已转向中国。”对珠三角一带城市的研究,库哈斯结集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概括我对中国的观察”——《大跃进》。目前库哈斯领导的哈佛研究小组,重点研究的目标是上海与北京。“北京是我发现的最后一座城市,它比我了解的南方中国城市更有序、更令人惊奇。”库哈斯说。
哈佛博士赵亮和他的来自四个国家的五位哈佛同学,正在进行的是北京保护的项目研究。“与其他建筑师不同,库哈斯的工作从研究城市开始。”20多年前,库哈斯对纽约的研究,“我跟他讨论过,老库说很难简单地概括《疯癫纽约》。在这本书里,他有赞美,也有感叹,当然还有讥讽与嘲笑。总体而言,库哈斯对摩天大楼所象征的进步,是肯定的。相信曼哈顿林立的高楼,也给了他足够的震撼。”赵亮分析库哈斯的纽约与北京,“纽约曾经所具备的活力,库哈斯在现在的北京、中国找到了”。
没有中标CCTV新大楼之前,OMA的几位建筑师告诉记者,“库哈斯的事务所好几次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即使如此,中国之于库哈斯,未必只是商机,CBD核心区竞争失败是一个证明,“他只坚持他认为最好的方案”。接受采访的OMA建筑师印象最深刻的库哈斯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建筑方案选择上,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也问他的建筑师。”赵亮以旁观者的观察是,“以库哈斯所拥有的地位,去迁就一个项目的成败,是一种资源浪费。”
库哈斯本人给出的答案,则含蓄得多,“我不喜欢大师这个称呼。同样,也不是大师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准确地说,中国更有空间让建筑师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南方城市研究的一本著作《大跃进》,从这本书看,您对中国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为什么直到CCTV新大楼,才以建筑师而非研究者的身份进入中国?
库哈斯:我在接到CCTV 新大楼设计邀请的同时,还接到美国世贸重建方案设计的邀请,当然这两个项目都是竞争性的。我后来选择了CCTV 新大楼的设计,这是因为两个项目差不多同时,都参加,精力上顾不过来。另外,“9·11”后,美国对自身越来越重视,这种内敛是普遍的心态,而中国却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CCTV,它是前瞻性的,这两者正好相反。对建筑师来说,选择CCTV显然更具挑战性。
三联生活周刊:对中国南方城市的研究,在什么方面帮助了您最终入选CCTV这个项目?
库哈斯:很幸运,我在哈佛的教席使我与其他建筑师有所不同,我可以有自己的日程,可以从研究城市开始我的工作。而过去对南方中国城市的研究,当然让我对中国的城市有了超过一般建筑师的理解。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越来越强大,在不断证明自己有能力重新安排社会生活、安排各种资源与安排各种活动,如奥运会——中国到了重新‘发明自己’的时刻。噢!当然,发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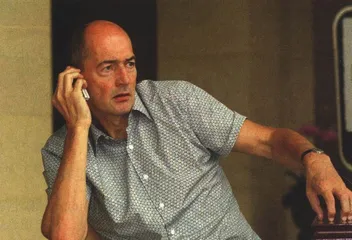
库哈斯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采访的一些中国建筑师,他们都提到过您早期的著作《疯癫纽约》,如果比较一下纽约与北京,您会给出什么答案?
库哈斯:北京是我发现的最后一座城市,我现在正带领我的哈佛学生做北京保护方面的研究,期待从这里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我们可以从一个建筑师的经历,简单地来比较(纽约与北京)。我们曾介入过纽约WHITNEY博物馆扩建工程,客户是董事会,由捐资人组成,能够进入董事会的,差不多70~80岁,而他们的身份又经常由股市升降来重新定义,因此制约建筑的机制很多,这个扩建计划后来就取消了。1880年开始,纽约的建筑就没有公共资本介入,这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同时,西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接近饱和,没有太多的空间。中国不一样,中国建筑师4年所建的房子,可能相当他的西方同行25年工作的总和。在CCTV这个项目中,我没有见到45岁以上的决策者,而且他们处理问题相对灵活,所以在中国更容易实现建筑师的理想。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起来更具前瞻性的CCTV新大楼,特殊性在哪里?
库哈斯:如果把CCTV看作一个媒体公司,同样的媒体公司,在国外可能由三处建筑构成。比如它的录播制作的技术部分可能在郊外,而行政与新闻采访部分则可能分别在城市的边缘与闹市区,这里面混合了各部分的功能以及不同功能所需建筑的经济计算。城里与郊外,地价显然是不同的。只有CCTV可以把这不同功能的各部分全部放在一起,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幢大楼里。这对建筑师而言,首先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行政、采编、录播等系统串联起来。我们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环,这个环将各个功能串联起来,一方面是媒体机构自身的;同时,也是参观者的。这个公共环的存在,表明CCTV的公共性,既存在于大楼,也存在于环境。意味着CCTV没有外墙,全部开放。
三联生活周刊:我是在看到您的CCTV 新大楼功能图示后,才发现您对媒体公司功能串联的重视。但是,在中国更多的讨论集中于您的这个建筑形象上,有将它形容为窗的,并且解释说其含义是:中国人通过这扇窗看世界,世界也通过这扇窗看中国;也有将它形容为大门的。总之,比喻很多。也许让建筑师解释自己的建筑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但我还是有好奇心,您自己如何解释您的建筑的形象?
库哈斯:对于建筑而言,它希望能够给别人以想象,而且想象越多越证明建筑师的成功,但我不想给出我的答案,暗示性的答案也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您描述的亚洲,“过去30年将高楼作为成长中新经济力量的象征”,很多人也由此来分析您的作品最鲜明地展示了财富与权力,是这样吗?
库哈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图纸,能够讨论的问题是形象。如果多一点耐心,等这幢大楼建成之后再来讨论,或许价值更大。我之所以放弃世贸而选择CCTV,是觉得这幢建筑有回应性的可能,也即世界对中国人雄心的印象,这幢楼可以回应其想象。当然,如此一来,也可能带来另一种看法,不少人将CCTV新大楼看作是一个纪念碑。而从设计者个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建筑的公共性——其对CCTV活动及其组织的展示,是更重要的。这幢楼到底是设计者用其对CCTV表示一份敬礼,还是用其来展示CCTV,我努力的是后面这一点,建成之后,相信大家会给出一个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疯癫纽约》里写道,“新建筑不再对某一种城市风格抱有审美义务”,在以故宫为建筑形象的北京,您的建筑作品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它无须“抱有审美义务”?
库哈斯:我们没有忽视故宫,也没有忽视这些传统建筑。但我相信,和谐是一种共存,对比也是一种共存;相似与对立,都是共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