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5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安琪拉 莫幼群 王怜花 曹红蓓)
歌之舞之
安琪拉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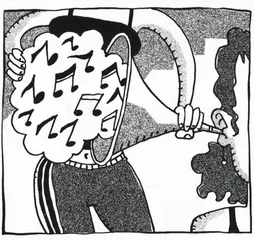
闲极无聊,脑袋就会蹦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未来的健身院是什么样子的。我猜想必然是寂静无声,大家团坐其中打禅、冥想,身上披的大概也类似《黑客帝国》的修士服,没有汗水模糊的面容,没有震天响的伴舞音乐,更没有五颜六色的健身服。
这种健身院可能已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静静地为某些尊贵客人服务,我等平民还得一复一日地赶集,上那吵闹无比的健身院。一个星期的有氧舞蹈班,老师天天不同,于是我们就有了惊吓度不一的体验。刚一开始,健身院还像模像样地把各个老师的履历贴在公告栏,有内蒙古的、江西的、湖南的,不一而足,但别指望在马头琴、花鼓声里优雅地起舞。有氧舞蹈千篇一律是用西洋或港台地区的强劲流行音乐,有次在放松运动时突然响起《梁祝》,一时间舞蹈室里整齐的晃手甩腿,像煞无数只殉情后飞舞坟头的蝴蝶。最可恨的是有一两个老师特别喜欢加插Chacha,长度虽是两三分钟,但只要音乐一起,久疏舞场的娘儿们立刻撅起屁股,腰身随之挺直,当年的妩媚与娇柔顿时满布脸上,旁边的女孩不知先出左脚还是右脚,笨拙得让她们心里暗暗发笑: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有氧舞蹈的伴舞音乐时时换,反正什么流行就拿来,版权费肯定是不用给的。《Lemontree》流行的时候,英文版、国语版、粤语版轮流播,耳朵听出茧子,腿也差不多跳断。有次,替班老师上来就是张国荣的《暴风一族》,“拳头无聊/怒撞晚空/如象灰色铁链撞裂街中的风”,让张迷的我听得心花怒放,“I can breakaway”配上踢腿的动作,我简直觉得自己比杨紫琼还厉害。一首接一首都是张国荣的金曲,一个小时的有氧舞蹈最后在《风继续吹》中缓缓结束。“人歌合一”的舒爽劲兴奋没几天,这个替班老师就给一大帮半老徐娘给轰走了,她们的Chacha估计像是Madonna穿Manolo Blahniks,只有性可与此相比。
无论换了多少首歌,我在健身院里一次也没听过Oliver Newton John的《Let's getphysical》,倒是墙上贴了几张宣传画,里面的洋模特竟然穿着紧绷绷的粉红色健身衣,把各种性征无限放大。上世纪80年代张扬健美身材的遗物,对比时下崇尚宽松、男女兼宜的衣着潮流,活脱一幅春宫图。
青木瓜与现代派
莫幼群
《青木瓜的滋味》说的是一个丫鬟赶走少爷的女朋友的故事。如果让张艺谋来导,说不定又会挂上欲火中烧的大红灯笼,可人家挂的是青翠欲滴的木瓜,还从头至尾配上了各类夏虫的呢喃,也算另一种活色生香。《青木瓜的滋味》最让我着迷的地方,是片中出现了大量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悄然退场的老物件,像蚊帐、蛐蛐笼、锅台等等。今年春天我去了趟越南,大概就是为了找一点“青灯有味似儿时”的感觉。
在越南每餐必有毛主席爱吃的红烧肉,但最后压轴的是大路货西瓜而不是青木瓜。我们居住的宾馆倒是临近湖畔,阳台挑在湖面上,蛙虫的鸣叫灌了个满耳,而且生态好到浴室里竟然有一只毫不惧人的大壁虎。宾馆里的陈设都很传统古雅,挂画却是一水儿的现代派,一幅描绘孩童的油画让我想起毕加索的《第一步》,另一幅中年妇人像则让我想起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妇女。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我们参观了主席府、胡志明陵墓及故居,一路上都是革命传统教育。最后一站是胡志明博物馆,进去后意外地发现这里已被现代派“占领”。虽然我眼拙,可还是看出好几个陈列品应该属于装置艺术的范畴。馆内特设了现代史小展厅,挂着卓别林、爱因斯坦、林白等人的照片,没有梦露但好像有嘉宝;还特设了现代艺术陈列室,摆着康定斯基、米罗、马蒂斯的复制品。总之,在这个博物馆里,革命和现代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当年胡伯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正是现代派的青葱岁月。那时革命就是现代派,现代派就是革命。不知他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是否曾与毕加索擦肩而过。我能想象得到,这两个小个子走起路来肯定是风风火火的——革命可不是闲庭散步。
越南文艺界估计根本就没有列宾和列维坦什么事,艺术青年一上来就直接跟法国现代派接上了头。河内值得看的老房子,也大多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黄色建筑,初看太庸俗,但在那多雨的天气里,在绿树的掩映下,确实找不出比黄色更好的颜色了。现在法国人又过来投资,来造香水,来拍电影。在下龙湾乘船游览时,我就想起了《印度支那》,里面的法国军官和越南少女驾着小舟,在水面上顺流飘荡,任意西东。影片把下龙湾拍得那么美,如果以后越南要拍申奥片,得想法把这一段加进去。
下龙湾有很大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大色块的披肩,寥寥几笔的越南少女速写,蒙德里安风格的果盘,显示出这个国家的手艺人都有不俗的品味。当时嫌拎在手上太费事,就没怎么买。不料到了中越边境的芒街,工艺品就变得极其粗劣起来。无甚收获地回到了家,又翻出《青木瓜的滋味》看了一遍。镜头中的丫鬟用刀将青木瓜剖开,那白色的瓜籽仿佛一个个蠕动的虫蛹,渴望着在美丽新世界里破茧成蝶。
莫大
王怜花
春天的早些时候,在厦门海边的夜宴上,江湖上——特别是在金融界——鼎鼎大名的巴曙松博士在席间说起一个银行业界人士,用“才高于志,土木形骸”这八个字来形容。其时我的《古金兵器谱》正在当当、卓越、旌旗以及各地的书店热卖中——那是一本谈论古龙和金庸书中人物的道路问题的书。听到巴博士此言,我猛然想到,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
“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出场很少,总共不过寥寥几次,却次次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乃是一等一的人物。第一次出场是在衡山城的一家茶馆里,第二次出场一剑杀了嵩山派的高手费彬转身便走。第三次出场是和令狐冲在一个小酒馆中对饮。在令狐冲看来,“他有时出言甚是文雅,有时却又夹几句粗俗俚语,说他是一派掌门,也真有些不像。”他的胡琴,一味凄凉,往而不复,不求中正平和,但求率性而已。
对于个人来说,对幸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不过,一个人志向太大了,对他自己来说多半是一个不幸。不说那志大才疏的,也不说那怀才不遇的,单说那功成身就的,一般是少不了要勉强别人也勉强自己的。所以,一个人能才高于志,便已脱了苦海;还能做到土木形骸,那他是有福了。“土木形骸”这四个字,最早是用来形容刘伶的。《名士传》说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随之,日:‘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关于刘伶的记载,都是很有趣的。《竹林七贤论》说到有一次别人跟他吵架急了要揍他时,“伶和其色日:‘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最有名的要算《世说新语》里说的故事:刘伶的老婆劝他戒酒,刘伶说好呀,你弄点酒肉来,我对神发誓戒酒,结果,刘伶对着祭神用的酒肉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不过,刘伶最高妙的地方是他虽然才高八斗,却“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这是他胜过“竹林七贤”中另外几位的地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窥见“唯有文章才能不朽”这一奥秘,以他之才,却“未尝措意文章”,一辈子只写了一篇《酒德颂》,呵呵,那是不求不朽的智慧和境界了。
在真实的刘伶或者虚构的莫大这样的人物身上,我印证了我对生活的一个朴素的见解——幸福就是做一个不求进取的天才,胡乱快活一世。这和巴博士所说的“才高于志,土木形骸”应该是一个意思。
十年的一首歌
曹红蓓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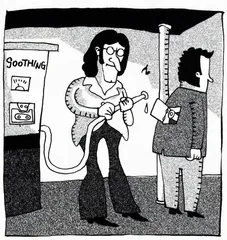
我和《HEY,JUDE!》属于一见钟情。
当时我们正在军训。压抑的情绪总也找不到出口,只有通过狂吃肉卷来发泄。有一次,区队长集中大家的磁带去资料库录东西,我填上了BEATLES。晚上熄灯号吹了以后,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听着耳机里的BEATLES。开始是几首快歌,突然毫无准备地,“HEY,JUDE!”这一句呼唤就在脑袋两侧凌空炸出来,没有一点前奏。当时我的眼泪像得令似地刷地就下来了,虽然根本就不知道JUDE是什么鸟人,可是感觉就像自己被呼唤着一样,上帝呼唤的。他老人家终于他妈的想起我来了。旋律那么单纯,节奏那么熨贴,歌词那么不知所云,具备好歌的一切素质,这个就是音乐了。只有音乐能直入人心,它根本不需要说清楚什么,可是它能在第一时间拨开层层乌云,把你心底的灯泡逐个点亮。
渐渐地,我发现BEATLES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SOOTHING,慰藉!人这种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向死而生的可怜的动物,总得不停地寻求慰藉,靠着这样那样的慰藉,好不停地在脑内产生某种幸福的幻觉,再靠着这种幻觉来制造勇气。就像《HEY,JUDE》,我出生之前它就在人间广泛从事着SOOTHE的工作,而不久前新加坡小女孩孙燕姿把这盘老化石差不多原样重炒后居然还能做排行榜第一名,可见人就是人,早生晚生其实都无所谓。
另一次被《HEY,JUDE!》拥抱,是有一次在包间唱歌,和一帮各色老外。那次唱歌是为了作鸟兽散,醉里言欢,没有人放不开。其中有一A,学的专业是导演,平常顶滑稽搞笑。他五音勉强能凑足四个半,点了《HEY,JUDE》。刚开口,马上变成大合唱,唱了一晚上,原来只有这首是中外通吃。A意外地唱得特别正确、正经。不仅他正经,大家帮腔都帮得怪严肃的,到了结末副歌NANANA的时候,简直有点宗教气氛了!理想,理想在腐败的KTV激荡。浩歌长吟后的结果,就是他的脸红得像西红柿要爆炸,还NAIVE地问:“咦,怎么你们的脸全都红的?”就因为这首歌,我会永远记得这位仁兄的面目。
《HEY,JUDE!》之前之后,让我红了眼圈的歌有多少,我没有算过,但《HEY,JUDE!》稳坐我最爱的歌头把交椅至今10年,特此铭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