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沈宏非:祭鳄鱼文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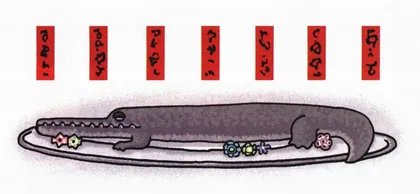
“驯化我吧,那么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千万别忘记,你永远对你所驯化的东西负有责任。”这是一只狐狸对小王子说过的话。
“负责任”什么的先不去说它,就“驯化”而言,同样的三个字,在事前和事后所表达的含意是不太一致的。虽然广州的野味批发市场上曾有人工养殖的狐狸出售,但是我不知到狐狸有没有被人类驯化过。鳄鱼也是这样,广州某动物园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鳄鱼养殖场,存栏量可达十万条,并且在这家动物园所属的酒店里提供鳄鱼大餐。“非典”前的“负责任”的说法是:鳄鱼肉“滋心润肺,补气壮骨、止血化淤、驱除湿热,口感细腻,味道鲜美”;“非典”后,在无任何证据表明鳄鱼就是传播“非典”之大鳄的情况下,店方又高调宣布为了防“非典”而从此不卖了。
当然这谈不上什么始乱终弃。鳄鱼不会表演,不会顶球,也不会骑单车,但是可以人工养殖,可卖,可吃。在某种意义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卖,有目的有态度地吃,本身就是“驯化”的目的之一。就是不知道商标化、符号化能否也算是“驯化”或者“驯化”过程中的某种阶段某个层次——Lacoste,法国名牌时装,汉语地区统称“鳄鱼”,衣衫上,作为Logo的鳄鱼真有一条。但Lacoste并非鳄鱼之意,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网球手Rene Lacoste之名。因他打球攻击性强,鼻子特长,江湖上人称alligator,鳄鱼。就像前几天广州某报赠与威廉姆斯姐妹的最新封号:“威廉母狮。”Lacoste毕生最辉煌的成就,不是赢过两届温网、两届美国公开赛、三届法国公开赛以及一届戴维斯杯,而是驯化了一条鳄鱼——他改革了球场着衣传统,除了“长袖改短袖”,还在左胸绣上鳄鱼标记。Lacoste 退役后,绣上鳄鱼标记的Lacoste运动衫进入批量生产,当时在衣服上绣标记之风尚未开启,Lacoste是商标外化的始作俑者。Lacoste的魅力名望使“鳄鱼”得到迅速推广,尤其在北美,“鳄鱼”成为中产阶级衣橱里的主力。
Naomi Klein,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8岁时就是一个迷恋名牌的美少女,故成年之后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成为“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在《NO LOGO》一书中,Naomi借“鳄鱼”Logo描述了商标的做大史:“70年代初以前,衣服上的商标大多是隐形的,谨慎地缝在领子的内侧里面…70年代晚期,Ralph Lauren的Polo骑士以及Izod Lacoste的鳄鱼逃离了高尔夫球场,奔入大街小巷,毅然决然将商标推上了上衣外侧。这些商标的社会作用就跟衣服的价格标签一样:大家清楚知道穿者愿意为品味花上多少钱。80年代中期,CK、Esprit以及加拿大的Roots加入了Lacoste和Ralph Lauren的阵营,商标已从夸炫的无聊玩意儿转变成活跃的时尚配件。更重要的是,商标本身的体积变大了,从3/4英寸的符号膨胀为胸膛大小的图形。这股商标膨胀的潮流依然在发展中……过去15年来,商标膨胀得如此巨大,衣服实质上已变成了承载商标的一团空白。换言之,作为隐喻符号的鳄鱼已一跃而起,吞下了真实的上衣。”
隐喻的“鳄鱼”有多膨胀,有多生猛?Naomi引用了另一个文本:1998年3月,里斯本动物园商业处处长Silvino Gomes对Lacoste公司颇富创意的企业赞助案发表评论说:“既然鳄鱼是Lacoste的象征符号,因此我们猜想他们也许会有兴趣赞助我们这儿的鳄鱼。”不管鳄鱼的符号有没有符号化/驯化里斯本动物园里那些生物学上的鳄鱼,它还是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们对鳄鱼的认识,例如,鳄嘴的向左还是向右。以下是吾友的亲身经历:90年代初,港产Crocodile横行内地,这名香港男青年穿一件Lacoste到沪,夜里出去玩,在酒吧里竟吃了一识货之上海女青年的背后讥笑:“这个港巴,连鳄鱼都要穿假的。”许多年以后,坐在新天地的衣香鬓影里,回首当年非典型鳄鱼事件,中年港巴唏嘘不已,久久无法释怀:“那种感觉,就像请人吃鱼翅,那人吃后一抹嘴扔下一句:‘没想到连粉丝也可以做得这样难吃。”
因以形态各异之以鳄鱼为商标出产“鳄鱼”服装者众多(在中国及东南亚市场上,一度有三条大鳄共趟着这潭热得冒泡的浑水),Lacoste后来在另一条经典品牌线IZOD LACOSTE已将原先的鳄鱼标志修改或者移去。这意味着一场驯鳄记最终很可能以鳄鱼符号的淡出而收场。人对他所驯化的东西负有责任,还是人所驯化的东西对人负有责任。驯鳄凡70年来,从符号消费到消费符号,就好像从暴力美学到美学暴力,对于我们日渐衰退的常识和想象力,到广州来喝几口鳄鱼汤,不知会不会起到“滋心润肺,补气壮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