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要反什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邱海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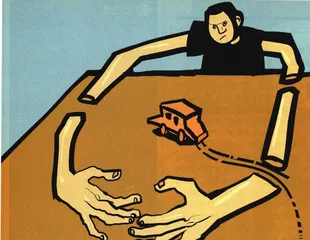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出台了《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被认为是《反垄断法》的前奏,您怎样看待这个规定的意义?
毛寿龙:反价格垄断规定多少还属于政府价格管制的范畴,和反垄断法有很大差别。这个规定的意义在于提出了具体反对目标,如区别定价、捆绑销售、协议定价等等,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走出自己操作价格的困境。对企业来说,反价格垄断规定让企业很难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制订价格同盟,但要注意口头协议是无法杜绝的,价格垄断仍将广泛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制定《反垄断法》重点应当反哪几类垄断?
毛寿龙:反垄断在中国的任务主要是反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目前集中表现为地方性保护垄断和行业协会垄断。中国仍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大多数行业表现为分割市场的垄断,也就是由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目的而与企业配合制造垄断。其次是行业垄断,现在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行业协会垄断。
三联生活周刊:《反垄断法》能不能打破目前电信、石油、电力、烟草等行业存在的垄断现象?
毛寿龙:很困难。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虽然也进行了拆分,但仍属垄断性竞争,是相互隔离的竞争,要靠《反垄断法》改变这种垄断格局非常困难。这些行业本身是国家的垄断部门,和政府权力密切相关,即使《反垄断法》出台,国家还将会给它们很多扶持政策。另外在《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这些垄断部门的干预和插手,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是垄断的主要受害者,但在立法过程中很难对立法决策产生影响。最后《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存在疑问,中国的司法体系非常分散,执法主要由基层完成,即使有了《反垄断法》,也很难对国家级大企业实施制裁。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应当成立一个独立的执行机构来保证《反垄断法》实施?
毛寿龙:这正是《反垄断法》将要面临的一大难题。理论上说,确实需要一个独立机构来承担反垄断职能,这个机构必须独立于行政部门。但中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体制人为因素较多,立法、司法机构力量不强,最后还是要依靠行政手段。因此我认为至少在目前,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时机还不成熟。
三联生活周刊:《反垄断法》是否应当对企业购并行为做出规定?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外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反对《反垄断法》,尤其是其中对企业购并的约束条款。
毛寿龙:一般说,《反垄断法》会对企业并购做出某些规定,但我个人认为,目前对企业并购在法律上规定过严不一定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增强竞争力。我们经常看到政府靠行政手段组合“国企航母”的行为,但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依据市场信息做出兼并重组决策的案例,微软案带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是:在市场空间非常广阔的情况下,出于市场目的、经过市场手段形成的垄断实际是非常微弱的,政府不应当过于干预。因此我希望中国《反垄断法》在吸取国际智慧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应当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入世以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整合力度越来越大,《反垄断法》是否应当对外企在国内的并购行为做出规定?
毛寿龙:如果刻意地用《反垄断法》保护民族工业,那是用错了工具。外资企业应当享受国民待遇,不应在《反垄断法》中制订歧视跨国公司的条款。但跨国公司是在中国市场尚未成熟时进入的,在很多领域,跨国公司的资本、管理、技术优势能自然形成垄断,更需要警惕的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实际具有和大型国企相似的政治地位,外资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这类政治影响力取得对国内企业的优势,进而形成垄断。《反垄断法》应当对跨国企业这类非市场行为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