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时期的典型读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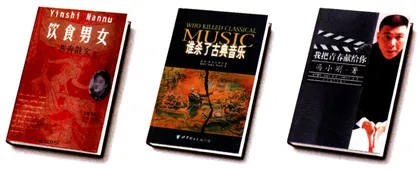
我们毫无准备地被抛进了疫情恐慌。生于忧患的中国人什么倒霉事都想过:战争、地震、洪水……甚至外星人入侵,但没想到突然来的是萨斯。我们显得非常狼狈,面对这么大的麻烦,大家没有经验(谁经历过这种事啊),没有理论(没有人能告诉你疫潮中什么是真正合乎理性的态度),甚至没有知识(中国有那么多在编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但居然没人能说一点掌故,聊一聊更早的人类怎样和瘟疫作斗争或被瘟疫斗争)。我只读到山西谢泳写的一篇短文,介绍1918年晋北的肺疫,山西都督阎锡山定下的方针是“主防不主治”,一声令下,“清洁隔离,埋尸封室”。
恐慌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就娱乐文化市场而言,那些必须在公共场所完成购买和消费的娱乐活动大受打击,甚至死期不远。电影院、戏院的上座堪虞,餐饮业(也算一种娱乐吧)的食客日稀,更会有多少寻芳客如今还敢在密不透风的夜店包房里消费小姐?能够在家中完成的文化消费将指数上升,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订阅报刊的阅读率肯定走高。而必须在公共场所购买、消费可回家进行的商品,比如影碟,比如图书,会在方死方生之间挣扎。
其实读书是逃避恐慌的好办法。因人而异,各种图书都会有反恐防恐的麻醉作用,但比较而言,一些轻巧的奇谈怪论更能化解百结愁肠。
《我把青春献给你》(冯小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首印15万册,已经畅销了近一个月,走完首印数应该问题不大。这本书号称是冯小刚的自传,不过大多数读者肯定不会把它当真。这本书是以传记的名义,以段子集成的写法,记录了作者经历见闻的趣事和笑话,所以读来很惬意。
看完这本书,竟然有些感慨。第一,娱乐界人士真叫胆大,什么事张嘴就来。譬如书中提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如何如何,陈布雷如果做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那陈伯达就肯定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这段“史料”太新鲜了。第二,娱乐明星有时比知识界清流更清高。“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葛优,他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买块地板革。”能为买一块地板革谢绝《纽约时报》捧场,中国文化界大小人物中百无其一。
《谁杀了古典音乐》([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查修杰、施碧玉、陈效真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3月第1版)写的是欧美的艺术市场,作者是位讼棍似的评论家,行文泼辣,用词尖刻,他写作这部材料极为丰富的书是想说古典音乐死了,古典音乐被市场行为杀害了。这部书里故事多多,而且大多数都用来糟蹋西方古典音乐大师。作者认定这些贪婪的大师,还有“那些肥胖的、俗不可耐的、西装上还有烟灰斑点的经纪人”,是杀害古典音乐的罪魁祸首。
莱布雷希特的说法起码是言过其实,甚至是不经之谈。中国人能亲炙西方古典音乐,完全拜唱片工业之赐。不过读到那些恶心故事,遥想高尚的古典音乐身后竟然是有娈童癖的著名指挥、“裤子拉链大开地站在女秘书身旁”的制作人……你总会有点灰心,会忍不住揣摩萨斯是不是对肮脏人类的一种惩罚?
《饮食男女——一苏青散文》(《边缘书库》之一,李庆西、陈子善主编,万书堂策划,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是近年来苏青多种文集中的最新一本,有可能是编得最讲究的一本。书的封面来自苏青最早的出版物,创意大胆。
苏青的才情不如张爱玲,但想法和表达都比张爱玲更直接。她的一些话,现在听起来还是语出惊人:“女人以‘失嫁’为最可怕。过时不嫁有起生理变态的危机。不过知识浅的还容易嫁人,知识高的一时找不到正式配偶,无可奈何的补救办法,说出来恐怕要挨骂,我以为还是找个把情人来补救吧,总较做人家的正式姨太太好。丈夫是宁缺毋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仅1/3。这样说来,似乎太便宜了男人,不过照目前(希望仅限于目前)实际情形而论,男人也有他的困难,不能牺牲他的第一个妻子(假定她是不能自立的,也无法改嫁的)。而知识妇女自有其生活能力,不妨仅侵占别人感情而不剥夺别人之生活权利。”作为女人,她说话太犀利,有伤天和,虽然让古往今来男人听了偷着乐,但她自己却遭了报应,一生情事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