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脑死亡“首例制造”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雷静)
46天后,武汉东西湖区的毛子俊才从当天的报纸上得知:父亲毛金生的去世被称作是“中国首例脑死亡”——4月11日,武汉同济医院通过媒体公布了46天前发生在医院的这一“事件”。
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
4天后,29岁的毛子俊在接受采访时仍满脸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地“一夜之间成了名”,不断地被媒体追踪采访,“有些接受不了,心里很乱”。在叙述当中他一再想表达的是,这一事件中自己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更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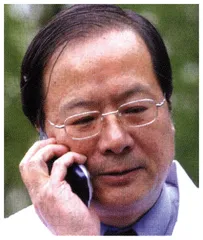
张苏明
“3月22日晚上7点多,当时他正在看我们结婚录制的光碟,有说有笑的。没想到上完厕所回来就满头出冷汗,不能说话。”2月8日刚结婚的毛子俊回忆说,这之前,61岁的父亲除了有点糖尿病外,身体一直都还不错。
在当地医院初诊为脑干出血后,毛金生次日晨被紧急转往市中心的同济医院。“脑外科的专家会诊后认为,情况非常严重,随时有危险。”毛子俊说,“当时我们手里带着3万多现金,家里人表态——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病治好。”
但是,父亲的病情在4月24日继续恶化,已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毛子俊说当时来了七八个专家会诊,“很感谢医院这么重视”。他已很难记起当时做了几次诊断,只记得专家和家属一起“开了两次会”。
开第一次会时的毛子俊手上已经有了病危通知单,“专家说要做好准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第二次会是在4月25日晚上的9点钟,“当时专家就说,父亲的心脏还在跳,但其他地方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脑干反射消失。在国外,按惯例这已经是脑死亡。问我们愿不愿意录像,保存好完整的资料,为以后的教学和立法做贡献。”毛子俊回忆,当时家属并没想到那么多,“只知道人已经不行了”。
在这个时候,毛子俊面临着两种选择:签字承认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每天继续提供几千元的费用对父亲进行治疗,延续心脏跳动这一生理反应——而这在传统里面,意味着人还没有去世。
毛子俊的父亲生前是街道退休干部,医疗费用可报销75%,“不存在费用问题”。但他也从专家那里明白一个事实:不管用什么先进的仪器,继续治疗是无谓的,父亲不可能再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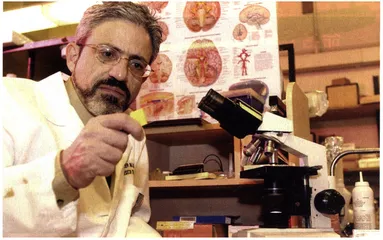
脑死亡标准的确立,牵涉到法学、社会学、医学等问题
在这两个选项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前者。他说,家属之间并没为这一选择产生过争执,另外一些家属跟他一样,没有反对意见。“当时的会议作了纪录,在场的十几个亲属都在上面签了字。”
这确实是一个范例
领衔进行诊断的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苏明教授,依据此前进行的三次脑死亡诊断填写了《死亡通知书》。“这是一份特殊的死亡通知书。”张苏明说,通常通知书上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而在这份通知书上则是:“脑死亡,脑干死亡。”
当晚10时45分,帮助毛金生维持了30多个小时呼吸的呼吸机被拆除。11时零5分,毛金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的21分钟。“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男家属相对比较冷静,一些女家属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张苏明教授回忆说。
在这21分钟,当其他家属都在病房注视着父亲的时候,毛子俊说他一直呆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感觉都没有。”当病房里面的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他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知道怎么救都救不回来。
4月12日晚,在央视播出“中国实施首例脑死亡”的消息时,坐在陈忠华身边观看新闻的是英国器官移植学会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对陈忠华说,“这是在中国脑死亡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身为同济医院脑死亡工作协作组组长的陈忠华在受访时,更愿意用“国际上(而不仅是国内)引起反响”来表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而在这一事件的传播中,一个关键词汇是:“首例”。在公众的印象中,脑死亡的记录这次并非是第一例。但张苏明教授告诉记者,说“首例”有明确依据:第一次按正规的脑死亡标准(卫生部颁布的《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通过严格审查;正式通知家属,征得家属同意,终止治疗;全程用图像记录案例资料。
“这不是中国人首次实行脑死亡,但以往的案例没有公开报道,没有公开的标准,没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作为证据。”陈忠华教授说,在这一案例中,他是策划者,对整个操作步骤、程序、标准等进行监控,“这确实不是炒作,是一个范例。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又没有违背法律,延伸生命的自主权。”
最终还是要促进立法
“要通过这一案例传递一个科学概念,让人们对死亡的本质有一个重新界定和认识,同时推动立法。”张苏明教授说告诉记者,这是实施首例脑死亡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与脑死亡专家的沟通中,“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放在一起则成为专家避讳的话题。担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陈忠华严谨地向记者表示:“我的身份是多重的,在这一案例操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外科医生,一名科学家,我在这中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这一案例不存在器官要求,是一个很干净的案例。”陈忠华表示,即便是此事推动促成脑死亡立法,也对器官移植供体缺乏起不到缓解作用,更无实质性的帮助,“产生质疑是正常的,科学在质疑和争论之间明了。”
“我们所做的和所谈的是纯科学的事情,最终还是要促进立法。”张苏明教授说,“至于立法后会有什么功效,那是‘后话’。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往往会把好的事情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