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英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怜花 舒可文 老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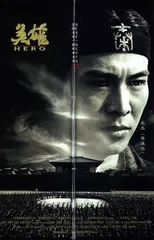
“文化淤积”与“庸常的审美”
王怜花
导演卡梅伦不止一次在海底13000英尺处打量着“泰坦尼克号”残骸,与日后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引起的轰动相比,海底是沉寂的,内心的冲动怎样慢慢平息和积累?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得到这样的表达机会,他需要大笔的金钱把自己头脑中绚丽的画面搬上银幕。
陕西人张艺谋也许对秦始皇情有独钟,3100万美元的投资帮助他讲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各种批评也随之而来。
“文化淤积”,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本来就是一个看热闹的电影,怎么会引来那么多关于历史观的讨论?一方面,我们讨厌说教的东西反对“文以载道”,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看到某种反抗,似乎电影是文化斗争的武器。电影不是一种杂耍吗?
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游戏精神与文化反思都缺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这两个东西哪一个都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效应。艺术应该宽容,可我们还不习惯纵容大家的想象力。如果说《英雄》是我们第一个商业大片,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好观看《真实的谎言》那样的准备,像接受施瓦辛格的肌肉那样接受李连杰的动作?
“庸常的审美”,这是我想到的第二个词。人们进入电影院,得到视觉上的享受,得到一个简单的能用镜头讲清楚的故事,得到一两句台词,这就不容易了。“庸常的审美”反对沉闷,反对病态和苍白,反对高深。
正如中产阶级正在中国缓慢地形成一样,“庸常审美”的价值观也还远没有成为文化评判的主流。这个词不含有任何贬义,就如同可以用“单调和乏味”来形容一种幸福的生活。我们看电影不是搞艺术鉴赏,而只是作为消遣。相应的,对电影的评价,更多是消费指南,而不是有关艺术与艺术家的战斗檄文。在这一点上,《英雄》的成功之处就是它作为消费品的可贵——成本高,广告促进购买。
刺秦故事与历史责任
主笔 舒可文
荆轲刺秦的故事几年之中被周晓文、陈凯歌讲,现在又被张艺谋讲,三部电影都在各说其是。《秦颂》和《荆轲刺秦王》在对这段悲剧故事的整理中,都浸透着现代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嬴政不仅是君王,也有其丰满的精神世界,荆轲的牺牲挡不住历史车轮;或者政治理想在人道主义牺牲的比量下渐渐暗淡。
艾科在对他的历史小说《玫瑰之名》的解释里说,他不是要讲中世纪,而是把故事放在中世纪讲,仅仅因为他要毒死一个教士。在历史问题上避开了哲学家从大处着手的评价责任。而按张艺谋的解释,《英雄》的动机是因为他想看看“一个放弃的英雄会怎么样,因为什么放弃、放弃了还是不是英雄。”其余部分就是构造技术程序了,所以他也讲的不是秦,不过是放在秦讲,表达历史观当然不是其志之所在。
张艺谋常常被人比作农民,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叙事中有一种评书式的务实,其故事都被一个个梦想简而化之。有失复杂的反思,却也从执拗里获得了一种力量。《英雄》在传统悲剧模式之外,试探了一个新形象——无名的无功而死不是因为命运难料、小人作梗;没有误解障碍,没有偶然事变,他在别人的牺牲与信任之上,扫清所有障碍后放弃命运,像所有英雄一样的凛然,他在成功与失败难以判定中展示出一种更可探讨的悲剧力量。这是张艺谋依然不失为“文艺片”导演之所在。
一个中国导演想讲一个免于西方的普适思想解释的中国故事已经很难,《英雄》里所说“天下”放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里,构成了意识的复杂化——如何来看待个人与历史,历史究竟是谁创造,在现代国家意识上又怎样读解历史?这些在叙述与历史互文性中都成了问题。张艺谋无疑需要为他对历史的态度付出代价。
三个不可比的导演的勉强联系
老于
50年前,还年轻的黑泽明决定把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改编成电影《罗生门》,他觉得《罗生门》是他的想法及意念付诸实验的最佳素材:“我将人心曲折和复杂的阴影加以素描,以锐利的刀剖析人性深处。”
为了对应不可知,黑泽明选择了对一段做事的多重叙述,每次叙述人都有自己的说法,都推翻了前一个叙述人。他采用了多视角、环状的重复叙事结构了整部电影,你永远不可能从樵夫、贵妇、强盗和通灵者相互矛盾的故事里找到真相。也许就是叙述上不断推翻的方式,让很多人觉得张艺谋《英雄》里模仿了黑泽明。其实两者相差太远。张艺谋在《英雄》里其实使用了线性故事线,尽管秦王确实根据个人的判断不断纠正着无名的故事,但这是张艺谋为了让故事更吸引观众而安排的推理。何况影片还有一个确凿的结尾,毫不迟疑地告诉了大家一个真相,这很符合张艺谋要讲一个简单有力的故事的初衷。
黑泽明的《影子武士》里有黑压压的军队,《英雄》里也有,偏偏给黑泽明做服装设计的和田惠美也给《英雄》定了造型,两者在大场面上的影像风格确有相似之处。但张艺谋的军队更多是一种声势,而非用来衬托个人的渺小。对应黑泽明影片的深刻,反映出张艺谋的朴实。
从一开始“模仿”的话题就不曾离开《英雄》,这跟李安《卧虎藏龙》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同样是武侠片,很多工作人员也相同,但张艺谋和李安的个人气质决定了两部片子的差异。张艺谋不会像李安那样与影片里的人物纠结。李安对李慕白有一种知识分子性的,近乎自怜的认同:“我曾一再地追问自己,在李慕白心中,玉蛟龙到底是什么?这堆纠结是否就是‘藏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在背后驱策着他?……没有赌干净,不到自我毁灭,他是不会停止的……人就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是与‘浪漫’非常相似的力量,亦即‘感性’。挡不住的。挡得住,你这个人也就没啥味道了。”相比而言,张艺谋的英雄们恰恰是什么都挡得住的,《英雄》是刚性的,接近张艺谋对侠的看法。李安的侠先是一个有心事的人,张艺谋的侠注定不是一个平凡人。
李安能理解他影片里所有的人物,所以其电影有知识分子气和阴柔之感。李安一反新武侠片漫天乱飞的做派,更靠近胡金铨时期的拍法。他无意中给张艺谋出了一个难题,让此后《英雄》的拍摄处处充满着对照性评论。
张艺谋差不多每一部电影都让人跟别的导演的作品联系起来。也许由0到1不是张艺谋的擅长,他的长处是能从1做到3,甚至到5。张艺谋确实有一种本能,就是知道别人想要什么,完全如同农村的庙会上,什么鲜艳用什么,什么热闹用什么。很多时候他像一个世俗智慧的大实在人。他在拍摄《英雄》的时候说:“我们就把这些文化符号都一一排列出来(大意)……”他对视觉的感悟力是中国电影导演中数一数二的,从《英雄》中看,他在黑色上做足了功夫,反光的黑、收敛的黑、陈旧的黑一一显出层次。也许他也真心喜欢着大家喜欢的东西。
黑泽明是有历史感的人,他早期电影实际上有一个雄心,就是用电影书写日本历史,后期拍摄《影子武士》,也是打算给当时的日本观众上历史课,尤其想重新解释武田信玄的儿子到底怎么样造成了整个家族的崩溃。而李安和张艺谋只是想讲一个自己心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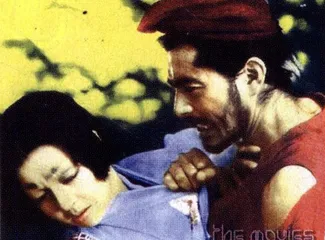
《罗生门》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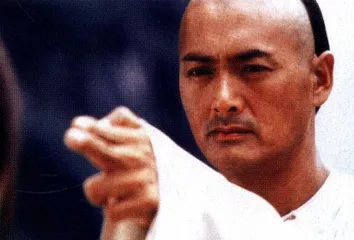
《卧龙藏龙》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