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焉不详的暧昧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许浅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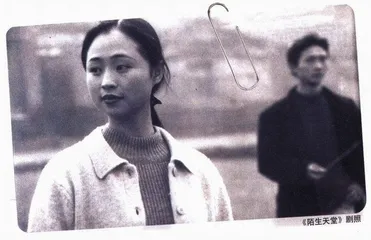 、
、
《陌生天堂》剧照
杨福东是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被邀请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参展作品电影《陌生天堂》曾因资金问题晾了五年,直至此届文献展提供了足够后期制作费用才正式制作完毕。《陌生天堂》始摄于1997年岁末,使用35毫米的黑白电影胶片,今年4月在广州完成了拷贝,最后定稿于76分钟。
杨福东曾在2001年北京首届独立映像展以一部《后房,嘿,天亮了》获得实验短片大奖,从而引起电影界关注。他对电影的痴迷开始于一些图片摄影和实验性影像。由于毕业于专业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杨福东的出身和国内其他独立电影人有所区别。
“独立电影”这个名词本身带有标签性质的虚荣作用,其传达出不同于主流电影的新鲜感令人很好奇。其实,《陌生天堂》的故事并不令人觉得新鲜。影片由一段类似纪录片的国画创作讲座开始,冗长达5分钟,这奠定了整部片子的气质基础。年轻人柱子自述生活在人间天堂的杭州,与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和未婚妻一起平静地过着一成不变的小日子。在杭州三四月份春雨季节里,柱子突然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恐慌不适,他怀疑自己和这个潮湿的城市一起得了一种怪病。一次次不停地去医院检查身体,每次医生都会告诉他,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从眼睛、鼻子、耳朵,到内脏,骨骼……柱子渐渐地觉得医生也许是正确的,他的焦虑和躁动慢慢平息下来。在一次邂逅中,柱子和一个清秀女孩开始了暧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和未婚妻的正常生活,两个人在人流中、街道上、居民楼里含含糊糊地亲密着。柱子的父母造访,他发现自己大概并不是真的有病,只是生活得过于安静,内心渴望激情。在雨季即将结束时,柱子送父母回乡,他还是结婚回到正常有序的生活中来,只有火车站上的一个疯子依旧故我勇敢地宣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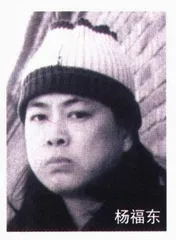
杨福东
城市病态男女的生活状态是许多电影不断重复的话题,至今还没有什么合乎逻辑值得确定的表现手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陌生天堂》虽然做到了将一种浮在镜头之上的情绪刻画出来,但也许这的确要归功于杨福东的影像感。有学习油画的底子,杨福东的影像明显比其他独立电影成熟许多。摄影风格舒缓凝重,高光的影调和略生硬的镜头切换显示出主人公的飘忽。从他的影像里,一位普通观众也可以抓住导演要叙述的故事或者情绪。很多独立电影的镜像手法让观者没有足够的耐心看下去,借助更多的旁白解释或影片分析才能得来导演的真正意图。杨福东的《陌生天堂》对白很少,大段的沉默与主人公长期面无表情的特写构成默契、明显而刻意的意图。影片从始至终就是这种闷闷的劲和不知所终的暧昧。
杨福东笑言柱子是个“小文人”。影片里小文人内心和他的行动相背离,没有一丝明朗。柱子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缺少服从意欲的认识和勇气,又不甘心沉沦,于是一切只能暧昧起来。柱子执著于想象中的病态,并在自己觉察生活过于平凡安静时享受着病态。作为一个小文人,他的反省能力可以感受到自身的需要,但在日常生活形态里,他却从根本上畏惧行动。无聊,则成为一种真正的困扰。画家顾磊在片中扮演了一个在火车站上的疯子,这是整部影片叙事风格中极不和谐的场景,带有一定的抽象性。疯子的行动有力校证了小文人的自欺欺人,倒成为影片中最大的亮点。与其说散淡风格的画面下的慢悠悠是杨福东影像的叙事节奏,倒不如说他实在愿意用此形式来准确表现这种自觉但不觉悟的困扰,可惜在他试图接近真实的表达自我时,向现实妥协的结局使这种着力表现的暧昧情绪淡化得语焉不详,这成为杨福东自己对梦想和现实的说不太清楚的认真妥协。
据说杨福东用的黑白塞璐璐古老胶片是过期的。他没有多余的钱成全自己完美的“胶片癖”。电影胶片确实帮了杨福东的忙,胶片对色彩的宽容度让他的镜头感画面感更充分体现出来。《陌生天堂》带上了一种四五十年代的优雅,有人因而认为这是杨福东向费穆的致敬。从2000年的作品《城市之光》到2001年的《后房,嘿,天亮了》,杨福东拍了几部实验性很强的观念短片,《陌生天堂》是惟一一部电影长片。(图片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