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上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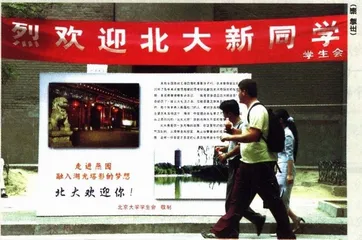
100个报名者中只有1个能成为“北大新同学”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北大学校规模的扩大是否也是社会需求的一种表现?
王登峰: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北大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完全在本科生这方面表现,北大选择了其他的方式,包括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远程教育等。北大的职能所在是解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现在我们几乎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北大现在已提前超过了“十五”规划所确定的规模。
三联生活周刊:北大还是坚持精英教育,这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从更长远角度,社会上关心的是,北大在规模上扩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王登峰:北大有一个先天问题,它决定了北大的扩展空间。我们的校园如果以燕园墙内的面积算起来只有1600亩,校园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承载量。我们的学生宿舍从建国以来就没有改善过,反而是越来越糟——人数一直在增加,宿舍没有明显的增加,新建的宿合远远抵消不了人数的增加。
三联生活周刊:在采访中,新建的北京电视台附近的北大学生宿舍被很多学生提起,很多人用“怨声载道”描述这个宿舍给学生带来的不便。
王登峰:这当然也和扩大规模有关,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建20万平方米的宿舍区,住在那边的北大学生要超过6000名。工程由北大做的担保贷款,但到现在工程依然没有交工,如果学生住不进去,那么我们一年要少招1500名学生,那还招什么生?这件事很复杂,既不是北大所能决定的,也不是学校之所愿。
三联生活周刊:宿舍是学校资源“瓶颈”的一个方面?
王登峰:这不是简单的学生宿合的问题,师资力量、实验室面积等都存在很大不足。5个人一起做实验与50个人一起做实验绝对是不一样的。在北大,每增加一个教师,学校一年投入的费用就是10万元。
三联生活周刊:人员性经费是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比重很大的一块?
王登峰:每年学校发给他的基本工资就要两万元,还有住房、配备的各种实验室、办公室,他的孩子在幼儿园、中小学的费用……这方面的投入国家没有给足。
三联生活周刊:北大同样面对着资金来源相对单一和不充足这个制约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
王登峰:从经费上来讲,我在加州大学时,他们圣地亚哥校区的一个行为科学系一年的运行费用就是2.4亿美元,这只是一个系的费用。北大一个大学一年的经费是5个亿。香港一所普通大学每年都有100多个亿,我们根本没法比。如果说我们之间经费差100倍,我们需要用100倍的聪明来弥补;那么北大与一些世界名校的历史也要差上100多年,我们又需要用100倍的聪明来弥补,这样北大的聪明就应该是他们的10000倍。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比较起来很悲观。有学者也认为,在未来大学竞争中,中国大学将在相对较长时期里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那么,北大提出的在2015年前后将北大建设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该怎么实现呢?
王登峰:这只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人才等,这看的是北大这个团队,是一个集体显示度。我们是在1999年的党代会上正式提出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的设定是保守估计吗?
王登峰:我们原来的规划是2030年前后,后来规划有所提前;第一个七年是打基础阶段,后十年是全面提高办学科研水平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北大的“世界一流”体现在哪里?
王登峰:主要是科研水平,我们强调的只是某些学科可能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一个多大的北大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北大相对应?
王登峰:数量的增加是以质量的牺牲为代价的,我们在大幅度增加研究生后就有了这样的教训。我们今后要在总体上控制现在的规模。比如在燕园校区,从明年开始缩减规模,比例大概在1%~2%左右,当然这是“上策”,研究生和本科生再缩减下来是比较难的。所以“中策”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稳定控制现在的规模,北大医学部的运行机制与燕园校区不完全相同,还有一定可利用的资源,所以还可以适当稳定地增加人数。下策就是增大规模,当然,我们的扩招规划主要是在北京之外的校区进行,比如在去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